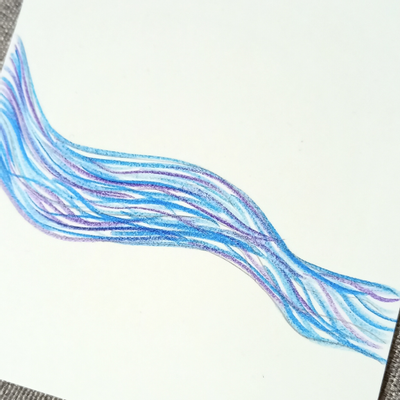巴黎的街頭,瀰漫著清霧般的小雨。
你的靴敲打在石版路上,聲音格外清脆。你不時的回頭張望。
而她,依然踩著自己的步伐,絲毫不受影響地欣賞沿路的櫥窗。你沮喪的走到我身邊,眼神仍無法離開她的身影,你試圖捕捉一絲來自她的關懷。她就像一隻靈巧的知更鳥,早已看穿了你的心思。你在她跟前的嘻笑,不曾改變她呼吸的節奏,只混亂了你靴子跟地面敲擊的間隔。
你放棄了,寧願繞到我們身後。她開始向我訴說離開愛人的思念。
他們分手了,沒有理由。「可能是相處太久,濃情轉淡了。」她說。語氣中沒有一丁點哀怨,就像她平常面對眾人時,那麼恬淡的語氣。在她的世界,大概沒有人間所謂的衝突。她敘述著分手的細節,有一段長長的間斷,伴著她呼吸的霧氣、跟車行過積水反射到她眼眸的亮光,很怕她在異國的街頭哭泣。那只是我的錯覺吧!她晶亮的眼反射的,僅是雨夜街頭的燈影。
我們遊走在新年的冷清街頭,一個不屬於我們的國度。
昨天市區的廣場上,擠滿來倒數的人們,他們瘋狂恣意地互相親吻,巴黎市的傳統。零點一到,我被陌生人擁在懷中,她尖叫地想要逃跑,我跟她都看見你,正開心得向一旁的褐髮女郎張開雙臂,反正,我們都收倒數不清陌生的吻。我討厭扎人的鬍鬚、醺人的體味、過近的距離,卻無法抑制的咯咯傻笑,粗魯的善意,瞬間沸騰我們降至冰點的情緒。
今夜,我們卻是無藥可救。
昨天的狂歡,更顯得空虛的突兀。我的手,放在冰冷的口袋裡。沿著無言的長街行走,我們三個是誰也安慰不了誰。總是一點點牽強的痕跡,就讓我想起那個男孩。你如小孩般受氣的表情,跟那個男孩有幾分神似,他總是在拉下臉孔後,就倔強離開。我不喜歡他的倔強好強,每次跟他爭執,這總是我情緒的引爆點。我再也不會見到他倔強的表情後,看到你跟他神似、卻老了十歲的臉,我憋著笑意。你看到我欲蓋彌彰的眼神,對我發了一頓莫名其妙的脾氣。我並不生氣,繼續跟著她的腳步前進。我知道你,跟那個男孩一樣,不想讓人看出你需要安慰的脆弱。
天空的雨好像快停止了。
你嚇倒大家。在杜拜的舞廳,離去前還見你拉著她在舞池裡輕移著腳步。我卻在隔天早晨被震耳欲聾的電話驚醒,有人看見從你的房間走出一位金髮碧眼的俄國女子。她的反應很平淡,對你的反應更平淡。大家都等著你澄清的說詞,你卻一句也沒留下。你對我說:「我需要愛情,心靈的,肉體的。」我很佩服你誠實的勇氣,而你對愛情的追求,同樣人印象深刻。
快走到香榭大道的盡頭,抬頭看見了摩天輪。
她領著我們快速穿越巴黎特有的複雜圓環,到了摩天輪的入口處。摩天輪前終於有了人潮,這是為了慶祝跨世紀而建的暫時性地標,當摩天輪車廂升到最高處,可以望見相榭大道的盡頭,另一側是羅浮宮及巴黎的動脈塞納河。
「雨停了。」,她試探性的望著我們問道。
「走吧!」,你爽快的回答,「今夜的我想要有飛行的感覺。」
我們坐上了摩天輪,車廂緩緩地往上攀升。
你突然抓住窗戶的欄杆猛烈搖晃著車廂,把頭伸出向著窗外大喊:「我怕高,我-怕-高!」我跟她面色蒼白的抓著你的肩膀,不知道突然陷入瘋狂的你,下一步是甚麼舉動。
突然,閃光燈亮了。
就在你把頭伸出摩天輪車廂的同時,我們被遊樂場的照相機拍照了!
我們三個楞了一下,過了兩秒,同時沒命的笑起來。
她開始瘋狂的搥打你,你扯著嗓子著往窗外大喊:「我-有-懼-高-症!」而我,因為笑得太用力而肚子痛、並且發不出任何聲音,我們的摩天輪車廂比剛剛搖晃得還要嚴重。
甚麼塞納河、羅浮宮、香榭大道、美麗的巴黎夜景,我們全都錯過。
一下了摩天輪,我們三個像是比賽賽跑一樣的直奔相片區,找尋那張讓我們驚愕的照片。我們的影像出現在14吋的電視螢幕上:你那佔據畫面五分之四的大臉正面朝著鏡頭吶喊,我跟她像扁豆般大小的臉孔也扭曲著、顯示我跟她正使出全身力量拉著一個害人精。
在這個怪異到極致的經典畫面前,我們三個的表情出奇的正經。你終於打破沈默:「不管啦,這張照片除了我也不會有別人買,這是我今年第一張照片,我要把它帶回家!」
我跟她當然沒有買那一張照片。等到數位相片沖洗出來,我們還是搶著再看一次。
我們在開始飄雪的巴黎街頭,盯著照片看了好久,好久。
後記:這是我最早的小說作品,寫在還在航空界值勤時。
因為有了開端,才會踏入小說創作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