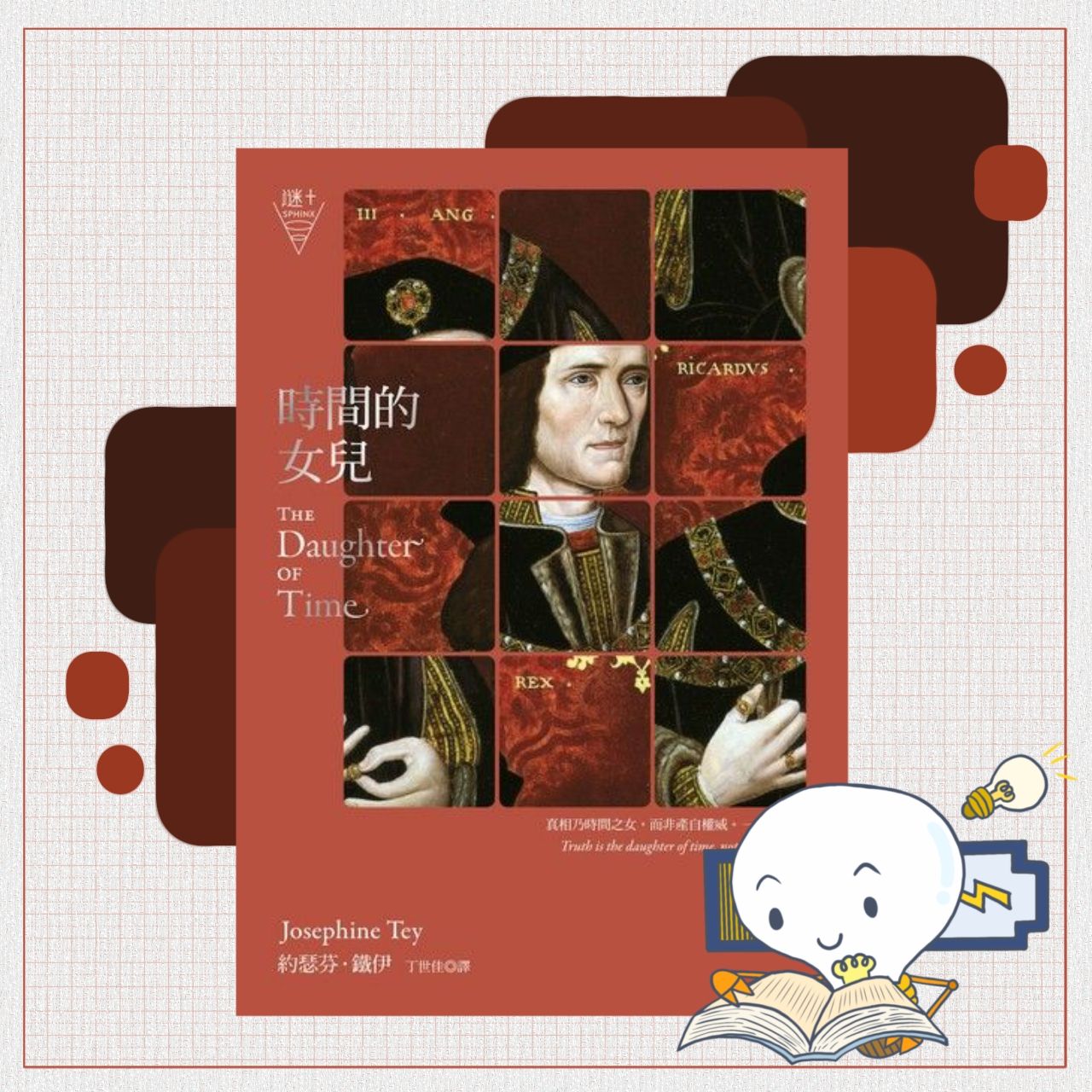只要他者存在就會有秘密與謊言
春節是台灣人與家人團圓的時候。雖然溫馨,但對不少人來說,也是壓力滿載的緊張時刻。有時我們會保守秘密,或是編造一些小謊言做為搪塞,因為親情的關心經常變成界線跨越的質問,讓我們渾身不自在。
只要他者存在,我們就會有秘密與謊言。
我曾經在另一篇文章討論過祕密這個主題,請參考:1996年榮獲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的《秘密與謊言》,數位修復版在春節期間重新上映,不禁讓我想到它與家庭議題的相關性。
這是一部真正的英國電影,我指的不只是導演跟演員都是英國人說英國腔,而是一看就會感受到具體而清晰的倫敦氛圍。不是富麗堂皇Central London那種情懷,而是庶民的倫敦氣味。那一本London A to Z,是否勾起了你的懷舊心情?現代人都是靠Google Map,年輕的朋友說不定完全不知道地球上曾經有這種地圖書呢。
英國導演麥克李(Mike Leigh)是深刻的社會觀察家,他的作品以現實主義手法著稱,忠實描繪日常生活中的細節,特別是普通人面對的挑戰與困境,反映出貧窮、勞動階級、家庭矛盾等社會議題。他特別注重角色的內心世界和情感層次,讓觀眾深入理解角色的動機與人性的多樣化。高齡81歲的他仍創作不懈,其新作《Hard Truths》在今年英國影藝學院電影獎(BAFTA)入圍最佳女主角與最佳英國電影提名,湊巧這位女主角正是《秘密與謊言》中飾演霍坦絲的Marianne Jean-Baptiste。麥克李跟肯洛區(Ken Loach)都是英國電影界的驕傲,也都堅持跟工人階級站在一起。
本片的配樂相當傑出,室內樂的編制,恰如其分地烘托出家庭動力的深層糾結。
片中主角都有祕密,隨著三條敘事線交織而浮現,但謊言並不多。幾位演員的表現既傳神又自然,無疑也是本片亮點,其中飾演辛西亞的Brenda Blethyn更是囊括各大影展最佳女主角獎。

(底下略有劇透,請您斟酌……)
霍坦絲:追尋「我從哪裡來」的勇者
電影用一場墓園喪禮開場。英國倫敦,一位從小被收養的黑人女性驗光師霍坦絲,在養母去世後,即便世故的社工隱微勸阻,她仍想要找尋生母,探問「為何拋下我」這個身世祕密。
死亡與誕生在這裡產生連結,電影要談的就是生死之間的人生,以及領養這件事對人生產生的巨大衝擊。
霍坦絲從未想過,生母竟然是白人。她選在自己生日那天跟生母見面。
這段接近祕密的旅程,衝撞著自己內心以及幾位未曾謀面的家人,眾人傷痕累累。

霍坦絲的人格特質相當平衡穩健。她既堅持要尋找生母,就得面對被拒絕的風險;但她卻也不會在面臨對方否認時咄咄逼人,而是願意給對方迴旋的空間,這需要相當的共情能力。再者,她是在養父母均過世之後,才去做這件事,足見她的體貼。她跟社工強調,養父母對她很好,她的動機並不是要找一個人來替代剛過世兩個月的養母。
精神分析最愛討論的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也是一位被收養的孩子,他也是堅持追求真相的勇敢之人。不幸的是,他的養父母沒有告訴他收養這件事,造成了災禍,而霍坦絲七歲時養父母告知她這個事實,但未多做討論,留下一道未解謎題。
如何「做自己」必然關係著「我從哪裡來」這個問題,不管是個人或是國家,我們都無法迴避這個扣問。
莫里斯:好好先生的快門下是真實或謊言
莫里斯是一位溫柔而成功的攝影師,經常要去婚禮拍攝。婚禮跟開場的喪禮構成一種對應。
他與妻子莫妮卡住在郊區的新家,過著小康的生活,但婚姻關係隱藏著秘密。莫妮卡脾氣陰鬱易怒,腹部常會不舒服。對這對夫妻來說,令人稱羨的別緻居家環境,或許像是某種謊言。
莫里斯一段時間沒有跟把自己帶大的姐姐辛西亞聯絡,也已經兩年半沒見到姐姐的女兒羅珊。羅珊的21歲生日快到了,他和莫妮卡想著是否要邀請他們來家裡坐坐,同時幫羅珊慶生。
莫里斯的工作必須要激發客戶的笑容。
我覺得這就是他個性的寫照,他是一個面面俱到的好好先生,好攝影師、好丈夫、好弟弟、好舅舅,他總在照顧身邊的人,想要帶給他們快樂,但委屈只能配著啤酒往肚裡吞,或許因為這樣,腹圍愈來愈大。

而他最愛的三個人,彼此之間相互仇恨,他被夾在中間。
辛西亞跟他說「你都不給我機會當姑媽。」這番話戳到他祕密的痛點。
片中的攝影場景非常精彩,帶著一種靜觀人間百態的悲憫,特別能攪動我的思緒。對我來說,這些場景相當於本片的強烈印記,永生難忘。
快門按下的瞬間,所呈現的情感究竟是真實還是謊言呢?
一個金髮美女的絕美側臉,頭側向另外一邊,觀眾發現她臉頰滿佈車禍的傷疤。
有一對夫妻,太太嫌先生戴眼鏡不好看,先生嫌太太十字架項鍊沒有亮出來。一拍完倆人的笑容秒收斂,呈現某種怨懟與不耐。在這個情境下,相片中的笑容與和睦顯然是謊言,而攝影師竟成共犯。
關係中我們總是可以從對方身上找到不順眼之處,但如果將之無限放大,關係要如何維繫呢?是否因此忽略了更可貴的部分?
關於這個議題,請參考我《墜惡真相》影評:
辛西亞:想要親密卻把人推遠的單親媽媽
辛西亞是個生活拮据的單親媽媽,與脾氣暴躁的女兒羅珊住在倫敦的一間小屋中。
記得好友看完本片說,他很討厭辛西亞這個角色,聽到她的聲音、看到她的表情,就覺得受不了。
我知道辛西亞是一個生活窘迫、生命資源有限而筋疲力竭的勞動婦女,這樣的理解就減少了負面觀感。
辛西亞用自己的苦(我十歲喪母後被迫照顧爸爸和弟弟),要家人對她好一些,簡言之就是「情緒勒索」。
她相當迷戀自己的身體。做為男人慾望的對象,似乎是她最大的成就,但也因此成為單親媽媽。
她怪罪女兒「因為照顧你讓我人生失敗」,坦白說,這種台詞在台灣的家庭中並不罕見。
她不喜歡弟媳莫妮卡,隱約透露出「這女人把弟弟搶走」的感覺,明顯帶著嫉恨(她家裡為何需要六個房間)。
我覺得辛西亞擁抱莫里斯的方式,顯然是過分親近了。某種欲望的錯置,透露出她想要把弟弟當成家裡的男人、女兒的父親。那是這個家從來不曾擁有的角色,或許丈夫/父親的缺席,導致母女之間的衝突愈發激烈。
辛西亞關心女兒,愛卻總是越過該有的界線,她一直要建議羅珊該如何避孕,其實是因為這連結到自己年輕時荒唐歲月的過錯。但對羅珊來說,這個母親是侵入性的。
當霍坦絲聯絡上她時,她先矢口否認,接著忽然想起什麼,罪惡感、羞愧湧上心頭。曾經拋下自己的骨肉就是她不可告人的秘密。不說出秘密,是希望保有客體對自己的愛。辛西亞陷入了深深的自責與恐懼,擔心家人無法接受霍坦絲的存在。
但在她認識霍坦絲之後,實際上生命似乎變得輕快一點。
辛西亞和羅珊衝突超多,這時忽然出現一個可以讓她引以為傲的好女兒,她獲得了和諧親近的母女關係,但同時亦運用合理化來自我說服,例如「沒有我,你活得更好……當初我的選擇是對的」。不過對一個16歲未婚懷孕的少女來說,送養或許真的是唯一可行的選項。
電影的高潮發生在慶祝羅珊21歲生日的家庭聚會上,隨著真相被揭露,家庭成員之間的壓抑情感和矛盾被徹底引爆。

秘密的心理意涵
傳統上精神分析就是一套關於祕密的臨床設置。伊底帕斯乃受到身世秘密的詛咒,而診間患者的精神症狀,像極了遮蔽潛意識祕密的謊言。那些我們做過卻不記得的夢、記得卻不想跟人說的夢、帶來快感卻必須隱藏的欲望,都是秘密。我們都是保守秘密的人,同時也是遭到某個秘密流放之人。
看完電影,我思考秘密的本質,是否也包括「無法被究極揭露」?即便我們想對誰分享一些秘密,但在那之後可能還是藏著某些更難以啟齒的部分,或是連自己也想不透的部分。個案對著分析治療師努力說自己的夢,但無法用語言描述的部分、忘記的部分都比講出來的部分多很多。電影中霍坦絲想知道父親是誰,但辛西亞始終無法說出口,只是一邊說抱歉、一邊說有難言之隱。
在這種關口,比較成熟的做法是尊重對方的困難感受,幫對方留個餘地,就像電影呈現的那樣,毋須窮追不捨。
在成長過程中,秘密的存在關係著主體性及自我認同的建構,是一種發展成就,代表分離與自主的里程碑。小孩會發現大人有秘密,而身體產生的性興奮當然也是祕密。
將秘密分享給他人知曉,彷彿代表著送人一個禮物,是一種愛的分享。
但是,祕密原本只屬於自己,揭露之後就不再是這樣,這過程必然同時帶有被迫害的恐懼,特別是要說出令人羞恥的過往,就會擔心別人怎麼看[1]。
而保守秘密,像是擁有一個別人沒有的珍奇物件,因為「不給你」而將對方排除在外,主體因此洋洋得意,這是肛門期特質的展現,也是某種自戀的表徵。以電影為例,辛西亞打扮好要出門,羅珊問「你要去哪裡」,辛西亞不正面回答,反而說「平常妳去哪也不讓我知道」。秘密成為一個反擊的武器。
如果把遭受過的創傷當作秘密,它極可能以一種隱而未顯的方式,在代跟代之間傳遞,成為某種「育嬰室的幽靈」。例如,辛西亞絕口不提曾經送養嬰兒這件事,但罪惡感、羞愧感、匱乏感會影響其情緒,這影響到她教養小孩的方式,牽連到羅珊的心智化能力。上述影響發生在潛意識的層次,辛西亞在意識上認為自己勞心勞力帶大小孩,這當然也是不爭的事實,但對小孩情緒發展的影響是她所無法覺察的。
片中還有一個遍在的秘密,那就是每個人心中都隱藏著嫉妒的感覺。辛西亞嫉妒莫妮卡有個好老公、有豪宅;莫妮卡嫉妒辛西亞有小孩,且不只一個;莫里斯或許嫉妒大家都可以表露情緒,只有他不行;而霍坦絲眼看羅珊的生日得到那麼多祝福與禮物,自己的生日卻無人知曉,她的嫉妒心讓她激動到必須去洗手間躲一下。

結語:你會想念你從未擁有的事物嗎?
《秘密與謊言》以其寫實的敘事風格和細膩的角色刻畫而著稱。影片探討了家庭中未解決的情感創傷,並呈現了種族和階級差異對人際關係的影響。它強調真相的重要性,同時也展現了坦誠溝通如何促進治癒與和解。唯有當我們開始緩慢而痛苦地拼湊過往被生活掩埋的破碎歷史,並且承認這些祕密在人際之間造成了痛苦,生命才可能繼續往前。
莫妮卡:「你不會想念你從未擁有的事物吧。」
莫里斯反問:「不會嗎?」
會的。
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師的答案,一定是會的。
人會想像、會觀察、會做夢。人未必總是從經驗中學習,卻很容易掉入想像的黑洞,想像自己有多匱乏,想念自己不曾有過的理想愛情,想念自己沒有的名牌包或名車,無限迴旋而痛苦著。
這些想像的缺憾,正是我們心底秘密的一部分啊。
或許這是上帝當初設計人類的小小錯誤,但這樣的不完美,也讓我們和AI機器人迥然不同,不是嗎?
[1] Sanz, M. C. (2020) Secrets and Lies. Revue Roumaine de Psychanalyse 13:5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