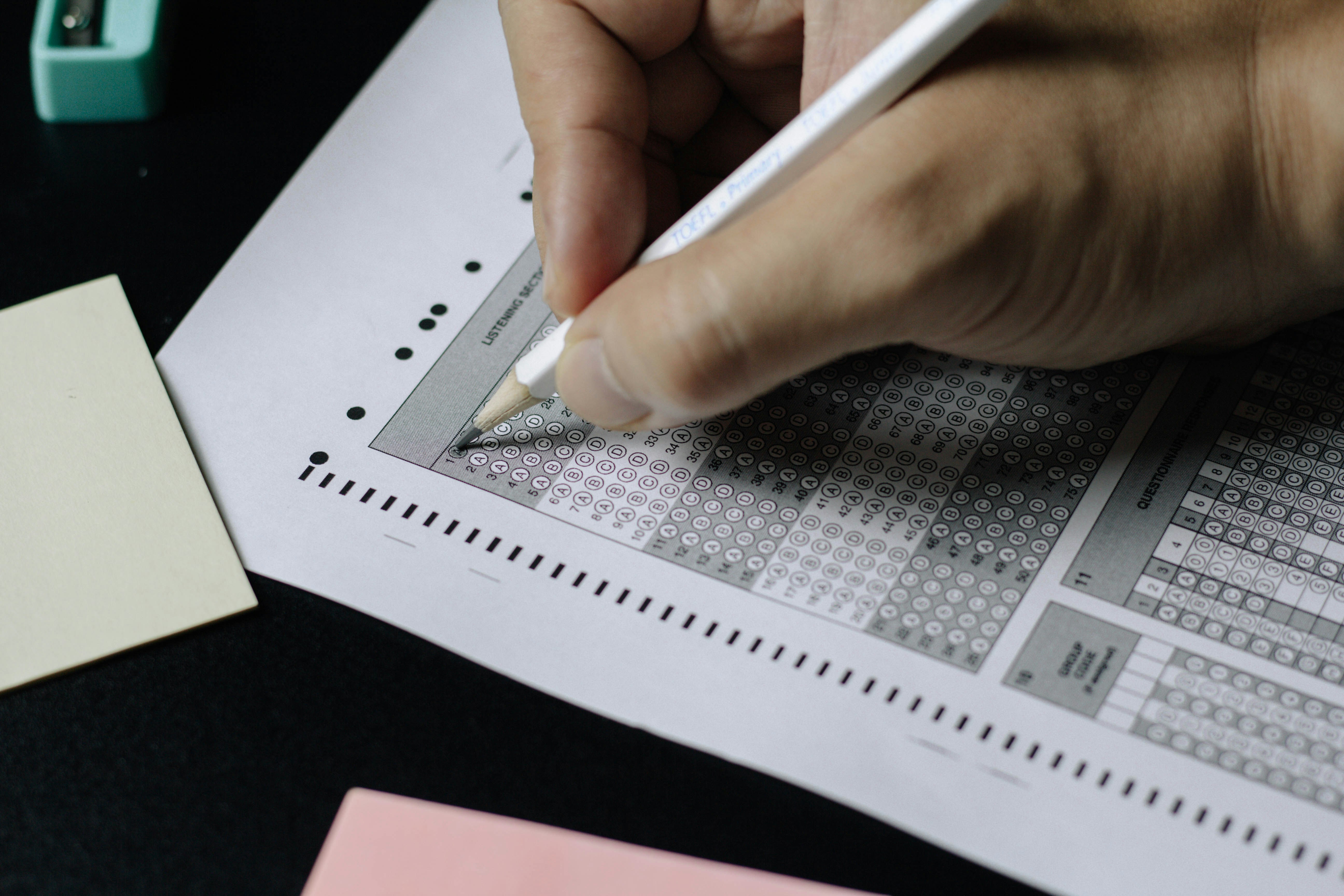《魷魚遊戲》作為一部充滿象徵與極端設定的影集,其實觸及了許多深層的社會哲學問題。若從尼采的思想出發,我們會發現這部作品不僅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正義,更以一種極端寫實的手法,揭露了民主機制的虛假平等與菁英主義的內在矛盾。
一、投票制度的假象:民主的虛偽公平
《魷魚遊戲》中的「投票離開機制」乍看之下體現了民主價值:每個人一票,尊重多數,決定集體命運。但尼采會指出,這正是一種深層的諷刺。虛假的平等:投票表面上人人平等,實則掩蓋了個體在能力、判斷、意志強度上的差異。這種形式民主,其實是平均化的暴政。
平庸的勝利:投票結果多由恐懼與本能主導,而非來自理性的深思熟慮。於是,常常是迎合群眾、操弄情緒者獲勝,真正有判斷力的個體反而處於邊緣。
道德的奴役:劇中角色常被迫在既有道德框架下掙扎,例如是否犧牲他人求生,但這些道德規則本身就是制度設計的一部分。換言之,他們的掙扎並非真正自由,而是被制約的選擇。
這正呼應尼采對「畜群道德」(Herd Morality)的批判。他認為,現代社會普遍奉行的道德其實是弱者對強者的報復,是出於怨恨(ressentiment)而生的價值顛倒。
二、菁英與創造:為何「超人」缺席?
尼采強調,「真正的價值不是來自群眾的同意,而是來自少數人的創造」。這種創造不是掌權或控制他人,而是對生命的重新詮釋與積極肯定。
然而,《魷魚遊戲》中我們看到的卻是:
創造力的缺席:所有參賽者都只能在遊戲規則下求生,沒有人真正質疑或超越這套體系。這象徵現代社會中制度化對想像力的抹殺。
超人的缺席:在尼采的構想中,應有一位「超人」(Übermensch)能跳脫善惡框架、自我立法、自我實現。但即使是主角基勳,在經歷血與火的洗禮後,仍然被困於道德與復仇的二元中,無法真正進行價值重估。
墮落的權力意志:遊戲設計者與觀賞的VIP群體自認為是掌控者,但他們的權力是以他人痛苦為娛樂,是一種扭曲的權力意志,遠離尼采所主張的「創造性權力」。
三、真假菁英的辨證:尼采菁英主義的反思
在這裡,我們需進一步反思:尼采所推崇的「卓越個體」是否總是善的?或是否可能淪為剝削與操控的工具?
真假菁英的辨識問題:劇中的VIP與管理者自認為站在文明與娛樂的巔峰,但其所謂「菁英地位」卻建立在血腥與剝奪之上。這種菁英,是否只是一種墮落的優越感?
創造的方向性問題:創造並不等同於善。尼采強調價值的重估,但他未必提供倫理上的準則。那麼,如果一位所謂的「超人」創造的價值建立在他人犧牲上,這樣的創造仍有正當性嗎?
這提醒我們:「超人」與「獨裁者」的區別在於是否承擔創造所帶來的責任與後果,而不僅僅是破壞與顛覆。
四、超越二元對立:制度與人性的深層張力
或許,《魷魚遊戲》最具哲學深度之處,不是對民主或菁英主義的簡單批判,而是揭露了這兩者的共通陷阱與相互依賴性:
權力的腐化本質:無論是群眾主導還是少數菁英掌權,一旦制度無法自我反省與修正,便會走向暴力與非人化。
人性的雙重性:人既有創造的衝動,也有毀滅的傾向。制度無法消除人性陰影,只能壓制或引導。
創造的集體性可能:或許我們需要的不是孤獨的「超人」,而是一種由覺醒個體組成的創造共同體——一種介於民主與菁英之間的中道形式:既維護個體潛能,也守住制度公義。
結語:我們能否在制度中重建價值?
《魷魚遊戲》最終沒有給出明確的解答,而是丟出一個沉重的問題:我們究竟是在制度中求生?還是願意承擔創造價值的風險?
尼采對民主的批判,不必然等於對自由的否定;而菁英主義的呼籲,也不必等於對大眾的鄙視。重點不在於選邊站,而在於我們是否真正理解「人是價值的創造者,而非制度的產物」這句話背後的代價與責任。
在一個高度制度化、極度媒體化的世界裡,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制度改革或英雄出現,而是對人性本質與價值生成的哲學重構。這或許才是《魷魚遊戲》真正的當代表述:制度不會先改變,除非人願意承擔自由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