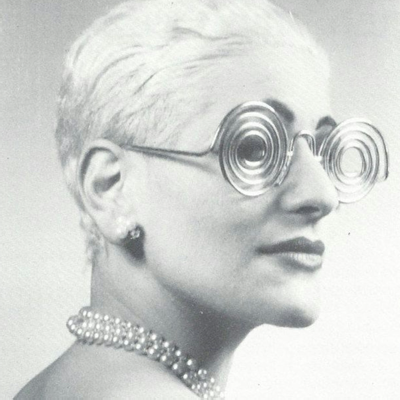今年,自初夏的薰風到仲秋的襖熱,幾場名畫展如向日葵在台北大都會綻放。我化身為一隻尋蜜的蜂,對畫作的讚嘆,化為我飽吸的心靈蜜汁。
從故宮北院的「大都會博物館名畫展」到英國光之畫家「威廉·透納」特展,我跟著展開了跨世紀的光影追逐。
透納,把我領到印象派之父──莫內的面前。傳說年輕的莫內一路追逐光。他在羅浮宮看見透納的迷濛:薄霧、落日、色塊輕輕推移。於是,他以更自由的筆觸捕捉瞬間,讓視覺在畫布上跳出一段段即興的芭蕾。
印象派的誕生:模糊與自由
印象派的誕生始於他創作《印象,日出》——天光、晨霧與海洋連成一氣,丹紅的太陽凝神於畫布上。前景撐槳的船夫,與遠方模糊的船影相互映照,巧妙地留給觀賞者填補細節的自由。「印象派」之名,因此畫而生。

台北展出的這幅《睡蓮》,屬於莫內晚年的寧靜。水藍的霧氣輕覆整個畫面,荷葉安安穩穩躺在左下方,兩點粉紅是它的呼吸。這份沉靜,不是青年時的炫目,而是歲月沉澱後的自在
美術館一大面牆的復刻畫,放大了池畔與拱橋的風景,色彩飽滿熱鬧,像在平日裡兀自綻放的節慶花火。


睡蓮:觀照自我的倒影
我憶起那段每年盛夏,與好友相約在植物園池畔賞蓮的日子。那時青春的笑鬧,像紅豆牛奶冰一樣冰鎮著暑氣。如今我們各自成家,賞蓮的閒情逸致不再。通訊軟體短短幾字,是各自安好的證明,卻無法承載她先生中風後,她那份走不開的牽掛。
日前再次經過荷花池,荷花不再,倒是幾朵睡蓮歪斜地飄浮在偌大的盆裡。我藉莫內的眼進入畫裡的蓮花池,卻同時感知自己曾經的歲月。一場畫作的夢幻芭蕾舞,真實在我眼前展開。
蓮花總能帶領人明心見性。即使是睡蓮,也能觀照出自我內心的模樣。
這份沉靜,是歲月經由莫內的畫筆,為我們留下的最溫柔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