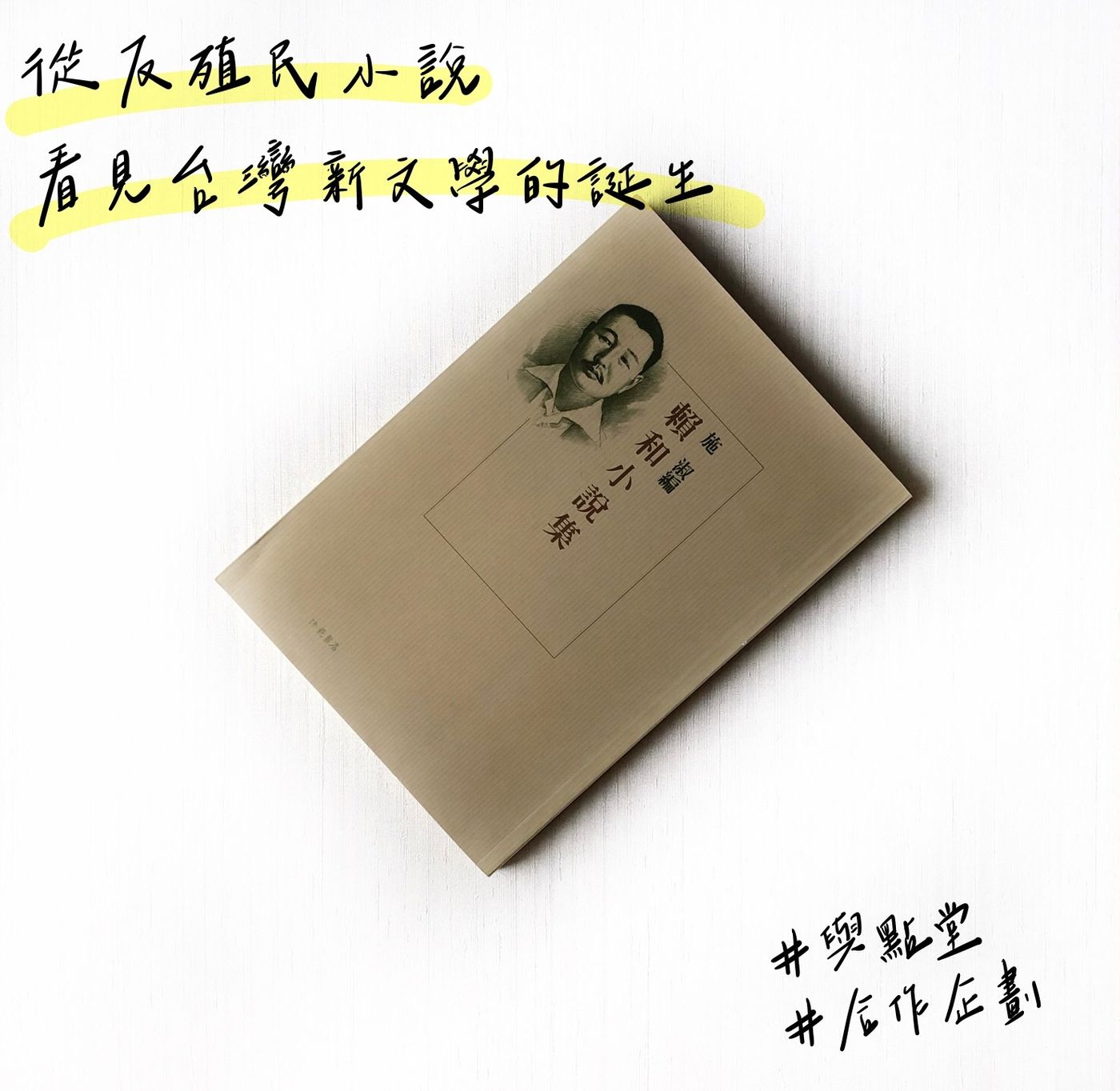1943,「都是無意義的」。
如果臺灣文學史上的〈1943年〉是一篇小說的話,它是從一個極富象徵意義的悲傷場景開始的:1943年1月31日,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領袖賴和逝世了。而就在他逝世前幾天,老朋友楊雲萍剛好才去看他。根據楊雲萍的說法,賴和那天精神很好,他們談了很多關於詩的話題,談了《民俗台灣》上面有趣的文章,還談了魯迅跟連雅堂。本來楊雲萍很擔心他的病況,談著談著竟然也忘了他是個病人。然而,看似心情頗佳的賴和,突然坐起身來,用左手壓著疼痛的心臟,激動地說:
「我們正在進行的新文學運動,都是無意義的。」
這可不是賴和平常的樣子。大家認識的賴和,都是熱情、勇敢、為了理想一往無前的。在他重病的病房裡,楊雲萍聽到這句話,心裡也不可能毫無感觸吧。楊雲萍只能忍住眼淚,急忙地安慰他:「不會的,三、五十年後,人們一定會想起我們的。」
事實上,不管是楊雲萍或賴和本人都心知肚明,這是一句軟弱、沒有任何道理的安慰。因為對臺灣作家來說,日子是越來越難熬了。日本發起的戰爭擴及全亞洲,而且邁入了泥淖般的第六年,仍看不出任何終戰的希望,不管是戰勝還是戰敗。而在越來越緊張的戰爭情勢下,每一個領域都要為日本殖民者的戰爭「協力」,就連看似最沒有「戰力」的作家也無法例外。官員的發言、報紙上的評論,一再催促著作家成為「筆部隊」,此時此刻的言論管制,已經不是「你不可以寫什麼」,而是慢慢轉向「你怎麼可以不寫戰爭」了。戰爭同時成為了殖民政府控制作家的手段與目的,等著臺灣作家的1943年,是一個醒不過來的漫長惡夢。
臺灣人離「建立自己的文學」這個夢想越來越遠了。
當時的文壇上,可以粗略地區分成兩大陣營。一邊是以日本作家西川滿為首,立場親官方、整天喊著要發揚皇民精神的月刊《文藝台灣》;一邊是以臺灣作家張文環為首,消極抵抗官方要求,希望保持自主性的季刊《台灣文學》。不過,兩邊的陣營並不完全依照族群來分布,《文藝台灣》陣營底下有臺灣人龍瑛宗、葉石濤;《台灣文學》陣營也有日本人工藤好美、中山侑、坂口れい子。臺灣文壇並不大,即便表面上看來分屬兩個陣營的作家,私底下可能都有很不錯的關係。本來嘛,作家之間就算立場不合,頂多就是打個筆戰什麼,是可以嚴重到什麼地步?
但《台灣文學》諸君並沒有意識到,有一場「併吞戰」已經悄悄在醞釀了。
名單的政治: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與台灣文化賞
就在賴和逝世的同一天,《文藝臺灣》刊出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特輯」。這個大會舉辦於1942年年底,在東京召集了日本、臺灣、朝鮮、蒙古、滿州、中國(汪精衛政權)各地的作家代表,討論一個十分囉唆的主題:「東亞文學者為完成大東亞戰爭及大東亞共榮圈建設的協力方法」。這顯然不是一個會令被殖民者的臺灣作家興奮的題目,充滿了濃濃的官腔和脅迫感——光是殖民地內的不平等都擺不平了,還共榮勒。
總之,這個特輯收錄了四名臺灣代表的感想,分別是西川滿、濱田隼雄、龍瑛宗和張文環。既然是官方活動,那感想自然也是一堆官腔。有趣的是這個代表團的組合和特輯的發表平台。表面上看起來,代表團是兩個日籍作家、兩個臺籍作家,十分「平等」,但事實上前三位都屬於《文藝台灣》,只有張文環在各種意義上都是「臺灣人代表」。而這個不太有代表性的代表團成果,還必須發表在臺灣作家的陣地《台灣文學》上,這就有一點侵門踏戶的味道了。
1943年的兩集團鬥爭,就從1月31日這個極富象徵意義的日子揭開了序幕。大約一週後的2月6日,主持皇民化運動的官方機構「皇民奉公會」頒布了第一屆的「台灣文化賞」,這個獎當然也是以推進皇民化運動、戰爭協力為宗旨的。第一屆的文學類獎項,就頒給了西川滿的《赤崁記》、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和張文環的〈夜猿〉、〈閹雞〉等作品。
再看一次這個名單,是不是有點眼熟?
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和「台灣文化賞」的名單,我們大致上可以看到日本官方的行事邏輯:無論如何,就是《文藝台灣》陣營的日籍作家為主,然後抓個《台灣文學》陣營的領袖張文環進來陪襯。而對於張文環來說,不管是入選代表團還是入選文化賞,這都是一件尷尬的事:官方授予你榮銜,這似乎是好事;但你接受了榮銜,就必須加入皇民文學的論述體系,你會「被成為」官方代表,而且你還無法拒絕。
在這個尷尬的狀況下,臺北帝國大學的工藤好美教授加入了戰局。工藤好美雖然是日本人,但一直是主張發揚臺灣本位、同情臺灣人處境的,1940年代的許多作家和雜誌都有他在背後支持。他在3月初發表了長篇評論〈台灣文化賞與台灣文學〉,詳細評論了三位得獎作家。表面上看去,他對三位作家都是有褒有貶,但字裡行間卻很清楚傳達出了厚張文環而薄其他兩人的意思。這畫面非常值得玩味:西川滿是文壇裡最大聲支持官方的作家領袖,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則是徹頭徹尾「符合國策」的作品,小說的結尾甚至突兀地插入了「到南方去」的呼聲(呼應官方的「南進政策」),但工藤好美都明確指出他們在文學上有所不足。相反地,作為臺灣最高學術單位的教授,工藤好美反而盛讚作品裡面毫無戰爭氣息、筆觸淡遠、政治立場也與官方隱然有隔的張文環,僅是點綴性地提到一些缺點。
這態度是什麼意思,不用說也很清楚了。
對西川滿等人來說,這是令人尷尬的半個巴掌——說是半個,因為工藤好美確實也沒有什麼會落人口實的離譜言詞,整篇文章看起來頗為溫和;但他又把應該是來「陪榜」的張文環標舉得比「正獎」還高,無論從政治上看、還是從「文壇之內的和氣」來看,譏嘲之意都非常明顯。要怎麼激怒一個得了獎的人呢?很簡單,說你不夠格、或說有人比更夠格就夠了。工藤好美則更進一步:我以一個日本人、臺北帝國大學文學教授的身分來教訓你們這些日本人,有個臺灣人比你們更夠格。
接下來一個月,是1943年罕見的平靜時光,文壇上沒什麼大事發生。但從後見之明看起來,此時此刻的西川滿陣營應該已經開始醞釀下一波反擊了。這波反擊,就是臺灣文學史上著名的「糞寫實主義論戰」。
兩方面的實力懸殊
「糞寫實主義論戰」是一場實力懸殊的論戰,「實力懸殊」有兩層意思:一是從論理的角度來看,西川滿的陣營表現得非常差,主要的幾篇文章發出之後,幾乎是被整個文壇圍剿的狀態,連大多數的日本籍文化人都看不下去;但另一方面,西川滿一方發起的這場論戰,恐怕本來就不是要以論述取勝,而是以此為口實來併吞《台灣文學》陣營,在政治層面上,反而是張文環一方被打得毫無還手之力。
有些論述認為,「糞寫實主義論戰」是從4月濱田隼雄發表〈非文學的感想〉一文開始的。但我們如果依著前面的時間序看來,就會很清楚看到本文其實是對工藤好美的第一招反打。工藤好美的〈台灣文化賞與台灣文學〉也不是無差別亂打,讚美張文環可以,攻打西川滿的力道可不能太重,畢竟後者是領袖級人物,那誰會遭遇最大的批評呢?當然就是年輕、資歷最淺的濱田隼雄,很容易就可以導出他「不夠格」的印象。所以那篇文章的評價,大致就是張文環>西川滿>濱田隼雄。反過來說,《文藝台灣》陣營的反擊,自然也是先派「受了委屈的」年輕作家當作前鋒。
濱田隼雄的〈非文學的感想〉發表於《台灣時報》,是「皇民奉公會」旗下的報紙,「官方背書」的意味很強。這篇文章比工藤好美更直接、強硬,雖然沒有明著說是回應工藤好美,但很有針對性。比如他批評有些作家受到歐美「自然主義」的影響,沒有好好思考戰爭的問題;而「自然主義」,正好就是張文環的正字標記。這種流派認為,作者在寫作時應該完全隱身,不要隨便介入去評價角色;同時,他們也希望可以更真實的描寫人類生活,而不要為了戲劇化去誇張情節,要把觀察到的東西忠實寫下來。因此,這種手法常常帶有一種冷靜的、知性的批判,能夠凸顯角色所面對的社會困境。
用這種手法來寫日治時代,很自然就會看到臺灣人被殖民的困境。也就不意外,為什麼濱田隼雄接著說臺灣作家太過沉溺於「否定性的現實」,專挑現實中醜惡的、不好的一面來寫。這不但是針對張文環,更是針對《台灣文學》和工藤好美的文學理想而來的。《台灣文學》站在臺灣人立場,認為文學必須批判現實,表達臺灣人在殖民生活會遇到的困境,自然看起來都是「否定性的」。
這就給了《文藝台灣》陣營借力打力的縫隙:你看看你,都什麼時節了,還在擾亂民心、說政府壞話?「自然主義」的寫法不鼓吹任何理念,不敲鑼打鼓激勵大家加入大東亞戰爭,是想袖手旁觀嗎?
雖然矛頭明確,但這畢竟只是一篇普通的文章,臺灣作家的文學活動還是如常運轉。4月28日,《台灣文學》策劃了賴和的紀念特輯,邀請朱點人、楊逵等作家撰文,回憶了賴和在臺灣新文學運動草創期的貢獻。其中,朱點人還提出了建議,希望能出版賴和的文學全集,以及創設「懶雲紀念文學獎」。可想而知,如果真有這麼一個文學獎,那必然會與皇民奉公會所辦的獎有完全不同的標準吧。
但這個願望並沒有實現。三天之後的5月1日,西川滿所主導的「台灣文藝家協會」改組,從一個民間的組織,搖身變為「皇民奉公會」旗下的「台灣文學奉公會」。這一改組,等於是讓西川滿瞬間「升官」了,從一個民間文學社團的領導者變成了全島文學體制的領導者。而也在這一天,新一期的《文藝台灣》出刊了,西川滿在該刊中發表了〈文藝時評〉一文,激烈地批評臺灣作家寫的是「糞寫實主義」:
大體上,向來構成臺灣文學主流的「糞寫實主義」,全都是明治以降傳入日本的歐美文學的手法,這種文學,是一點也引不起喜愛櫻花的我們日本人的共鳴的。這「糞寫實主義」,如果有一點膚淺的人道主義,那也還好,然而,它低俗不堪的問題,再加上毫無批判性的生活描寫,可以說絲毫沒有日本的傳統。[底線處為筆者所加]
注意,他說什麼東西是「糞寫實主義」呢?是以「歐美文學的手法」,「毫無批判性的生活描寫」。
嗯,不就是在講我們的老朋友張文環,和剛剛提到的「自然主義」嗎。
所以,從濱田隼雄到西川滿,這兩篇的論調基本上是一樣的。西川滿此文唯一的創意,就是用大便來罵對手,用「糞寫實主義」取代濱田隼雄文謅謅的「否定性的現實」。這樣的罵戰水準,即便發生在網路鄉民之間都會引人恥笑了,更何況是堂堂《文藝台灣》的主編。因此,該文一出之後,不分臺籍、日籍,大量的作家一齊出手批駁西川滿,參戰者至少就有世外民(邱永漢)、吳新榮、伊東亮(楊逵)。除了正面交鋒的,也有些作家會在主題無關於「糞寫實主義」的文章裡面找地方偷酸西川滿,如寶泉坊隆一、垣之外、辻義男等。而在另外一方,除了濱田隼雄、葉石濤之外,基本上沒有人公開支持西川滿的說法,就連最傾向皇民化的評論者也只能重申官方論述,很少人願意去淌這攤混水。
有趣的是,在此次論戰中寫了〈給世外民的公開信〉一文,完全擁護西川滿論調的少年葉石濤,正是西川滿今年才收的「徒弟」。這位徒弟在幾個月前,也曾投稿給《台灣文學》,但被退稿。他因此覺得自己跟張文環等人的路線不合,改為投稿《文藝台灣》,因而加入了西川滿陣營。當他「代師出征」時,《台灣文學》諸君想必哭笑不得吧,誰也沒想到幾個月前退稿的「果報」這麼快就來了。而更耐人尋味的是,葉石濤晚年自述:當年的〈給世外民的公開信〉不是他寫的,是西川滿自己寫,掛葉石濤投書的。由於自述時西川滿已經逝世,死無對證,因此我們無法證明此事真偽。但如果是真的,那就代表——
西川滿當時還真的沒什麼盟友了。
亮出併吞戰的底牌
〈文藝時評〉這篇文章在當時和未來,都給西川滿留下了無盡的罵名。但我們重新檢視時間點,就會發現「論戰」並沒有那麼單純:西川滿在自己主導的《文藝台灣》發表文章,是可以控制時間的;西川滿也一定會提早知道「台灣文藝家協會」要改組為「台灣文學奉公會」。
因此我認為,這兩件事湊在同一天,形成的是一個「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態勢。從一開始,「糞寫實主義論戰」就不是來跟你研討自然主義或日本文學的,而是進行一連串「以政逼文」的操作:先扣你政治的帽子,取得官方的大義名分、形成論述之後,再用這個說法把《台灣文學》陣營整個併吞掉。
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就能看到1943年下半年綿密的攻勢是指向什麼目標了。7月底,伊東亮發表了〈擁護糞寫實主義〉 ,此文巧妙地生出了一套說法,將「描寫臺灣的現實」與「體會日本精神」結合起來,以此反駁了西川滿陣營。在這篇文章中,伊東亮舉了坂口れい子和立石鐵臣兩人的文章當作佐證,也是聰明的做法——一來是用日本人的案例,顯示自己沒有臺日對抗之心;二是選擇了立場相近的日本文人,隱微地表達了自己的意志。
然而,這種字裡行間的小巧騰挪,終究是敵不過政治力量的粗暴介入。8月,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召開,這一次的口號比上一次更激進了,變成了「決戰精神昂揚、擊滅美英文化、擁立共榮圈文化」。也就在這段期間,本來屬於《文藝台灣》一員的臺灣作家龍瑛宗辭退了該社同仁的位置,轉而投稿給《台灣文學》,這樣的人事變動,多少也反應了「決戰」態勢底下,西川滿所主持的《文藝台灣》是怎樣嚴峻而令臺籍作家窒息的氛圍。
而這一次的大會距離上一次只有九個月,顯示官方催促作家加入戰線的節奏已經全面加速了。沒想到短短三個月後的11月,西川滿主導的「台灣文學奉公會」竟然再次召開了一個大型會議,這次叫做「台灣決戰文學會議」。官方把用詞從「戰爭」、「協力」這些詞升級到「決戰」,這是催促到不能再催促的意思了。而就在這個會議上,西川滿提出了非常陰毒的提案,他稱之為〈文藝雜誌的戰鬥配置〉:
如今以處於決戰的態勢之下,對於那些玩票性質的,或以玩樂心態寫出來的自我安慰式的文學作品,今後已不能再容許它們的出現。必須讓文學發揮思想戰砲彈的偉大作用,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
在此我建議,應該由臺灣文學奉公會來編輯一本,能反應今天諸位文學人集結於此所發表的崇高理念,並集結了整體力量的強而有力的雜誌,以作為今天會議的一個成果展現。[......]但是在今日,要由文學奉公會發行一部新雜誌,這在出版管制之下仍是甚為困難的一件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唯有靠我們這些會員們把正在發行中的雜誌獻給奉公會,以這些篇幅的實績做基礎發行新的機關誌,除此之外別無他法。於是,我們文藝台灣社全體同仁決定拋磚引玉,首先將《文藝台灣》獻給台灣文學奉公會。容我說一點心聲,《文藝台灣》現在總共發行了7卷37期,老實說,雖然我個人非常的珍惜,但我願以這次的會議為契機,拋棄所謂「小我」,希望能做到滅私奉公。[底線處為筆者所加]
這招既狠又準,在「台灣決戰文學會議」猝然提出,使得與會的《台灣文學》諸君全部措手不及。〈文藝雜誌的戰鬥配置〉僅千餘字,但全文的謀畫非常綿密。先從這大半年論戰烘托出來的「戰爭協力」氛圍起手,以「決戰」的急迫感,要剔除所有不合官方需求的作品,「不能再容許它們的出現」。接下來,西川滿提出要讓「台灣文學奉公會」發行一本機關誌,這聽起來順理成章,但雜誌沒辦法說辦就辦啊,怎麼辦呢?於是話鋒一轉,提出要「獻上《文藝台灣》給台灣文學奉公會」的說法,並且以「拋磚以玉」一詞暗示其他人也應該跟進,否則就是缺乏「滅私奉公」的精神了。
西川滿不愧是掌握臺灣文壇半邊天領袖級人物,並不是只會用大便罵人而已。這套組合拳是一箭多雕,穩賺不賠:一來首先對政府表達忠誠,先馳得點;二來把自己的雜誌獻給自己主導的組織,西川滿根本沒有任何損失;三來「獻上」雜誌,就可以先作一個姿態去脅迫其他雜誌屈從(當然主要是《台灣文學》啦不然還有誰),為官方消滅不聽話的作家陣營;四來由自己發動這個提案,往後再加入的所有雜誌都等於是進入西川滿的主場了,拿什麼跟他鬥?
諂媚政府、消滅對手、擴張勢力——還有比這更好的買賣的嗎?
於是,長達三年多的《文藝台灣》、《台灣文學》兩大陣營對立的態勢,就在1943年年底畫下了句點。《台灣文學》於12月25日出版了終刊號,《文藝台灣》則在隔年的1月1日終刊號,五個月後通通合併改組為《台灣文藝》。

事已至此,我們才看懂了這件事的全貌:從一開始,這就不是一場論戰,而是一場併吞戰。是殖民政府以親官方陣營的作家為打手,掀起論戰、把臺灣作家逼入必須澄清「忠誠度」的角落後,再突擊、消滅民間陣營的一場戰爭。這也是官方巧妙利用文壇內部的矛盾來「統一」文壇的故事。
於是,在終刊號的《台灣文學》中,刊出了〈記「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一文。文章的最後引述了會議的「決議文」,決議文的最後一段寫著:
我等乃是為追求大東亞戰爭之勝利,而以筆代劍,奮起抗敵之戰士。我等歃血為盟之同志,以皇道精神之神髓為本,奉行文學經國之大志,破除任何險阻,在此團結一致,竭盡全力建設臺灣文學。
「破除任何險阻」
「在此團結一致」
台灣人能不被團結嗎?那可就會成為被破除的險阻了。
而這個時候的西川滿,則已漸漸不是當年那個熱愛媽祖意象、對臺灣文化充滿浪漫想像的文藝青年了。他和張文環分歧,本來或許還只是文學路線之爭,但超過了一個臨界點之後,有些事就再也無法回頭了。
1994,「人們一定會想起我們的」
走到了1943年的盡頭,臺灣作家眼前展開的是一幅完全絕望的圖景。戰爭不知何時才會結束,日本殖民統治更像是沒有終期一樣。楊雲萍從賴和口中聽到的那句話,而今看來似乎一語成讖了:
「我們正在進行的新文學運動,都是無意義的。」
什麼都要沒有了。
然而,歷史並沒有在1943年停下來。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殖民統治突然結束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臺灣人開始意識到自己是不是又落入了另一個殖民者手中。1949年,國民政府迫遷來臺,隨之開始了漫長的戒嚴時期和白色恐怖。在這之後的三十多年,「臺灣文學」四個字成為禁忌,誰要是敢提起,那就要冒著被特務盯上的風險。這使得日治時代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完全被隱沒,像是被冰封起來一樣。這樣的壓抑至少要等到1987年解嚴之後,才有一點冰雪消融的跡象。
而這一切,賴和都沒有看到。
張文環看到了。龍瑛宗看到了。葉石濤看到了。楊逵看到了。他們之中有的人中途離世了,沒能看完整齣劇。而活下來的人,在冰層裡看著外面的世界,懷抱著不為人知的文學記憶。
直到1994年。
那一年的12月27日,在清華大學辦了一個研討會。這個研討會的名字有點饒舌,但沒有日治時代的那幾個「文學者大會」那麼囉唆。它叫做「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在這個會議當中,長年研究臺灣文學的各路學者進行了一次大型火力展示,向外界證明了「臺灣文學」這個領域有足以自立的學術價值。也在這一次研討會中,奠定了往後成立「臺灣文學研究所、臺灣文學系」的基礎,使得臺灣的文學有了自己的學術建制。
而這個會議,就是以賴和為名的。
距離那令人絕望的1943年,差不多就是半世紀。
楊雲萍安慰賴和的那句軟弱的話,竟然真的應驗了:「不會的,三、五十年後,人們一定會想起我們的。」
而1994年的楊雲萍,已經走到了人生中的最後幾年了。但他沒有錯過這個會議。八十八歲的他,當時就坐在台下,聽著「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的學者們輪番討論他年輕時熱烈地活過的時代。
現在開始,將不只有他們幾個人記得這些事了。
★作者簡介
朱宥勳 1988年生,畢業於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台積電青年文學獎。已出版個人小說集《誤遞》、《堊觀》,評論散文集《學校不敢教的小說》、《只要出問題,小說都能搞定》,長篇小說《暗影》,與黃崇凱共同主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目前於「深崛萌」擔任高中國文課本執行主編,並於鳴人堂、蘋果日報、商周網站、想想論壇等媒體開設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