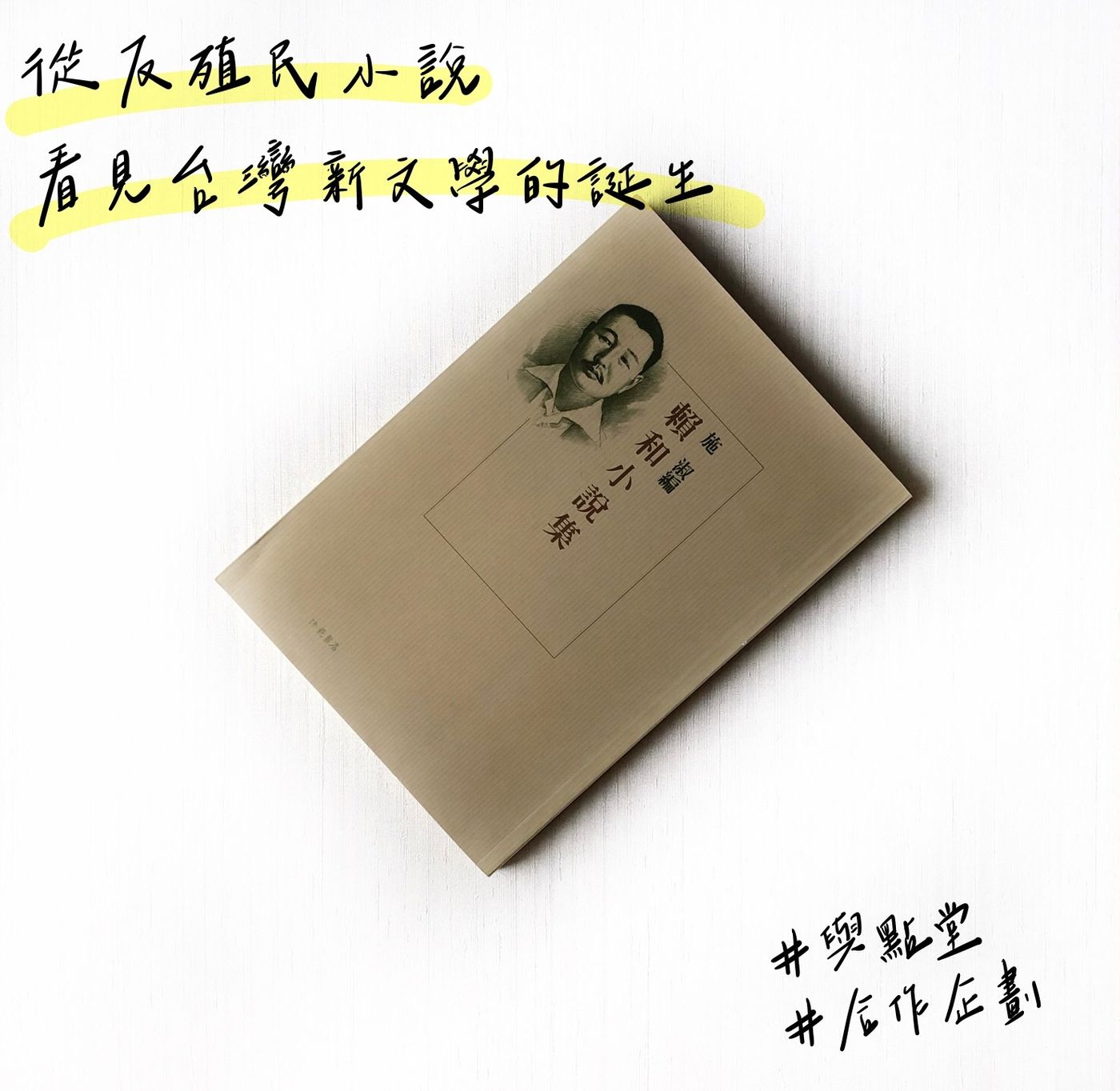2015/001《前山報》
◎ 陳冠文
月前,應林語堂故居所發刊《前山報》之邀約,著手為賴和紀念館來寫一篇專訪,作為一個老彰化人,重新面對賴和這麼一位台灣新文學的重要人物,是日,踏過八卦山上的台灣文學步道,最後在舊市區中正路上一棟掛著「全國電子」招牌的公寓大廈找到賴和紀念館,不禁百感交集,雖然賴和誕生來到這片土地已經超過一百年,他的靈魂卻彷彿隨著老彰化沉沉睡去。

搭乘電梯上了四樓,按了電鈴才得入內參觀,映入眼簾是牆上掛著七個大字「勇士當為義鬥爭」,心頭微微一震,作為國內完整收藏賴和的遺物、藏書、字畫及相關文獻資料的地方,在有限資源下,仍盡力提供個人與團體預約導覽。門口邊陳列著「賴和手稿」的櫃子,放置他與同學、友人的書信和課堂筆記,一角處可見賴和銅像,分別出自林慶祥老師與王英信老師的手筆,一則飛揚挺拔,一則沉穩內斂。雕像旁邊放了張診療椅。
除了賴和本人,「賴和紀念館」也得到同時期作家楊守愚的兒子楊洽人的授權,展示部分的手稿,供讀者來認識。
談談賴和,賴和出生於1894年,死於1943年,一生幾乎橫跨整個日據時期,除了自大正六年(1917)從台北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回到彰化開設「賴和醫館」開始專職開業醫師的生涯外,主要活動是參加臺灣文化、台灣事務會與一些政治活動,後人認識賴和,往往因為他在台灣新文學運動上的貢獻。
縱觀賴和一生,自幼習漢文,1921年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並當選為理事;1923年因「治警事件」初次入獄;1925年開始積極投入台灣新文學的創作,於1927年起擔任《台灣民報》文藝及新詩專欄主編;1941年珠港事變當天,再度被拘入獄,後因病重出獄,於1943年逝世,行年五十。其間經歷20年代的摸索語言與文學形式的啟蒙階段,3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與聯合陣線文化抗爭,以及1937年爆發盧溝橋事變之後的皇民運動。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幸好館內還細心保存著一些藏書,此為當時為推廣台灣文化協會啟蒙運動的理念,賴和在診所旁邊附設了一間閱覽室,提供民眾自由使用,其中可見當時台灣知識分子努力和世界接軌,人們普遍以日本與中國為窗口,來接觸歐美、俄國的民主思潮和左翼思想。另外,館內亦陳列日據時代出版的報紙、雜誌的復刻本,如《臺灣新文學雜誌叢刊》、《文藝臺灣》、《臺灣民報》。
從賴和作品,我們可輕易發現自我認同的困境,例如《一桿秤仔》、《可憐她死了》,藉由死亡來表現台灣人民的生存處境;例如《辱》,統治者的法律摧殘侮辱市民的憤恨,《豐作》則是警察意象貫穿於其中;例如《鬥熱鬧》,赤裸地揭露舊式封建社會當中傳統階級仕紳的性格;例如《一個同志的批信》、《獄中日記》,更可以窺見啟蒙思想的徬徨掙扎。
殖民地最強烈的特色,是讓個人失去自己的歷史和語言。作為一個日本政權培育的本土醫生,賴和一方面感嘆殖民體制帶來的現代化;另一方面,這種思想的啟蒙亦代表一種反抗。同為一個殖民地的知識份子,即便失去了自己的發言權,他仍一直在寫自己的東西,來抵抗政治支配下的失憶症及失語症。

這點我們從賴和的文學表現可以一窺端倪,身為弱小民族文學的一環,他一方面以自傳體方式來書寫屬於自己的歷史,一方面運用寫實主義的視角來揭露外在環境的虛妄。同時,他堅持用白話文寫作,把文學運動當成啟蒙運動來推廣,但是困難重重,賴和在二0年代開始創作新文學,故事篇章裡面的對話,得把它修訂成為台灣話,他一生卻始終用漢文寫詩,其內心的糾葛可見一斑。
對大多數橫跨了解嚴前後,居處社會上中年位置的世代而言,去理解這一種源自理性精神而產生的內外矛盾,亦即賴和作品中最重要的現代性特徵,同樣也是在重建自我。特別是台灣社會走過日據殖民時期、戰後的再殖民時期,直至今日進入後殖民時期,轉型正義尚未落實,不同族群之間的歷史記憶卻相互牴觸,在後現代的大旗揮舞下,彷彿自我尚未建立就要被迫瓦解。
從前閱讀台灣文學,總是在悲傷來臨前就被暗示要悲傷,彷彿過去如同千頭萬緒一般地遍尋不著,又在遠處虎視眈眈,緊咬著自己不放,成為一種無根的、陳述自我時頓生的失語困境。要感謝賴和的文學,提供人們在重建歷史記憶時所需要的田野,他的痛苦掙扎,精準地呈現出日本殖民社會下,一個漢族遺民、一個知識份子的心靈狀態。
作家楊守愚的老家即目前彰化民生市場,距離賴和醫館舊址只有一街之遙,過去他經常到賴和家裡借閱書刊雜誌,深夜幫忙賴和主持的《台灣民報》文藝欄校稿的景象,如今已經難以想像,我們只能睹物思人。彰化多年來一直以小鎮的姿態存在,從山上眺望彰化市全景,越過八卦丘陵便是台化遼闊的廠房和煙囪,煙囪總在雨後夕陽下升起紫金色的煙霧,龐雜的建築物籠罩其中,透出無比新鮮的色澤。從賴和、洪醒夫到李昂,無論代表是台灣新文學、鄉土文學還是女性主義,都可發現被社會環境壓抑下,仍掙扎著求生與追尋意義的強韌生命力,在這個逐漸被時代所遺忘的老地方,鳳凰木仍悄悄沿著城市的周邊生長。
因為政治因素,我們在成年後才開始接觸賴和,正如遊子總在離開之後才緩慢拼湊自己的故鄉,每一個曾經背叛自己和故鄉的孩子,都曾徬徨不由自己把握,這是這塊土地留給我的永恆印記,提醒我的存在,不同的是,故鄉始終沒有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