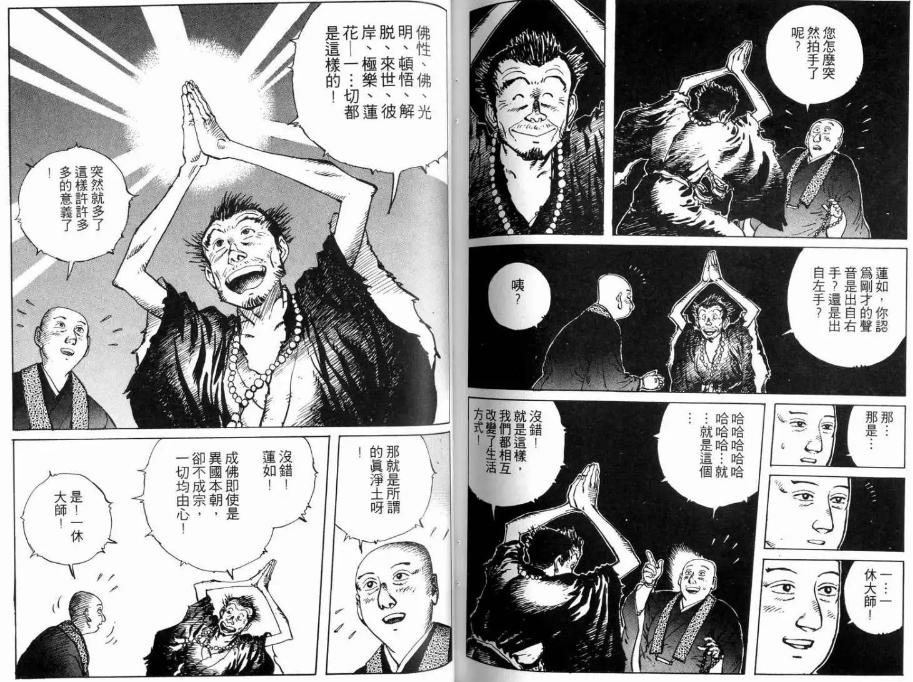我們平常談論慈悲的時候,聯想到的多是道德式的慈悲,並且比較容易跟某些行為連結在一起。最常見的一些對慈悲的認識,像是放生、說好話、做好事等等「正面」的行為。在某個層面上,我們的確可以說這些是慈悲-一種俗民式的慈悲。這類慈悲有時會變成道德式的譴責,比如說「那個人做了那麼多壞事,怎麼不早點去死?」「他殺人越貨,以後一定會下地獄」等等。
不過,若我們繼續看一下慈悲,不讓自己停留在這種與行為或道德牽連的慈悲時,我們會看到一些不同的風景,甚至會看到那些被視作不慈悲的行為,可能也是一種慈悲的展現。
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在他的《不是為了修道》當中,曾經提過四無量心的修持:
- 慈無量心:願一切眾生恆久住於無因之樂
- 悲無量心:願一切眾生遠離諸苦與一切苦之根本因
- 喜無量心:願一切眾生恆久不離無因之樂,遠離一切苦因
- 捨無量心:願一切眾生捨棄一切親疏我敵之別,持根本平等心
當中的悲無量心-祝願一切眾生遠離一切苦的根本因-所蘊含的內涵,包含了對於無常的認識,與持續而不間斷地體認無償。這種修持有時看來會很痛苦,而且殘忍。比如說,這類修持的其中一種方式,可能是觀想他的愛人在他的面前死去,身軀腐爛而化為白骨;或者,可能一名修持者選擇觀想自己所愛的器物破損或壞滅;又或者,這名修持者可能觀想自己正躺在棺材裡,焚毀身體的火從四面八方向著自己燃燒;也或者,觀想整個世界都化成一具一具的白骨,這些白骨都碎壞成段,或灑成灰。
觀想我所愛的人事物,或者我所愛的這具身體毀壞,從這個當下開始敗滅,這是觀想無常的一種方式。
另一種對反於有常的觀點,是祝願我所憎恨或不喜的人,願他們也能得到無因的快樂,並且永離痛苦的根。或者,觀想自己將所有的財物-物質上的、知識上的、精神上的,或者各種想得到或想不到的-全數、無條件地供養給本尊。
當我們開始觀修無常,我們其實就是試著練習用一種比較不忽略實際上可能隨時發生的結果,並且將這種觀點重新納入這個世界。原先的觀點-我們習慣、無感、執著、堅持生活是日復一日的如此這般的這種觀點,其實是我們用一種習慣性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其中蘊藏著許多佛教所謂的貪染(Taṇhā),這是一種大致固定、習慣的堅持「該是如此」,並很常伴隨對於被打擾與變動的厭惡。而貪染時常延伸出八種佛教中所謂的苦-生命的持續焦慮:
- 生老病死苦
- 愛別離苦:與所愛的人、事,或者器物訣別
- 求不得苦:得不到想要得到的
- 怨憎會苦:遇到自己所厭惡的人、事,或者物
佛教的慈悲並不僅止體現在說好話、做好事等形式的好,這是一種道德式的好。如果以道德的參考點來評估,佛教的慈悲還很可能被看作一種反道德的形式。「整天說我會死,你是咒我死是不是?」然而,佛教的慈悲並非道德,也非反道德,而是將道德視作一種暫時性的聚合。
對於無常的最深刻體認,是真的深深的經驗到這個世界不斷在變化-更精確一點說,沒有恆存不變的世界,沒有任何被稱為事物的持續存在,唯一有的只有變化本身不斷地變化著。然而,這樣講或許還太籠統而概念化,因為我們的確有可能一邊說著「只有變化本身在變化」,同時對於自己肉體的整個變化習而不察。
對於變化本身的察覺,我們參考小孩子的眼光-特別是剛出生的嬰兒-會比較容易體會。我們是不是已經習慣了太陽的位置會移動,習慣了風吹過皮膚的感覺,習慣了每一片葉子上的綠都不相同?我們是不是已經習慣了蟬鳴,習慣了鳥叫,習慣了空氣中四面八方的聲音?我們有多久不再對這個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樹梢、花兒、泥土、天空、蝴蝶...-對這整個世界一切的活生生感到驚訝、神奇而感動?我們活在一種固著的、孤獨的殼當中多久?我們有多久沒好好地感受過身體呼吸時,每一寸皮膚、每一個毛孔、每一處骨頭、每一處組織和肌膜的活動?我們有多久把自己視為這個世界以外的一部份?
我們能站、能坐、能看、能聽、能聞、能感受、能被感動與感動,太陽、月亮與星辰持續地活動著、轉動著,這一切當中充滿著奧秘與玄妙,我們忘了這整個大奧秘忘了多久?我們遺落了我們與這一切無窮盡的連結多久?
當我們開始體認無常,我們就是學著體認這個世界的活生生,這兩者其實是一體兩面的,我們透過感覺死亡而知曉了活著,我們透過知覺有限而體驗到在這個當下展現的無限。這是另一種慈悲-一種不是先否認,而是從先試著認識那些被視作黑暗的、不悅的、不喜的、厭煩的事物開始,然後認識這整個繁複的奧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