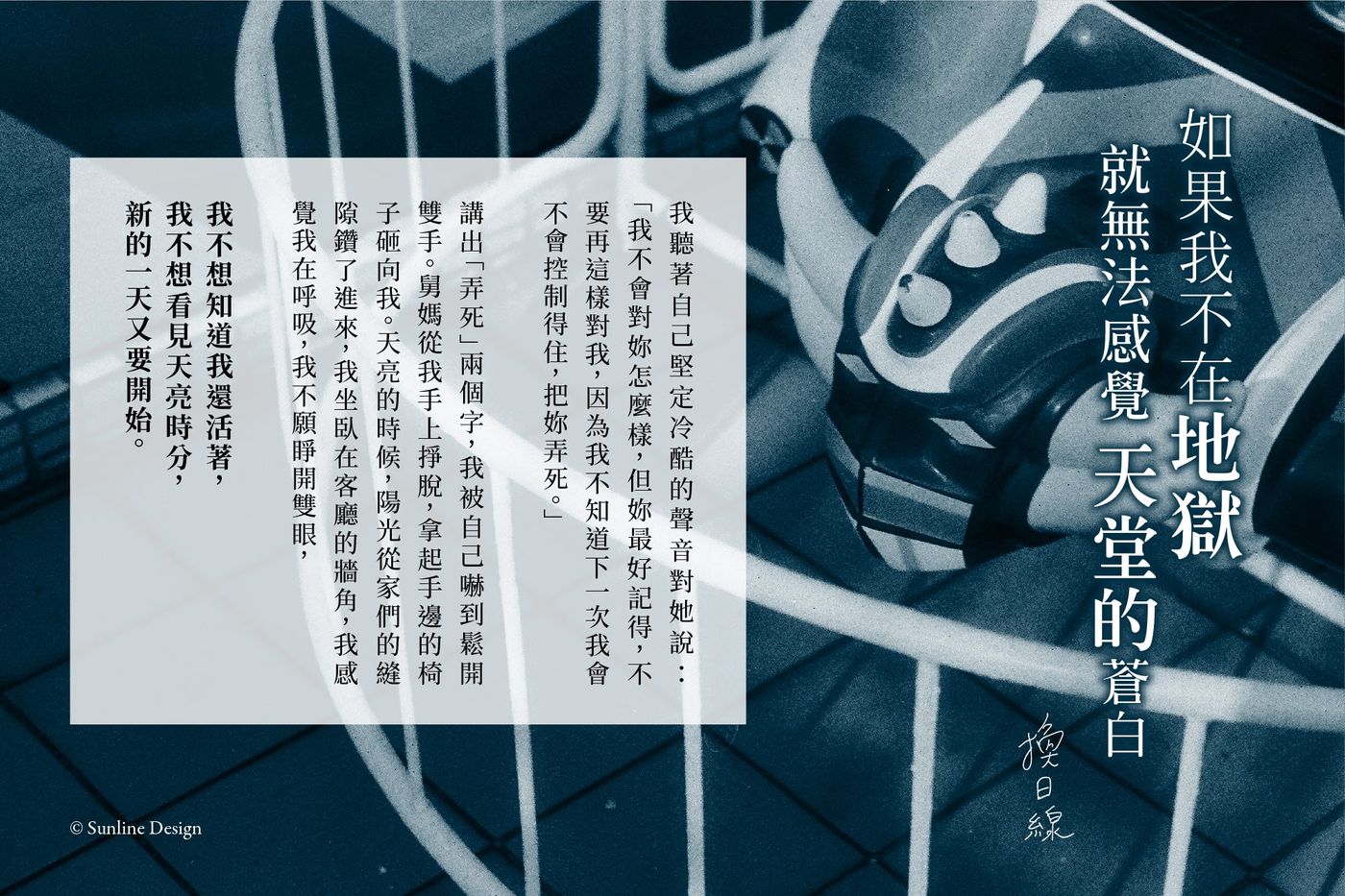為什麼兄弟姊妹必須要和睦相處?說穿了,兄弟姊妹只不過是隨機地被生在同一個家庭裡的陌生人而已吧。而陌生人,當然有的你因為某種機緣,幸運地和他成為了好友,大部分的情況卻是冷漠相待,或互看不順眼,因為種種你沒有和在人生中遇到的每一個人成為朋友的原因。那其中之一,剛好不巧地成為你的兄弟姊妹。來自相同的父母,有相似度極高的基因,那又如何?誰也不能否認,他們與好友的感情,甚至更甚於自己的兄弟姊妹。難道有誰會說,他們之所以和某人成為好友,是因為他們的血緣關係很近嗎?是因為意氣相投吧。
被囚禁的那段日子,我對於巫婆的要求有求必應、百般服從,假裝站在她那一邊,不管是燒柴煮飯或打掃,我都沒有怨言地完成。但我當然也不是呆呆地只是做家事,我趁著這些機會,把糖果屋裡裡外外都摸得一清二楚。
然後,那一天終於來臨了。一早起床巫婆就告訴我,今天是她的生日,她決定要把妹妹烤來吃。當我聽到時,無法掩飾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在巫婆的眼裡看來,也許還會質疑那只是強顏歡笑吧?巫婆打開關著妹妹的籠子時,我就在巫婆痀僂的身軀後,看著淚水已佈滿臉龐的妹妹,不停發著抖,不斷喊著媽媽、媽媽,然後看到我的臉,改叫哥哥、哥哥,但我只是把頭別開。巫婆抓著妹妹的手,把她拉出籠子,妹妹震耳欲聾的哭聲,幾乎要震破糖果屋的屋頂,然後我看著巫婆打開冒著熊熊烈火的火爐,把瘦小的妹妹給丟了進去。
妹妹的哭聲,逐漸淹沒在火焰裡,伴隨著巫婆滿意的表情與淒厲的笑聲,我知道巫婆的注意力暫時不會從火爐中移開了,也似乎忘了我的存在。我馬上跑進巫婆的房間,偷光她的財產,然後盡可能把糖果餅乾往身上塞,推開大門逃出糖果屋,沿著之前在樹上作的記號,穿越森林,回到家裡。
當我終於走到許久不見的大門前,我拿出一塊辣椒餅乾吃下肚(巫婆的最愛,藏在她的床頭櫃裡,不過除了我以外,大概也沒人會去吃吧)。等眼淚被嗆出來後,氣喘吁吁地推開門,看見面容枯槁坐在桌前發呆的爸爸,我邊用哀痛的神情說:「妹妹被……妹妹被巫婆害死了!」邊哭哭啼啼地衝向爸爸的懷抱。
爸爸的臉上頓時露出扭曲的神色,隨即也流下淚來,張開雙手擁抱僅存的孩子,陰暗的房屋頓時被啼哭聲填滿,我隱約聽到爸爸說:「沒事了……沒事了……」殊不知我在爸爸的懷裡,嘴角露出了勝利的微笑。
然而,我所沒有料想到的是,我的微笑,原來有人一直看著。從廚房緩緩走出來的,是我的新媽媽。那個說服爸爸遺棄我們的新媽媽,原來一直都在。她張開雙臂,抱住我和爸爸兩人,一邊說:「回來就好。」卻一邊低下頭,別有用心的看了我一眼。
在與她四目相對的瞬間,我的心好像被雷擊中了一般。不是什麼一見鍾情的母子戀亂倫爛戲碼,而是第一次覺得被人完全看透、第一次與人心靈相通、第一次找到人生的知音,一種完全被理解的感覺。
在那個黑暗與黑暗撞擊的瞬間,我忽然瞭解了。新媽媽內心的黑暗,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是一股不顧一切,甚至不惜犧牲親人或親近的人的生命,也要達成的意志。是一股除了自我,可以將一切捨棄的決心。這一股掏空良心的黑暗漩渦,一直都存在著,從不曾離開過,隨著時間逐漸壯大。
從我有記憶以來,我總是被遺忘的那個孩子,因為媽媽只愛妹妹。她只會說,妹妹年紀小,你要讓她;妹妹不懂事,你要多照顧她。她的目光,總是在妹妹身上;她的笑容,只留給妹妹。她過世的那一天,我十一歲,妹妹五歲。在病榻旁,她握著爸爸的手,說孩子就交給你了,但我實在聽不出來那個「孩子」是不是複數。大概不是吧?她捧著妹妹的臉,說我最親愛的寶貝,對不起,沒有辦法看你長大,再見了,媽媽永遠愛你。然後就斷氣了,一句話也沒有留給我,甚至沒有看我一眼。
那一天之後,我反而像是解脫了一樣,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因為沒有人會再叫我照顧妹妹。爸爸工作忙,什麼事都不管,妹妹從被百般呵護的小公主,變成骯髒的孩子。我一找到機會,就偷打妹妹,她卻像笨蛋一樣,以為我在和她玩。然後爸爸很快就娶了一個新媽媽。新媽媽,我們兩個人她都討厭,但奇怪的是,我反而對她一點敵意也沒有,也許認為這才是真正的一視同仁吧?我故意在她面前欺負妹妹,她也假裝沒看見。
我比較喜歡新媽媽。
當她帶我們到森林裡放生時,我只覺得煩:為什麼我非得和這死丫頭一起被丟在這裡?不過,剩下的就沒什麼好說的了,除了新媽媽,我甚至還該感謝巫婆呢。
就這樣,我和新媽媽之間的那停格一望,成了我們之間永遠的默契。我、新媽媽和爸爸三個人,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