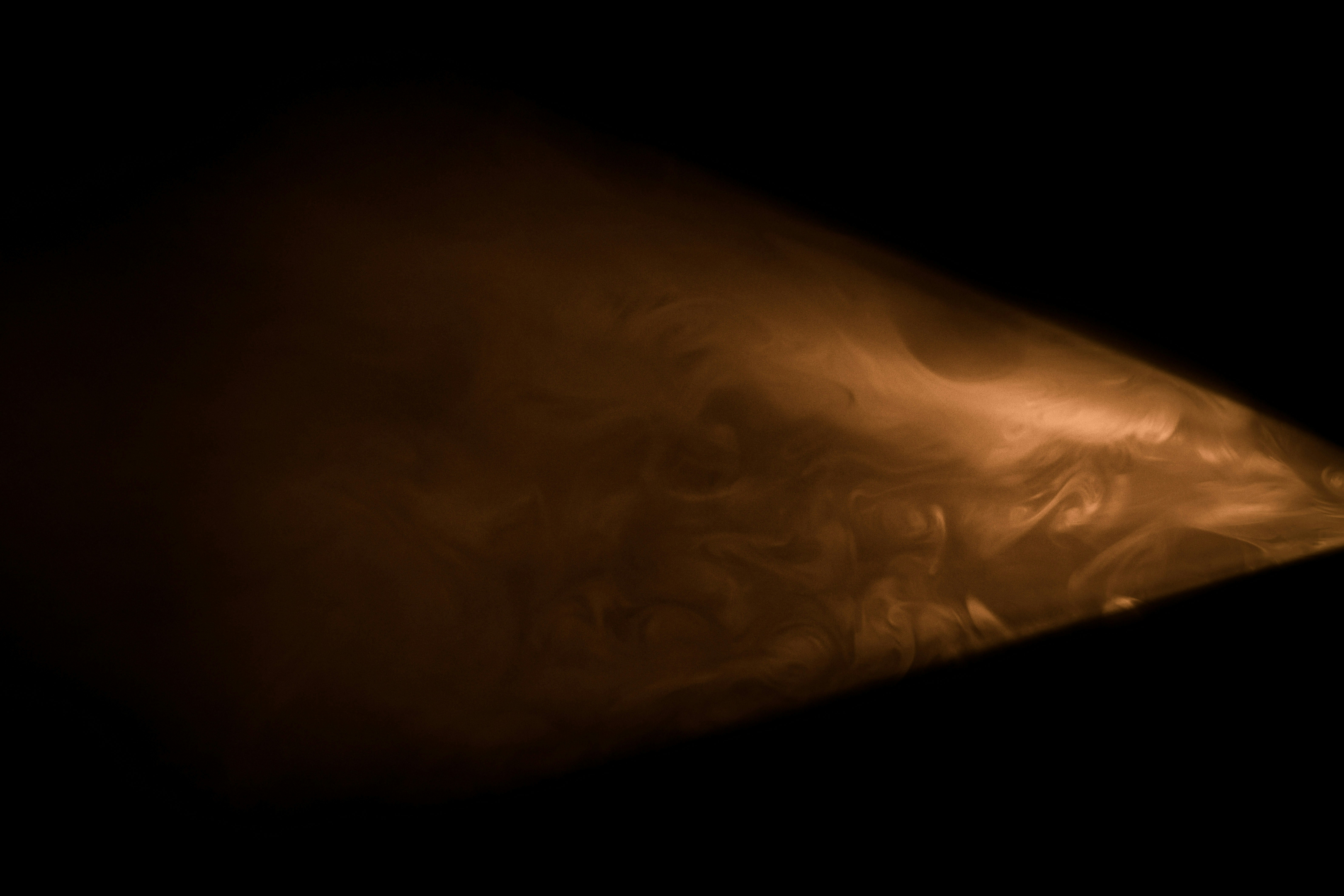《最後的自由時光》懺悔與抉擇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兇手與被被害者,善惡模糊的距離
死刑與廢死之間常被爭論,例如一個人決定人生死如同劊子手和一命換一命之間,各有不同的人以自身的經歷和思考釋出意見。當我們評論一個新聞事件時,那些終究是他人之事時,但如果是親身經歷會不會所得的結果和思考的方向又會有所不同?
《最後的自由時光》是一部在2015年的美國紀實動畫短片,訪談人比爾.巴比特敘述自己哥哥曼尼因一件謀殺案判刑入獄,最後處以死刑。讓比爾思考關於從他發現兄長可能犯案後,在警方、法庭、和他與哥哥之間的過往中,在精神疾病和殺人犯之間,各種回顧與探索自己的認知,當家人成了嫌犯或捲入事件之中時,那種矛盾感讓他陷入深深的懺悔與自責中。
台灣對於精神病患捲入謀殺案或隨機殺人案,其實是不陌生的,例如在台北捷運犯下隨機殺人案的鄭捷,和小燈泡案王景玉殺害女童的事件,都曾有精神疾病問題,而也因曾有過假藉精神病史是圖脫罪的案例,台灣網友常對於又是精神病犯案,從原本對於動機與證據的討論轉變為戲謔嘲諷的口吻看待案情本身。
2018公視影集《我們與惡的距離》與台灣紀錄片《徐自強的練習題》、《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等都在探討關於,精神病患、冤案、與殺人嫌犯的生心理上的認知和雙方家屬對於死刑和家人犯案和被害的各種看法與折磨。
《最後的自由時光》我認為表現的手法很有意思,一來他將原本看似很一般的訪談敘事紀錄電影,加上動畫濾鏡,利用線條勾勒和水彩與寫實背景和平面動畫互相交錯讓觀眾感受在虛實之間的動畫紀實魅力,這點我覺得是本部電影的一到亮點。
外加關於案件的故事本身比起其他未解懸案或是名人犯案等,沒有太多吸睛但這樣的手法反而可以讓人聚焦於想了解比爾他哥哥的人生故事,也讓人可以從這起在眾多案件中找到關於美國對於死刑、精神病患、種族間的各種探討點。
我們可以從故事中看出比爾從一開始對於死刑的支持,到最後因為哥哥曼尼的謀殺案轉變成為猶疑和經歷過各種司法程序後,對於他們對哥哥的指控有所反駁,並且不承認他的兄長有精神病史這件事情,還有全白人的陪審團,與同時出席甲、乙兩方被告提告的證人這點,看得出他的崩潰。
一方面因為他發現哥哥可能是犯人將他交給了警方,但另一方面他其實希望大家了解他哥哥是什麼樣的人,不是只有怪物與殺人犯,而是他眼中那個會陪小孩玩樂、童年與他挖蛤蠣、遭受車禍而腦部受創、軍人退伍後飽受越戰精神創傷所苦的大哥。
這部《最後的自由時光》是描述關於比爾親手將自己的大哥送入監獄後,一方面他認為他哥哥犯錯必須受到法律制裁,但另一方面他無法接受美國的司法因為選局與作秀的形式,把他哥哥當成政治的犧牲品。
例如試圖收回他哥哥越戰應當得到的國家勳章,和不翻閱提出兄長的精神病史,還有受害者心臟病發為主要死因等事實。在比爾心中對於兄長的死刑是有矛盾的,在他本身又是支持死刑之後,兄長的事件,讓他試圖用另外一個觀點去看待死刑與廢死。
但有些意思的是,裡面也稍稍提到關於受害者家屬對於比爾哥哥的看法是不諒解的,這點也能看出關於受害者這方其實有著和兇嫌的家屬有著不同的看法,畢竟他的家人死亡對於是否了解兇手是什麼樣的人,對他來講並非重點,而重點在於法律是否能給予一個讓他們信服的判定。
這部影片雖然獲得許多獎項支持,但回過頭來,他的確一面倒的往廢死、兇手人權等方向引導,雖說比爾的哥哥因退伍軍人創傷症候群被嚇到,但闖入民宅是事實,有攻擊受害者也是事實,故如果從死者那方看來,不管比爾大哥如何可憐都不構成他們的諒解的成分。
原諒是很艱難的決定,而廢死與不廢死在某種意義上為何一直相互拉扯,主要還是因為司法制度與家屬心裡雙方無法有著相對應的補償,但畢竟消逝的是一個人而非冷冰冰的物體,而司法是否有權利要一命換一命當一個跟兇嫌一樣奪取他人性命的兇手,或是死刑能否撫慰受害者的家屬,又是什麼都沒有兩者皆空?這點仍然是廢死與盼望死刑難解之事。
當局外人拍案叫絕一律死刑或有教化可能時,彼此都怕犯錯,怕錯放成千古罪人但也怕冤罪奪取一個無辜的受害者。但終究想要遲來正義的兩方,可能都只是變成法律上的一場審判遊戲。
為什麼會看到廣告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