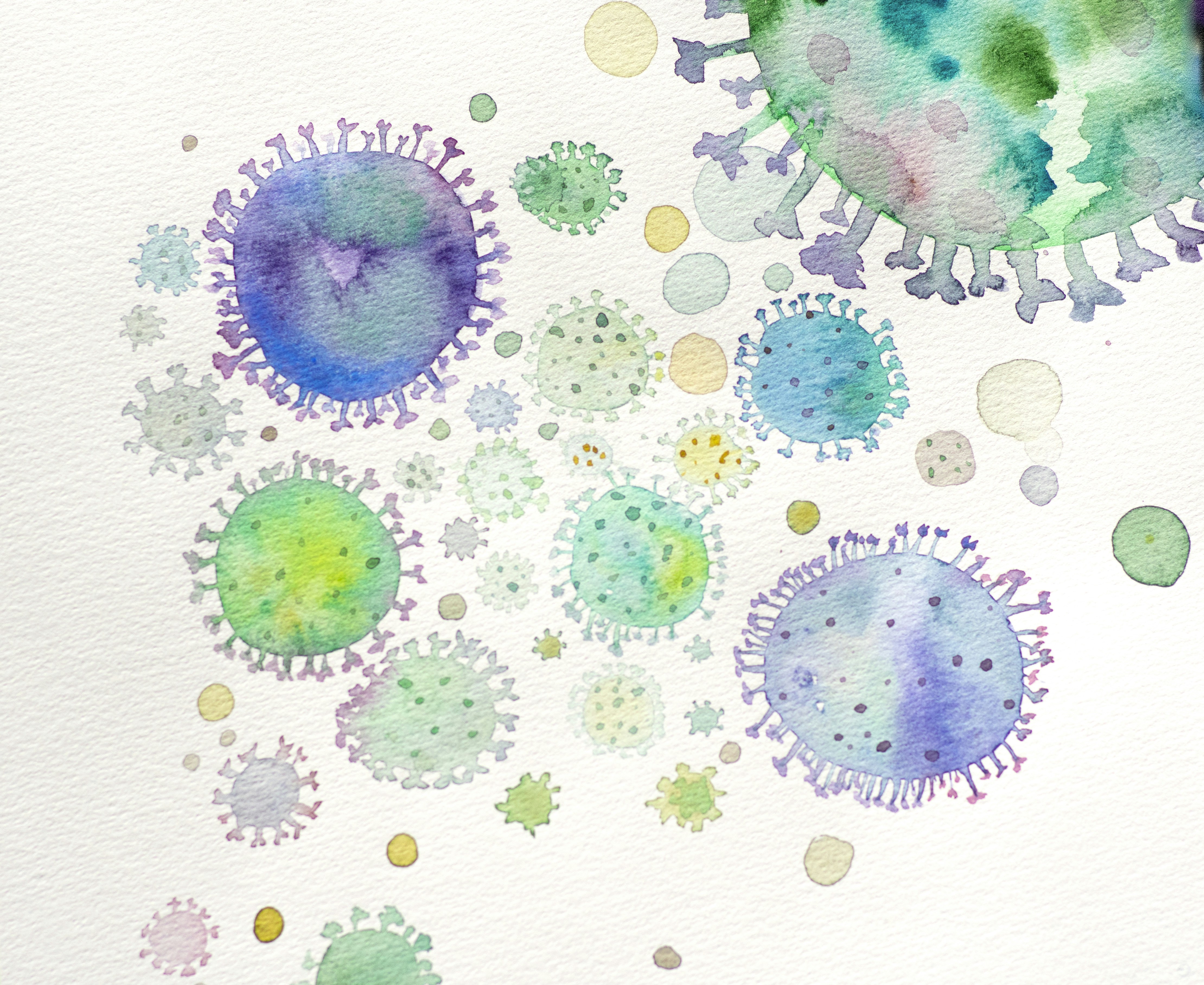過敏|4|失去的形狀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第一次接觸喪葬的所有儀式,便是因為你的死亡。
靈堂設置在家外面的大埕,在靈堂裡除了定時的上香、燒金紙,接著便是不斷的折元寶與蓮花,重複的動作慢慢在肌肉的學習下變成一種反射動作,接著進入一種不帶思考卻極度專注的無限循環,當摺紙的動作成為當下唯一需要專注的事,彷彿就能加速忘記悲傷的時間。
到了特定的時段,母親喚我去燒金紙,我將其中一張紙點燃,放進被燒得烏黑的鋼盆裡,並趕緊將手中整疊金紙攤開,在那張紙被燒盡前,丟入新的燃料,延續鋼盆中即將消逝的火光。
橘黃的火光在小小的鋼盆裡逐漸壯大,據說火擁有淨化的力量,我默默將心念揉進手中的金紙,期盼火能將所有遺憾昇華,每次想念你時,我會告訴自己,你的離開只是一種極為深沈的冬眠,我感覺自己很可笑,就像大人在欺騙孩子般,總有一天孩子會驚恐的醒來,發現原來這就是失去。
火焰在劇烈的高溫之下化成了黑煙,燃燒過後的東西被分解得更加微小,消散在我們看不見的呼吸裡,隨著襲來的陣風捲去了殘留的焰火,鋼盆裡的灰燼也隨風飄起,我邊收拾邊抹去飄散到手背上的灰燼,灰白色污線牽引著視線,庭院的大樹被陽光金黃色的紗簾輕盈的罩著,光穿過樹枝間那個較大的縫隙,就像一盞聚光燈停留在樹蔭下,我不自覺地注視著那道光,明明是剛好的自然現象,卻莫名像是為了這個瞬間而刻意產生的。
在這個當下沒有了時間,一陣風揚起了灰燼,我陷入這光影美妙的幻化之中,不自覺地流下眼淚,分不清這是出於喜悅或是悲傷,就像混在這金黃光芒下的灰燼,也變得晶瑩剔透,這陣風起也同時帶來了雲,漸弱了陽光,一切像是什麼也沒發生。
或許消失也是一種存在的方式,或許火並沒有真的淨化所有愁緒,以為飄揚的灰燼能隨風離去,其實一直都在,只是換了一種方式寄生在身體裡而已。
收拾完鋼盆內的灰,我進到客廳坐進了你的藤椅上,我小心翼翼地維持身體的平衡,畢竟那張藤椅破舊得連放在路邊都極有可能被忽略,儘管如次在那些破爛不堪的細節裡,卻依稀沾染了你存在的痕跡。
右邊的把手上明顯的磨損,是因為你習慣將右手靠在上面,有時候會倚著把手撐著頭看書,左邊搖椅的關節發出較劇烈的聲響,是因為你習慣翹起左腳搖著椅子,小時候上搖椅時,我也習慣坐在你的左腿上,所有的痕跡都隱藏著能細細品味的故事在其中。
你曾告訴我說,在我還沒有記憶時,你會將我放在你的胸前,搖著搖椅哄我入睡,到我長大了以後,偶爾會在吃完午飯後坐臥在椅子上休息,午後的陽光襯著透光的淡黃色窗簾變得柔和,椅子的關節因為長期使用發出了嘎吱聲,午睡時我習慣聽著那樣的聲音,這習慣彷彿是來自本能的呼喚。
我將四肢蜷曲在一起,讓自己被搖已全然包覆,如果當初在醫院那通電話,我直接顯露我的脆弱,你是不是會因為心疼而好好在家等著我回去,在我回到家打開門時,你會走到門口給我一個擁抱,摸著我的頭說:「佇臺北真辛苦喔,物件放放來食水果啦!」
幻想、白日夢是生而為人的少數美好之處,坐在籐椅上,我想像著你安慰我的情節,想像這一切幸運的在另一個時空裡發生了,心裡的酸澀像是計時器般,提醒著我現實將慘忍的否定這份無法擁抱的美好。
「嘎吱、嘎吱。」
我自然的閉上雙眼,在沈靜安穩的呼吸中,身體逐漸癱軟、下陷,意識變得柔軟、遙遠。
「嘎吱、嘎吱。」
我睜開雙眼,陽光因為改變了方向,在牆上產生出窗框的影子,室內因為日落變得更加黃澄,每項細節都和每次午睡清醒後一樣,我等著你呼喚我吃飯的聲音,才又一次意識到你已經成為一段無法重複播放的回憶,一樣的時間一樣的空間,卻得不到一樣的結局。
「嘎吱、嘎吱。」
我試圖閉上雙眼,隔絕所有能觸動悲傷的感官,這個空間充斥著太多你存在過的事實,高低櫃上珍藏四十年的威士忌、長青羽毛球比賽獲得的獎牌、實木相框中拿著麥克風唱歌的你,你走過的歲月都濃縮在這個空間的每個角落。
「嘎吱、嘎吱。」
搖椅上的靠枕終究還是被我滴上了調味,那是人體中和大海最接近的味道,淡淡的鹹味沿著靠枕上褪色的織線擴散,思念也隨之蔓延,我感覺自己因此和你更近了一點。
❄
「哈⋯⋯哈啾!哈⋯⋯啾!」
啊⋯⋯是海的味道。
明明就快要走到海邊了,但卻因為打噴嚏而走慢了這段路,接連的噴嚏讓我無法好好看路,有時候還必須因此站在路邊一次打完,擤完鼻涕才能繼續走,儘管對過敏沒有習慣的一天,但應付過敏倒是養成了習慣。
從以前不太有出門時隨身準備衛生紙的習慣,到現在必定隨身一包衛生紙,要說這是托過敏的福嗎?好像有些奇怪,但這樣在臨時要上廁所時,就再也不會找不到衛生紙了。
偶爾對過敏厭煩時,我都這樣安慰自己,或許也沒那麼糟,我也是因此而果斷離開臺北的,回到了真正屬於自己的地方,面對垂垂老矣的小鎮,或許正是充滿生機的時刻,有時候生命會以退為進,去尋找更靠近自由的答案。
當初我以為離開影視產業我就什麼也沒有了,畢竟我投入了全部的自己在這裡面,而等到真的離開之後,才明白原來離開才是擁有的開始。
我站在海堤邊,社群跳出一年前貼文的回顧通知,我看著自己一年前寫下的文字:
「失去所產生的哀傷,從你離開的那一刻,被時間凍結在一起,在失去找到自己的形狀前,會沒有盡頭的與哀傷凝結在一起,那段時間有時候是夜晚,有時候是觸景生情,儘管知道每一次的抒發,都向前走了一步,但究竟要走到哪一步,才能不再因為想起你而哭泣呢?」
一年了啊,時間的輪廓倒是因為這則通知變得清晰,而失去的形狀依然有些模糊,遠遠看著夕陽的落下,即使戴著口罩依然感受到,雙頰被強風冰冷的利刃悄然無聲的刺傷,冬季的海風不帶任何眷戀,呼嘯而過所有能到達的角落。
身後無人居住的破舊矮房原來是一間雜貨店,年老的老闆開著雜貨店也只是因為無聊,做生意已不是重點,開著店為得是偶爾跟路過的朋友寒暄兩句,所以店裡常常看見過期卻仍在架上的商品,但沒有人在乎,畢竟老闆也不在乎。
當老闆離世後,早已定居他鄉的子女便將店收了起來,老舊的房子掛上出售的掛布,在狂風的吹動下掛布啪嗒啪嗒的甩動,空蕩樓房也因風發出嗚咽的鳴響,或許是風把悲傷留在了那裡,我望著矮房的深處,黑暗吸收了包含微光照射時帶來的一切,在屋內形成一個無盡的深淵,不知為何我忽然想起了那天姑婆的身影。
-待續-
為什麼會看到廣告
38會員
86內容數
電影用影像說故事,那是第一次的創作,觀眾的體驗行程第二次的創作,文字電影院就像是翻譯機,透過我的體驗將電影的細節轉譯,用文字的方式寫下對一部電影的想像,闡述對我而言的「那部電影」。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