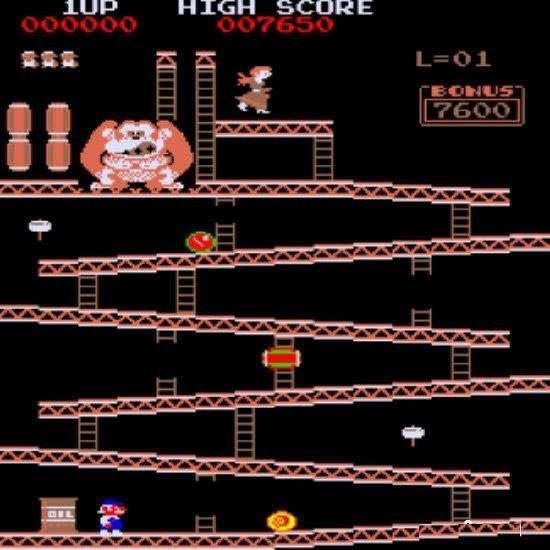方格精選
當我們一起走過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入院的第一天,你來到我的身旁,問我可否讓你坐在我的旁邊。我點點頭,沒有說話,也沒有抬頭看你。你拿起你的名牌,告訴我你是負責照顧我的護理師,你叫什麼名字,以及我有什麼需要都可以告訴你。然後你遞給我一本彩色插畫的方形小書跟我說:「你是基督徒,對嗎?這是一本禱告手冊,我去書房看了覺得還不錯,送給你。如果你有需要的話,你可以跟著書裡一起向上帝禱告。我也是基督徒,我們都是肢體,都是弟兄姊妹。」我拿著你給我的小冊子看著發愣,你起身離開我的身旁。那一天,當我們一起走過。
出院的前一晚,你來到我的病房,跟我說你聽說我明天要出院了,問我是否有空,我們一起來唱首詩歌?我笑著跟你說我五音不全,你說沒關係你也是;但想說我明天要出院了,你特別先過來看看我,晚點你必需值大夜。你拿了你印好的歌譜,那是一首兒童詩歌,你問我會唱嗎?我憑著不可靠的記憶向你點點頭。病房裡不能攜帶手機,你的手機不知怎麼地又剛好連不上網,於是我們五音不全的依照自己的印象唱著。唱完了,你對我說,你常常跑步,有次腳受傷了,你很沮喪,但抬頭看看天上,上帝就在那裡;你看著我,溫柔的對我說,永遠別忘記了,不管發生什麼事,一定要記得抬頭看看天上,上帝就在那裡,永遠地與我們同在。我哭了,你為我祝福後道別。那一晚,當我們一起走過。
你總是穿著一件薄薄的長袖外套,淡淡的鵝黃色身影在走廊上晃著;十六歲的你,臉頰稚嫩而面容顯得陽光。那天深夜,當大家都已經服用安眠藥入睡,我卻不知為何的恐慌驚嚇,害怕得跑到護理站前發抖哭泣。你悄聲來到我的身旁,輕輕地牽起了我的手,安撫著我陪我走回病房,為我拉上被子,握著我的手柔聲地跟我說:「不要害怕,我們都在這裡。」在藥物的鎮定中與你的安慰裡,我恍惚地進入夢境。那一晚,當我們一起走過。
另一個深夜,我失眠離開病房,看到你獨自一人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我來到你的身旁牽起你的手,輕輕的摸著你用衣袖遮掩的傷疤。我靜靜地告訴你別再割了,我以前也是這樣,在學校會被霸凌。你對我報以一笑,說著早已被霸凌習慣,而我們相視開懷,彼此分享起醫生與心理師還跟我們說過些什麼「愚蠢」的建議可以取代自殘。那一晚,當我們一起走過。
那天早晨,你要出院了,要回學校了,要再次擁有刀子可以傷害自己了,要再次回到社會被他人傷害了。我緊緊的抱著你,耳語輕聲地說著我會想你,記得可以的話不要再割了,真的沒有辦法,換個不顯眼的位置。然後我對你笑了笑說,我想,醫生知道我這樣跟你說,應該會很生氣。你對我開懷大笑,我笑著但很認真地回應你,告訴你我會想你,但別再回來了,而且一定要畢業,好嗎?你點點頭,我緊緊再抱你一回;病房厚重的大門關上,我們就此不說再見的永遠道別。那一年,當我們一起走過。
我哭著用公用電話打手機給你,告訴你我受洗這天,我真的好想領聖餐。你安撫我,跟我說沒事的,好好休息很快就會出院的。而你不知怎麼聯繫到我的教會,教會牧者在我受洗那天帶著聖餐來病房看我。那是他親自為我烤的無酵餅,以及一罐葡萄汁。我很愧疚地想著造成他的麻煩了,他笑笑地跟我說他邊烤孩子邊吃,吐司不是無酵餅,我不是想領聖餐嗎?我點點頭,他問我為什麼想領聖餐呢?我哭著說我不知道,而你帶著我唱詩歌,唱沒兩句就被一旁的病友打斷,吵雜的聲音讓聖餐絲毫不像在教會般莊嚴。我聽著你背誦著經文,耶穌的身體與耶穌的血,第一次如此深刻地進到我的裡面。我哭著謝謝你們犧牲假日特別來病房看我,深刻的感覺到生命間的彼此扶持,以及你口裡說著「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的安慰。「好好休息,出院以後,弟兄姊妹都在等你回來。」那一天,當我們一起走過。
你拿著你的名牌,告訴我你是跟主治醫生一起照顧我的醫生,問我可不可以跟你聊一聊,你每天都會過來看看我。我問你要聊什麼?服用的藥?發病的期程?然後我像背誦課文一般背給你聽。你對我搖搖頭,輕聲地問我為什麼住院,我哭著跟你說全世界都叫我住院,每個醫生都叫我住院,我怎麼知道為什麼我要住院?為什麼自我傷害就是不對?為什麼我要繼續活著?為什麼生命值得繼續下去?為什麼大腦會一直唱歌?為什麼我會聽到好多聲音?為什麼我怎麼也不會累?為什麼我整天又都躺在床上毫無力氣?為什麼吃藥感覺一點用也沒有?然後我像隻受傷的小動物,瑟縮起來,無法面對你的視線。你問我是不是很愛讀書?問我有沒有看過「痛苦的奧秘」,然後拿起手機查給我看這本書。我哭著跟你說我現在什麼書也讀不了,字彷彿都在飄,什麼也進不到大腦裡。你鼓勵我之後讀讀看,告訴我這本書很難,但我一定能夠讀懂。我帶著淚痕看著你。那個下午,當我們一起走過。
你拿了我的枕頭,告訴我這是小時候受傷的我,我現在長大了,我該怎麼保護她?我有什麼話想跟受傷而幼小的自己說呢?我吞吞吐吐,不知道該說什麼,眼淚卻無法停止的流了下來,用了很大的力氣卻說出很小聲又卡住的對不起。你引導著我跟年幼的自己互動,直到你的手機響起跟我道別。我一個人抱著枕頭縮在被窩裡,淚如雨下一直滑落,重複的不斷說著「對不起,請你原諒我」直到疲憊睡著。那一晚,當我們一起走過。
你同意我畫畫,每天給我一個時段在護理師與保全的允許下用筆。我在畫裡想拼湊回自己,卻在心情瞬間轉為沮喪下把畫中的自己吊死。你總是會問我今天畫了什麼,或是今天寫了什麼,要我拿給你看,要我跟你說我畫的是什麼意思。我跟你說蛇杖代表醫生,但蛇也代表魔鬼,如果有天蛇從杖上爬了下來,那麼牠是醫生還是魔鬼?你沒有回答我,我沒有繼續說,我們之間維持沉默,而我低頭繼續畫畫。你開始出作業給我,要我把作業畫下來或是寫下來,我問你我什麼時候可以出院,你跟我說藥物調整好了以後再說。你問我出院想做什麼,我說我想關在家裡面哪裡也不想去,外面的世界好恐怖。你跟我說慢慢來,我抬頭對上你的視線。那一天,當我們一起走過。
我想要自傷,但護理站不願意借我刀;趁著治療課程,我溜進教室拿了剪刀在桌下自殘,然後又悄悄溜出教室,卻迎面撞到正巧過來巡房的你。你看著我流血的手,問我怎麼弄得,然後說我們已經約定過,自我傷害必須拘束打針。我跟你抗議中午用橡皮筋緊勒脖子已經被綁住打針過一次,現在才差不到半個小時。住院期間,你第一次這樣嚴厲的對我說話,告訴我一次關一次,一次打一次針。然後把我綁在床上打針,你看著我讓我好好睡一覺,我不以為然的說剛剛打針我也沒睡,醫生明明都知道自傷跟自殺一點都不一樣,為什麼不准我自傷?你看著針打在我的手臂上,讓我好好的冷靜冷靜。我一個人被關在空調很冷的房間裡,但手腳被綁不能拉好被子。你在隔天巡房問我是否還好,我問你是否害老師需要寫報告?你說我害所有人都要寫報告,愧疚了吧!我低下頭不敢看你,你拍拍我笑了出來,跟我說你騙我的。那一天,當我們一起走過。
我畫了被囚禁在籠裡的鳥兒,你看了一眼跟我說你知道我想回家,然後開始跟我約法三章。我突然抬頭問了你出院有沒有禮物?你愣住了,問我想要什麼?我問你可不可以抱你一下。你再次愣住,說從來沒有聽過病人有這種要求,然後不太自在地跟我說你會考慮。出院的那天早晨,我看見你過來巡房,急急忙忙的從交誼廳朝你的方向跑去,你伸出手來跟我握了握手,告訴我出院後要好好加油。我問你不是答應要抱我嗎?你說剛剛不是握手了嗎?然後我追著你跑,你尷尬地說這裡人多又有攝影機,進了病房很快速的抱了我一下。我跟你說我會想你,你在口罩下對我一笑離開道別。那一天,當我們一起走過。
我記得陪我聊天的你們,記得哭泣時你們的陪伴,記得在保護室裡你們坐在我的身旁陪我。我不記得你們的名字,但我記得你喜歡達菲熊,你喜歡史奴比,而你喜歡角落生物。我記得你拿孩子的照片給我看,跟我說他們喜歡畫畫,給我看他們畫的作品。我記得你在綁我的時候小聲地讓我聽話,不然綁更緊會很難受很不舒服。我記得你們總讓我把嘴巴張開看看有沒有把藥乖乖吞下,然後說著好乖可以準備睡覺。我記得你們進來我的床邊問我為何都不吃飯,然後又騙又哄的要我把便當吃完。
我記得那一年,那一個月,那一天又一天,那幾十個在杜鵑窩裡的日子。記得醫生、護理師、社工師、保全大哥,還有一個又一個來來去去的病友。記得愚蠢的早操,煩人的廣播,開不了的窗戶,沒有塑膠袋的垃圾桶,保護室柔軟的牆壁,還有洗澡的種種不便。那一年,那一個月,你們和你們。我想著那年窗上繫著的平安;那一年,當我們一起走過。
64會員
320內容數
生活如同雲霄飛車,但也讓我共享喜樂與淚水。期待藉由這系列的文章,讓我們能更友善地看待精神疾病的親友。我無法代表精神疾病,也無法代表躁鬱症;但我相信每個人同心攜手,社會標籤與刻板印象將被溫柔的挪去;讓杜鵑鳥能自由翱翔、飛越杜鵑窩。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