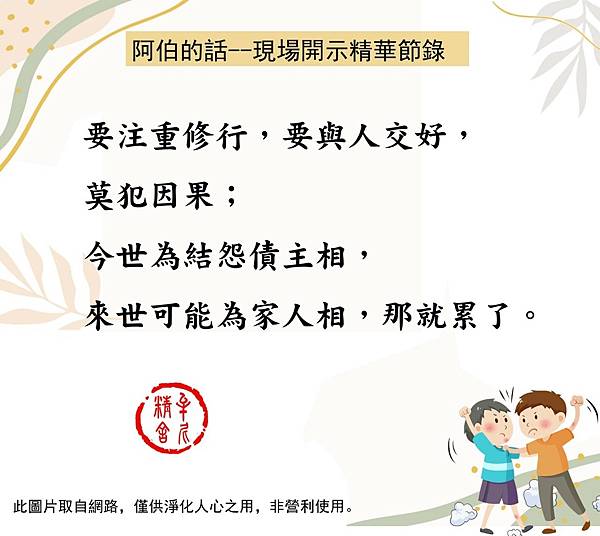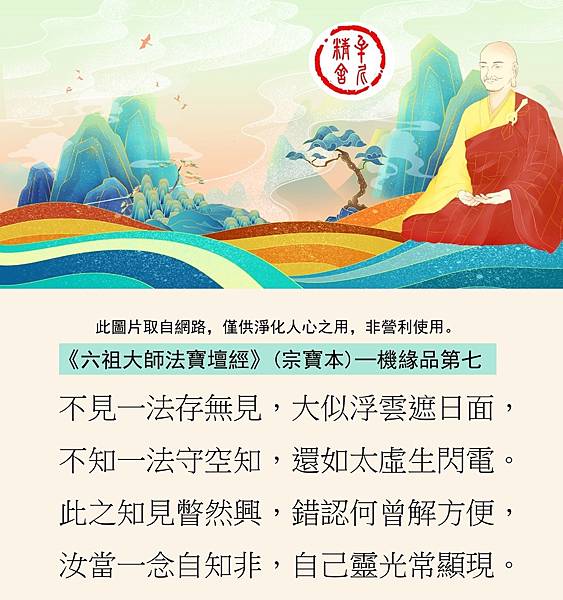難以勸誡的勇氣,是熊仁謙的自傳故事,從他小時候佛二代的出生,讓他注定走向與眾不同的求學路線,小時候就被迫研讀佛法,這對於修行者可能說:「這很殊勝」,他的確擁有了比一般修行者來的得天獨厚的背景,但事實上對他而言,對當時的他並非一帆風順。

童年時,他就被媽媽丟進了了海濤法師的僧團,在漢傳佛法的修行與學校之間飄盪著,因為他當時沒有選擇權,經歷了在修行者與一般學校的自我認同混淆,身分的混淆,在學校是與大家平輩,與大家玩在一起,被當作孩子一樣對待,但在僧團就要守僧團的規矩,也因為出家人的身分,就會倍受尊重。
這種身分認同與價值感的混淆讓他一直很迷惘。
在當時的他,感到一切迷惘,前方的路盡是黑暗,他看著眼前的師公,一直處理著雜事,受人景仰,但卻鮮少真的在做學問,想像著自己是否真的想要成為師公那樣的角色,直到他遇到藏傳的佛教,開始了藏傳佛教的求學之路,他明白他真正想做的不是受人景仰的法師,而是真正一個佛法學者。
在十三歲那年,他踏入了尼泊爾,開始了藏傳佛教的學習。
在我們羨慕和訝異他選擇的路,是幾乎台灣人走過的路,而且他回來之後也沒有那些可以被台灣承認的學歷背景,如果是一般人,肯定會很在意學歷,他如果失敗了、無法扛下去的話,他回來後,一切都要重新開始,重新讀國中,這後果是非常讓人挫敗的。
他在書中他寫下了:
完成夢想,你需要的是放棄。而且完成夢想不是不切實際,完成夢想恰恰才是最現實的。人們必須學會聽清楚自己內心的聲音,當時的我很強烈的知道那是我要的。
延伸閱讀:
很多人以為,追求夢想的人好像做出什麼很偉大的選擇,其實才不是這樣,我們不過是選擇生命中唯一一條看起來合理的路而已,因為其他方向都不是我要的。當那些東西不是你要的,你自然就不會想要。
我想正因為他很明白他要什麼,所以才能夠理所當然的勇往直前。
上述簡單闡述,熊老師在童年在台灣的經驗,更詳細的還是非常推薦,去看看實體書,去聽聽他本人在快樂大學的觀點,這本書我受到很大的啟發反而是後期他在印度的求學,對於不同文化的衝擊。
一、 自由奔放的思考
藏傳文化,盛行的就是辯經,這是他們一個很重要學習系統,與西方辯論的方式不同,傳統西藏佛法中採用的辯論系統,一般稱為因明辯論,一攻一守,攻方只負責發問,守方只負責回答。
守方只能給出:是、不是、不一定、不成立,攻方可以有許多空間來發揮,守方相對來說,非常不容易回應。
他們要說服的不是觀眾,而是彼此,因為限制很多,也讓守方在非常有限的空間發揮作答,所以每個回答都需要反覆的思考才能說出口,這是辯經的特色。
可以從影片了解他們辯經的形式

辯經強調的是自由奔放的學術氛圍,就像「前大法官許玉秀說: 「如果不能自由的講,那就不能自由的想。你我應該自由的講。」
這正是我們要對抗以前威權體制所遺留下來的陋習,威權體制的特點,是用恐懼去維護和學習的。就像我們會看到有些人在學佛的過程中一直被恐嚇,那是用恐懼去維護的。但我們在藏傳佛教讀書時的體制是用熱情、興趣、求學之心、自由的心態去維護,這是學風鼎盛。
我認為這也是在台灣求學很大一個挑戰,如果老師把自己視為一個權威,一個不能挑戰的權威,他捍衛的不是知識,而是自己的尊嚴,這也是我碩班求學時,感覺到窒息的原因,有些教授其實是非常守舊,也非常威權的。
學術自由在藏傳佛法上表現得非常好,這是我非常羨慕的。
辯經它具有自由奔放、沒有限制的立論,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配合著被精準定義的辯經語言,產生的結果:雙方在這個時候必須大量地思考。
這也是培養思考的習慣,讓我們遇到問題時,不再是恐懼害怕,而是「我要怎麼解決?」、「問題是什麼?」、「整個事件長什麼樣子?」
辯論的過程中,重點並不是要戰勝對方,而是透過對方的論證,進而發現自己的盲點。
如果沒有這樣大量的思考訓練,我們思維往往就會停滯在固有思考裡面,在同一個方向不斷的鑽牛角尖。
我們在筆戰或辯論的時候,很容易落入意氣之爭,這個意思就是我們只在乎贏對方,淪落到不斷挑別人的語病,不斷閃躲自己的邏輯錯誤,這是網路筆戰最終會讓你感覺到空虛的原因。
就如熊老師所說:戰勝別人不是容不容易的問題,而是沒有必要。我們必須戰勝的人,只有戰勝自己,這才是我們能夠活出自我的唯一方式。
而戰勝自己的方式就是要去推翻舊有的恐懼、推翻舊有的自我設限。只有透過這樣的推翻自我,你才有辦法挖掘出更好的自己。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思辨的過程中要減少價值判斷。
我們很容易下意識會認為某件事情就「應該」如何…這是大腦普遍有的直覺偏誤、道德判斷、過去的經驗,等等。
而思考可以對抗的是我們的直覺偏誤,大量的思考以及交流,更可以幫助彼此看到自己的盲點:「原來還可以這樣想」、「原來這個文獻的真正的意思」。
那個意識到「原來」的瞬間,洞察到自己的盲點,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成長。
價值是主觀的,我們每個重視的價值都不一樣,我們沒辦法在一個主觀的事情爭論對錯,因為主觀沒有對錯,只有客觀的事實才能區分真偽。
保持著這樣的信念,我們更加謙虛的對待彼此的觀點,往往別人的觀點可以刺激自己去看像未曾理解過的世界。
他的老師提耳面命地說:
「你來讀書,如果只是加固自己的觀點,那是沒意思的,讀書是為了知道更多元的觀點,體認到現實更多的面向是我們無法觸及的,然後養成求真的習慣」
二、老師:鼓勵學生表達的治學特色
(1) 「因為他很敢」:學習真的不要怕丟臉
在熊仁謙進入了「傳說的資優班」後,那一年他剛參與了辯經的活動,場上進行多對一的質問,旁人被允許幫攻方或守方,有位仁波切就幫守方回答,引來了拿過辯論獎的大魔王學長,來勢洶洶,讓守方非常緊張。
就在他的朋友謝立仁波切,在幾波攻勢下,逐漸顯出弱勢,熊仁謙一個護朋友心急,就跳出來對攻方大喊:「你這個論點不對!」,因為他是個門外漢,什麼規則都不懂,讓全場大笑。
剛入門的他,很多辯經的用語他都不理解,他也硬著頭皮守備,每一句都惹來哄堂大笑,就這樣讓大家笑到崩潰。
不過在大家要散場時,佛學專門教辯經的老師說:「他以後會很有好的成就,因為他很敢」,從那之後他也更加積極加入辯論。
老師常跟他們說:「你只有兩個選擇,要嘛就是在佛學院裡面丟臉、把臉丟完;要嘛就是到外面,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各式各樣的問題,然後丟臉」
學習真的不用怕丟臉,這應該要成為台灣教育的風氣,因為過去我的那個年代我遇到台灣教育太缺乏包容性了,台灣太注重考試文化,只有對和錯,沒有其他方向的思考,以及快節奏的教學模式。
也讓我高中時期,從跟的上節奏會去不怕丟臉的發問,直到越來越多問題,老師也會覺得你在浪費我的時間,讓我完全沒有自信再去發問,加上同儕之間的隱性競爭,「大家都會,為什麼你不會」也讓我的學習的動機降到谷底。
直到上大學,我就是一個不怕發問的怪咖,我只要有興趣的課,我就會坐到最前面,去與老師最直接的互動,儘管我不擅長背,很多科目都不到頂尖,但我到現在這些知識都成為我工作的專業。
(2)「一種現實,有千萬種觀點」的信念
有一次傳授觀點的老師是禪師出身,個性相對暴躁,他有個習慣,只要脾氣瀕臨爆發邊緣,就會不停搓手上的念珠。
隨著熊仁謙回答老師的問題,他發現老師手上的念珠搓的越快越用力,他幾乎感受到老師的神經就要斷線,隨時都會爆炸,他越講越緊張,深怕老師不認同,是不是就會被狠狠的臭罵一頓。
但他沒有打斷,而是保持耐心的聽完,還花了三十秒深呼吸平息情緒,建議熊仁謙可以回去看看那些經典,好好補完基礎,再來找他討論。
讓他意識到,就算是似懂非懂的情形,說出口也是種學習的過程,因為你在組織你目前理解的部分,一方面也可以讓別人找到你的盲點,或是再事後學習的過程,重新看到自己的盲點。
對他而言,最大的影響就是老師對於他人觀點的尊重,儘管暴怒無法認同,但老師們不會讓情緒嚇跑了學生表達觀點的勇氣,他們致力讓彼此可以自由說化的環境,他們也不會強加自己的觀點,而是建議學生如何思考得更深,看那些書籍,再來聊聊。
我讀書有三個老師,一位禪師,兩位學者,三人的個性天差地別,但有個共通之處:重視真理甚過於個人,如果可以把學生推得更貼近真理與真實,他們會發自內心歡愉。
(禪師就像是學者,教育學生們經典中的觀點,觀點在佛教裡又稱為內明)
另外有個老師,因為叫錯熊仁謙的藏文名,在教堂上慎重地向他道歉,他的身教表現出:「重視現實,甚過個人的面子跟觀點」
這是讓我非常佩服的身教,以及老師面對自己的信念,是把信念放的如此崇高,這是修心非常高的層次。
我著實深受感動。
心得
這本書真的非常精彩,也讓我見識到印度(藏傳)佛教的文化,他讓思考成為磨練我們信念的工具。
三年前,我深陷小劇場的困擾,多次告誡自己不要再欺騙自己,我意識到真實和誠實的重要,所以就把這個信念掛在心頭,發誓永遠不說謊,做一個內外一致的人,這個信念也讓我少走很多不必要的路,直面現實,我們要改變是自己的觀點和多方思考,來改善自己的盲點,承認自己的盲點,所以,我們需要學習、需要傾聽、需要同理。
這是本好書,推薦給你,還有好多很棒的觀點想要分享給你,篇幅的關係,所以,下篇見吧!
喜歡我的文章,歡迎按愛心、追蹤我及我的專題,也歡迎來我的臉書與我互動。感謝你的支持,願你成為完整的人。
昆陽 Peace 2021.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