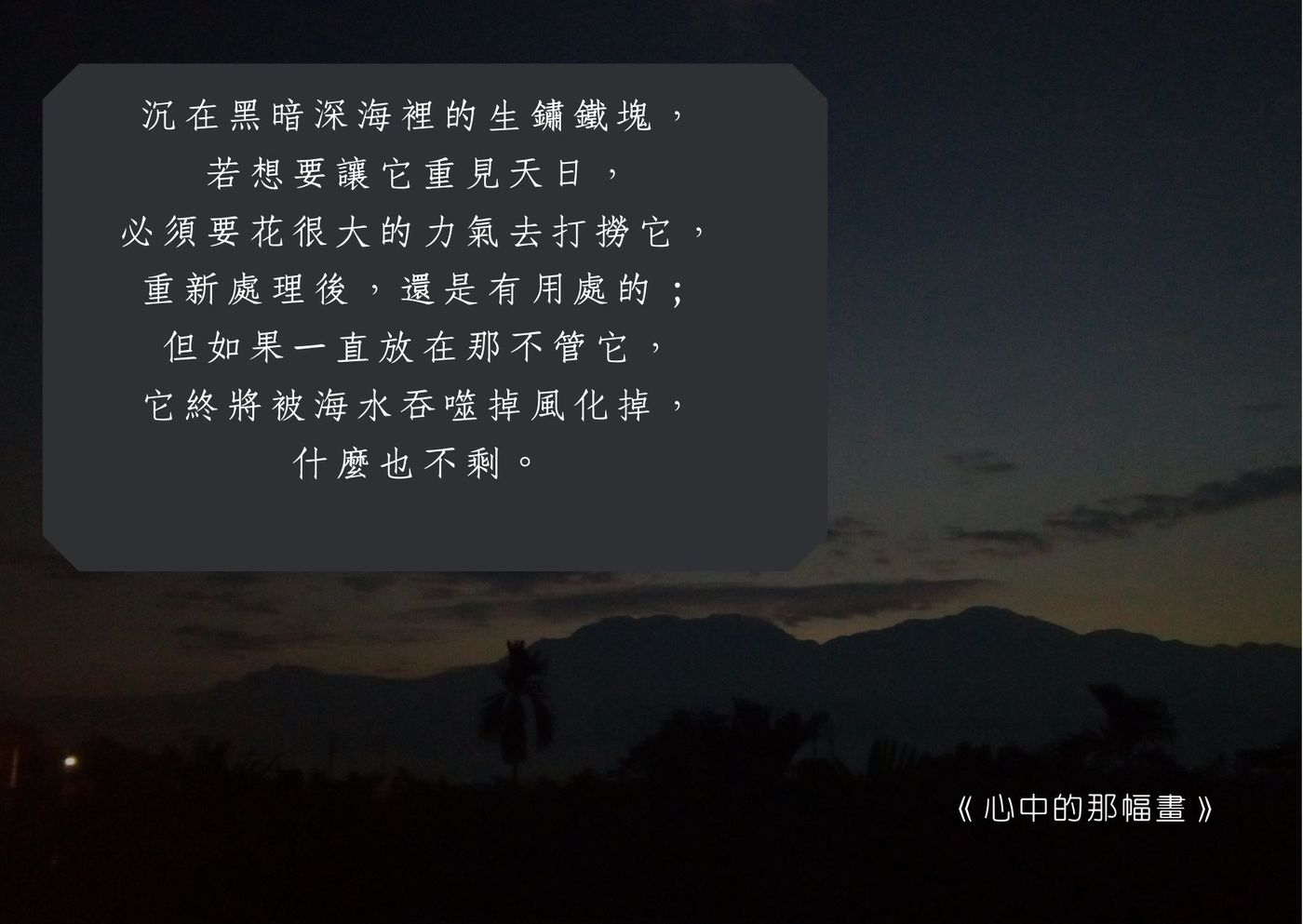解剖學中有一個部分特別讓培根著迷:嘴。一個在他作品中反復出現的形象,在《以受難為題的三張習作》中已經特別出現了,並且這位藝術家一直堅持不懈地研究此造型。
1935 年,在巴黎的一次旅行中,他買了一本關於口腔疾病的二手書,上面有手工上色的插圖,他對此書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培根承認自己被其強烈地吸引,並且被這些受損口腔內部的檢查圖像完全迷住了。他說自己很想用莫奈風景的全部美麗來畫嘴巴,但沒有成功。嘴能讓人尖叫,這是恐怖的終極表達。
事實上,目擊恐怖的在場以及膽寒驚懼的反應本身,比露骨地揭曉究竟是什麼在嚇人更具衝擊力。最重要的是,通過不定義對象,畫家完整保留了他主題的本質要素(也就是恐怖本身)。他就這樣帶出觀眾聳動的知覺,以情緒襲擊他們。
前文中說到中間人物臉上的遮眼佈時,所提及的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大師Matthias Grünewald,這位藝術家所繪的人物速寫草圖,也影響了培根。

據傳Grünewald性格陰鬱同時患有瘟疫,他的光芒一直被同時期同地區的巨匠杜勒所掩蓋,曾幾乎被遺忘,作品也大量佚失。然而他極擅長祭壇畫,對人物也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其中一幅尖叫的小孩可看出他將深刻的痛苦,或戲劇性的精神崩潰描繪到了極致。暴哭的孩子向後撐仰著頭,我們直視著他張開的嘴巴深處的黑暗。

同樣在描繪尖叫的畫面,培根也受到謝爾蓋·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電影《波坦金戰艦 potemkin’s cuirat》中保姆的啟發。
在奧德薩階梯上的大屠殺,這是影史上蒙太奇剪輯的經典,沙皇大軍從階梯頂端壓進,平民老百姓在階梯竄逃,乃至最終全數被無情槍擊的場景。
節奏的推動從一位母親被槍擊,她手一鬆,嬰兒車從階梯頂部開始滑落開始。小車顛簸地壓過無數倒地人群的手腳軀體,隨著劇情加速度衝下,充當了這場暴行的推進的時間線,伴隨人群被射殺的逃躲與死亡,緊張情緒持續累積,畫面切換的節奏越來越快,軍人猙獰的表情、強褓中無助的嬰兒、槍砲殘酷的煙硝、民眾驚恐的特寫,快速閃過的緊湊蒙太奇將屠殺推向最終高峰,乃至嬰兒車總算翻覆、軍官舉刀砍落、一張保姆血流滿面的臉--張開大嘴嚎叫,是痛苦和驚恐的極致--但同時又像是某種釋放--幾乎彷若性高潮般將這個段落收場。


嘴,是進入人體內部、進入肉、血和內臟的開口。培根的迷戀涵蓋了身體的各個方面。
培根曾屢次使用三聯幅式樣,這因此成了一種帶有他特徵的形式。粗厚的金色畫框和保護畫布的玻璃,系統地裝配在作品之上。藝術家意旨在通過裝置的手法,給“舞台佈置”自己所秀出的圖像,進而與觀眾產生距離。距離正是培根玩弄的手法,因為他也同時藉著觀眾在玻璃上創造的反射,使倒影與圖像融合,邀請並拉近了觀眾。
《以受難為題的三張習作》本件作品的標題明確提到了宗教。培根解釋說,他預計畫第四幅畫,以描繪其中提到的基督受難。在1950年代,他投入教皇英諾森十世Innocent X的肖像系列製作,共做出了45幅不同的變體,最著名的其中之一是《委拉斯開茲Diego Vélasquez的教皇英諾森十世肖像的研究》(1953)。

培根是位無神論者,這使得他對宗教的引用令人出乎意料,尤其是這個主題在20世紀的藝術中已經過時了。然而,本世紀也是心理學出現的世紀。在兩次大戰期間的超現實主義運動中,沒有人不知道無意識的重要性,也沒有人不知道一個主題經常隱藏在另個主題之中。
畫家在十字架上看到了最暴虐的處決形式,一種極端野蠻的行為,簡而言之,這是對恐怖相當忠實的體現。至於他對教皇英諾森十世肖像的創作,培根給出了與宗教無關的解釋。例如,他聲稱自己需要一個「使用這些顏色的藉口,你不能給普通衣服畫上這種豔紫而不陷入一種山寨野獸派的伎倆。」然而此舉最重要之處在於,培根對維拉史貴茲繪畫的高度推崇--特別是那件出自他筆下的英諾森十世的肖像,引致了這個選擇。

然而與西班牙大師不同的是,法蘭西斯·培根畫裡的教皇正在尖叫,他表示,這場尖嚎早已以一種匿伏在潛意識中的態勢,隱身在維拉史貴茲的肖像裡了。培根感興趣的是超出畫中的視野之外、教皇究竟目睹了什麼、那個致使他尖叫的根源。他說,這可能是一個裸體的少年,也或者,正是培根本人,就如《1962 年紅教皇研究 Study of Red Pope,第二版》(1971 年)所描寫的那樣。 1953 年這幅畫所表現出的壓抑而神秘氣氛似乎與宗教無關,而更可能是出於自傳式的層面。

隨著《以受難為題的三張習作》,培根提出了自己對厄里尼厄斯(復仇三女神)的解釋。在古希臘,她們是負責懲罰人類罪行的神祇。她們公正且毫無憐憫。她們嫉妒駭人,折磨那些作惡者,並無情冷血地追捕他們。
在培根1939年觀看的T.S.艾略特的劇作《家庭團聚The family reunion》中,這三女神具體化身成為了主角的懊悔和愧疚,強烈地引起了畫家的注意。另外,在閱讀埃斯庫羅斯Eschyle的著作《奧瑞斯忒亞Orestie》之中,培根對她們有了更加細緻具體的鑽研。她們啟發了培根畫面中這些扭曲的造型,其遠離了古典的表徵形式。在他眼中,她們是在作品中反復出現的複仇、痛苦和厄運宿命的體現。雖然厄里尼厄斯確實使人受盡煎熬,但她們也守護並捍衛著既定的秩序。

法蘭西斯·培根的畫作是對立概念的交匯點。
吸引/排斥可能是最顯而易見的,因為它向觀眾揮出一道重擊,讓他們立即在著迷和不安之間搖擺不定,在想要窺見每個細節的渴望以及想要逃離的渴望之間搖擺不定。培根本人很可能也感受到了這種矛盾心理。他所描繪的恐怖源於他的痛苦,這顯然讓他迷戀。他說他將自己的神經系統投射到畫布上。
培根也混合了生與死。他重現了受到折磨的身軀,而此折磨就在最終極地調動起軀體能量(表現為緊張)之時,畫龍點睛地強調了令它活轉的生命。讓我們回想《兩個人物》(1953),它以鬥毆的形式表現了性快感,又或者也許一場如同耦合般的打鬥。在這兩種情況下,無論是趨向死亡還是趨向生命,都只剩下一種我們可以稱其為對“慾望”的痴迷。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以受難為題的三張習作》已經包含了培根繪畫以及他之後即將發展的所有作品中的許多元素。培根本人將這幅畫視為他職業生涯的第一件作品,而他在1944年完成這幅作品時已經35歲了。在此前他已經進行了不知幾凡的試驗,不計其數的探索,畫了很多很多。
在這首部官方作品裡,他已成功綜合了一種已經非常純熟的技術與風格以及一股龐大的能量,而這通常是藝術生涯初期所特有的。培根在1988年的《1944年三聯畫第二版》(Second Version of tritych 1944)幾乎就是複製品。兩者主要的區別在於尺幅(超過兩倍大,每個畫板147×198公分),與背景相較,人物圖像所佔的比例更小,而之於背景,血紅色取代了橙色。

普遍的看法是,這第二個版本在大小上相當雄偉,並且筆法的精湛程度也加倍高超。然而它不那麼暴力、不那麼粗生,總之不如第一版強有力。這也是培根的觀點,最終他之所以想作第二個版本的原因仍然不明。雖然這位藝術家經常再畫自己主要作品的第二個版本,然而有趣的是,在經歷了40多年大量創作後,他卻選擇了為新版不更動任何東西。
同樣有趣的是,培根言下之意是懶惰導致他放棄了原始的背景顏色(因為太痛苦且太耗時而無法實現)。他以這種隨意口吻來談及自己的出道作品,似乎令人意外。

想要根據作者的生平來解釋一部作品,總是有些冒險的。法蘭西斯·培根的一生有很多面向可以用作為這類解釋的基礎,然而這種解釋永遠只是些詮釋觀點。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以及在他身後提出的所有觀點中,有些是毋庸置疑的,有些則可能是...

法蘭西斯·培根於1909年出生於都柏林,父母是英國人。
他不具備自己父親--一位馬匹飼養師和前軍官--所瞧得起的男子氣概標準。培根身形孱弱,甚至陰柔,並患有哮喘,以至於無法接受正常的學校教育。當父親發現他是同性戀時,憤而斷絕了父子關係,可能還令人狠狠毆打了他。
年僅17歲的培根被放任自流,在倫敦、柏林和巴黎探索了波西米亞式生活的樂趣。然而,他始終有著保姆相伴,他與她非常親近,而保姆也持續照料他直到她去世。

培根再也不掩飾自己對於壞男孩以及對身體暴力的癖好。他也是一個賭徒,有明顯的藥物濫用傾向,尤其是酒精。 《三張習作》實際上是在短短兩週內完成的,培根回憶說,「我心情很爛所以喝酒,在嚴重宿醉的狀態下作畫,而且同時還在喝;有時我幾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想也許這種杯中物能幫我變得更自由一些。」最後,他患有抑鬱症,這導致他毀掉了自己的許多作品。
在一個不能容忍同性戀的社會以及一位拒斥同性戀的父親底下,培根很可能感到受到沉重負面批評和壓迫(彼時同性戀在英國是一種犯罪)。釘上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徵,而當時的社會風俗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基督教的傳統。這種傳統所代表的權威,傳播了規範,將培根推向社會及其家庭邊緣。


同樣的狀況也適用於厄里尼厄斯,他們懲罰那些違反既定規則的人。十字釘刑的受難以及古希臘的報應與復仇女神,他們兩者的形象完美地展示了盲目和絕不饒恕的力量。而這種強大力量的宿命,與培根以及他的作品產生了共鳴。
教皇英諾森十世長相很像他的父親,使這個人物的系列肖像,因此反映了教皇所代表的權威,也同時反映了父親這個人物、那個拒絕了他的父親。他們的重疊可能解釋了培根在肖像中所加入的,以及溢於作品畫面之外的尖厲嚎叫。

培根的許多作品都將生與死揉合在一起,並且經常過分強調一端以放大另一端。畫家對這兩種對立衝動的博弈,經常與他將爽與虐並存的性取向被相提並論。對於將生命視為只是一段短暫旅程的人來說,對身體以及經由其中所感受的兩種主要緊張狀態,產生出濃厚興趣似乎很合乎邏輯。通過在畫布上安置他自身的精神性與本能性內在,這些主題必然會回歸。
正如我們所見,他的傳記中的某些部分比其他部分被挖掘得更加入裡。
試想,在愛爾蘭爭得獨立之際,一個英國孩子在那裡渡過的童年中所可能伴隨的緊張局勢,甚至是某種環境敵意。他和保姆的關係也不是很詳細,然而,那顯然是一種強烈的情感紐帶以及堅定不破的支持,對將培根拒斥邊緣的所有種種都毫不在乎。
這些等等其他面向的生平背景,卻普遍在討論培根藝術時,被刻意的忽略或簡化。因此,一部作品的心理解釋,也提供了關於評論者及其所處時代的明確訊息。

當然,這位藝術家紊亂的一面、他的自我毀滅行為、他的抑鬱或他在畫布上置入的狂暴,往往立馬能引起人們的直覺性地口舌和熱議。然而弗朗西斯·培根並沒有年紀輕輕就死於暴力,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了近50年,直到82歲去世。因此,我們可以假設,他性格的其他方面緩解了前述的黑暗勢力。
首先是創造,它可能最完美地代表了生命的驅動力。創造需要沉思、判斷和能量。即使培根將“意外”作為他作畫過程中的要素之一,他的作品也絕非是即興或隨機的。更甚者,雖然他描繪的人物充滿暴力和混亂的能量,然而作品背景卻精準規劃得簡單而赤裸,非常堅實地建構出整個畫面。他告訴記者,他喜歡這種控制感,包括了其中的樂趣。

他同時也舉出自己對酒精的嗜好為例,他承認自己喝得很多,但也非常小心不要成為酒鬼,在此處所透露出的清明與自我毀滅行為似乎還相去甚遠。法蘭西斯·培根最首要的慾望(也許是他的需要)是繪畫。這是他性格中最重要的層面。
《以受難為題的三張習作》在情感上打動了觀者。畫家拒絕任何帶有誘惑和說明性的意圖。他描繪了身體和穿過它的緊張情緒,反映了一種精神和神經狀態。嘴是為了尖叫而生,而尖叫則是為了將之激起的恐懼而生。他創造出一個畫面,在到達我們的思維之前便先撩撥、激發了我們的心理衝動。

透過圖像,他藉著活化觀眾內在的緊張感,向我們傳達了讓他著迷或折磨著他的情緒,這種緊張可能非常近似當培根作畫時自己正身陷其中的那種狀態。因此,確實,這幅三聯畫的三個人物以某種方式鑽進我們的體內。因此似乎培根主要是在畫一種自畫像,一幅情緒性和心理驅動力的自畫像。顯影那些無以名狀與不可言喻之物是超現實主義繪畫的提問。培根以一種基本而直接的,幾乎是“物理性”的方式實現了這一點。

法蘭西斯·培根作品的豐富性是一種智力獨立的結果。他不屬於任何藝術運動。比起紐約學派的抽象,他更喜歡具象。他探索的是自身的內在性,而不是像當時大多數歐洲運動那樣探討理論和社會問題。他根據自身喜好和經驗進行了自主的藝術教育,而並非以學術的方式。他能夠從前輩那裡汲取靈感,而更在技術與繪畫主題上拓展出自己的藝術抱負。

有了這些,並同時由體驗汲取,他所創出的所有作品都強而有力,深深地觸動了他那個時代的公眾,就像它觸動了今天的我們。培根在我們每個人身上擊中的是我們生命的本能,這種本能囚禁我們、驚懼我們,是我們體內最殘暴的惡魔,也是夜裡不能擺脫的夢魘。這是一種基本而強悍的本能,常令我們的心智迷失在存在的種種不順遂之中。
然而儘管如此,這種本能也時刻讓我們被名副其實的“生存機器”--即這具身體--給敲響警鐘。因為它的駭人與艱鉅,並非為了摧毀我們,而是讓我們跨越、讓我們凌駕,並向自我與整體的人類存在證明,這個超越的壯麗與偉大。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