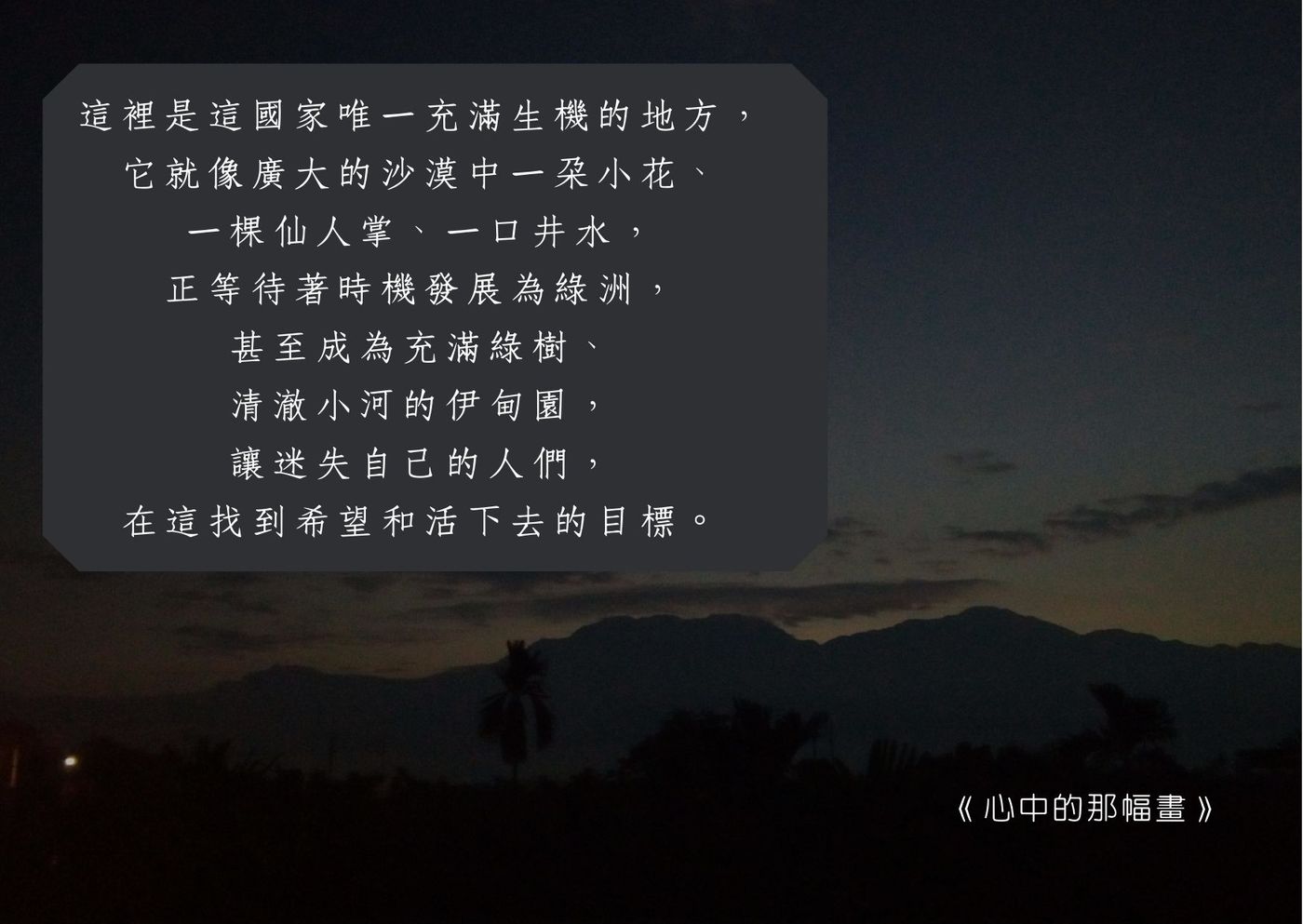「老闆你好,請問我這個是算短髮?還是長髮阿。」一位皮膚黝黑的男人,拉開木門,指著自己的頭頂客氣地問到。
我正背對著門,拿著手持式吸塵器吸著鏡子跟櫃子中縫隙的頭髮,被突如其來的客人問到(可見生意寥寥),剎時間還有一些應答不出。
「短髮,男生都算短髮,先坐吧」我回過神來答到。
「謝謝老闆,麻煩你囉!」男人露出一口乳白色的牙,微笑著說。
男人似如異鄉人,從輪廓、口音,到眼神都不像本地人,當他坐在鏡子前時,那高聳的眉骨,圓潤的鼻頭,尤其是那如曝曬成杉樹表皮的皮膚顏色,和那麥穗色的髮辮馬尾,都不像是在這都會中心的理髮廳會出現的客人,更像是某個海灘男兒或是職業漁夫,似乎是一位經過歷練的壯年船東,但不屬於那種不善表達的傳統男性,而是有些話嘮的屬性。
經過了一段的寒暄,簡單確認了想要修剪方向,從男人的粗獷的身後低著腰打量了一下造型。
「不好意思,雖然有些冒昧,想請問你是哪裡人?看起來好像不是本地人呢?」我問到,想開啟一個話題,並將理髮斗篷的魔鬼沾撕開。
「我是本地人喔~」
「你知道更西邊的地方,有個金黃色的燈塔嗎? 」
「我住在那個燈塔下。」男人試著用鼻頭指向那個方向,他應該是想用手指指出方向,但可能雙手都被黑色的理髮斗篷蓋著,不容易活動。
「我不太確定。」
「我記得那個方向有一個灰色煙囪,天氣好的時候,可以從頂樓看到」
「但我沒印像那邊有海岸,也沒真的靠近看過。」我說到,拿出兩個髮夾固定男人馬尾旁的頭髮。
「是你說的煙囪沒錯,實際上的確沒有海。」男人閉著眼睛,略帶微笑地說。
「沒有海的地方也會有燈塔嗎?真有趣。」我將男人的頭扶正,在鏡子前確認側邊的頭髮有切齊打薄,男子的髮絲較粗,茶褐色的髮絲掉落到黑色斗篷上就像是某種生物的鬃毛。
「準確來說,是目前沒有海,但在過去是一個小港口,因此才會有座燈塔蓋在那邊。」男人說到。
「這我倒是沒聽說過,是一個怎麼樣的港口呢?」男人勾起來我一點點的求知慾,讓我停下來電剪去充電,換上剪刀準備修剪後腦勺的雜毛。
「是一個不太知名的港口,也因為沒有多少魚貨或觀光,大部分的居民,甚至土生土長的在地人都不知道西邊有片內海,雖然海跟港口名不見經傳,但那邊卻有非常熟悉而溫暖的味道...」男人侃侃。
海、燈塔、內海和港口,這些不屬於都市的名詞,幾乎不可能在理髮的話題中出現,聽起來是如此飄渺而遙遠,即使我(自認)是學有所成的談話型理髮師 ,但這的確超出了我守備範圍。
年輕的時候,我在高校旁的理髮廳當學徒,是一間很傳統的小店,有一大片鏡子,沒有分隔的那種,老式的花磚地板還有墨綠色的不鏽鋼升降理髮椅,鏡子連接的桌子上,整齊排列著橘黃色的毛巾,每條都像剛出爐的老麵饅頭,散發著蒸氣,裡面的理髮師穿著更是復古,身襲淺青色的亨利領襯衫、黑色的紡紗長褲。透過櫃台的金魚缸,門外的玻璃窗映著赭紅色標楷字,寫著:「男士.純.理髮」。
這間理髮廳在當地小有名氣,除了剪髮技術之外,這裡的理髮師出了名的健談,當時的店長座右銘是:【沒有人喜歡沉默的理髮師】,因此每次理髮廳有三組以上的顧客在剪髮時,儼然成為一個喧鬧的早市,充斥著吹風機、笑聲、電剪和沖洗的聲音。
還記得在當學徒時,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店裡闖進一位慌亂的中年上班族大叔,穿著骯髒的襯衫,頂著的背頭髮型混亂,頭頂像是颱風摧殘過後的花圃,表情更是十足的缺乏養分,剛闖進來的時候,用極小的聲音拜託幫忙修剪頭髮。雖然有點不知所以,但來者是客,還是開始替他理髮。
經過了店長循循善誘的聊天技巧後,才知道原來是一個負債累累的大叔,為了面子不和家人商量,在走頭無路之際,決定要燒炭自殺,但想到自己身為一家之主,死的時候竟如此狼狽邋遢,至少保持一個整潔的儀容走完最後一程,因此來到理髮廳,希望我們替他剪一個簡單潔淨的髮型。
聽到這荒謬的故事,並沒有讓店長感到驚訝或是惶恐,反而是收起了平時隨興的態度,專注的修剪,彷彿士兵收到一個極其明確任務,身為愛國分子的他誓死都要完成使命,只見電推剪、長剪刀、剃刀輪番上陣,器械和頭髮漫空飛舞,經過一陣精細的修剪後,均勻的髮流從眉心向上延伸,平均且蓬鬆的髮絲整齊地以七三分配,兩側平推的高度也恰到好處,展現出俐落的層次感,並且也將鬍子和鬢角都修剪乾淨,整個人的精神狀態都正面了起來,面容也不再陰鬱。
店長跟那位大叔一同注視著鏡子前,煥然一新的樣子,沉默了一晌,只聽見店長對大叔說 : 「鏡子裡的這位先生,看起來是如此的英俊瀟灑,無論他碰上了什麼困難,他應該都能迎刃而解的,畢竟肩負一家生計重擔的他,都可以梳出如此漂亮的油頭了,沒什麼比這件事更厲害了吧。」店長的話有一些無俚頭,但這番吹捧意外的有效,能量好像從後腦勺毛細孔充進了大叔喪氣的皮囊裡,彷彿店長接觸大叔頭髮的瞬間插上了 USB 傳輸線,讓原本漠不相關的人,因為頭髮而能夠連結溝通一起,實在是非常神奇的事。至於,最終大叔是不是真的頂著那顆完美的油頭去燒炭,沒有人得知,也沒有人再提起了。
也許渾渾噩噩的自己晃了一圈,最終成為一位理髮師,也跟這個荒謬的故事有些連結吧,我想。
「曾今在這個都市的地區,被稱為羊島...」
男人見我有一些走神,錯過了一大段關於這片大陸的歷史,因此稍微放大了音量跟我說。
「羊?羊島?」
差點陷入回憶漩渦的我趕緊持續動起剪刀,修剪鬢角的部分,接著男人的話問。
「是的,就是山羊的那個羊,島嶼的島。」男人回答道。
「羊島的故事源自加拉帕戈斯群島,一個遠在太平洋的島嶼,在十七、十八世紀時人類開始拓荒,以拓展文明為口號,隨著航海家與漁民燒片原始家園的腳步,人類圈養的動物如同旅長跟班,一同開始拓張登島...」男人一如歷史文本的描述,彷彿換了一個人格,用著艱澀且饒口的語氣說著,像是傳唱著某個口傳歷史。
「那跟被稱為羊島有什麼關係?」我打斷男人,同時是急迫的求知、同時是想切斷這個攏長的細節。
「老闆,你知道高端的獵手,往往會以獵物的形式出現嗎?」男人挑起一邊的眉尾問到,沒等我應答,他繼續的說
「身為外來者的山羊,從原先的只有三隻,在島上無盡的繁衍後,種群擴張到四萬隻,巨量的山羊們將整個加拉帕戈斯群島的草地啃噬殆盡,原先棲息的巨龜,被山羊的過境淹沒,沒有了草地的陸龜,爬遍了島嶼,卻找不到一根嫩草。」男人持續說到。
「 山羊也太可惡了吧?」我下意識的回覆了這句話,情緒還有些激動。
「是啊,當時的人類也是這麼想。」男人冷靜的回覆。
「因此當地政府決策,以重回達爾文之島的名義,決定撲殺島上的所有山羊,以人類的姿態拯救島上瀕臨的巨龜,那個也曾今被人類以拓荒之名撲殺的陸龜。」一陣靜默。
「一九九七年,島上展開了一場屠殺,被稱為伊莎貝拉計畫,政府出動獵人、步槍、直升機、狙擊槍,而被稱為屠殺的原因,是因為這樣的殺戮並非為了殺牲取肉,而是為了讓羊群的能量回歸地力,所有被射殺的山羊就地曝屍荒野,直到化為塵與土。」男人喃喃。
「那不就如獻祭一樣?是邪教儀式嗎?」我不可置信,覺得這個故事越來越荒唐。
男人露出溫柔但有點滑稽的微笑,好像我又答對了某個賓果答案。
「邪教?老闆你聽過十二門徒和猶大嗎?」
「島上山羊在種群被人類大量滅絕後,獵殺開始越來越不順利,山羊們學會了辨識槍聲、直升機翼旋的噪音,一聽到聲響就會隱蔽起來,人類無法再有效率的滅殺山羊,於是自認萬物之主的人類派出了*猶大羊」男人補充說到。
「*猶大羊?」我不可置信的問到。
「是的,*猶大羊指的是人類訓練出來的領群牲畜,出生後唯一學習的事情,就是引領種群導向死亡,利用羊群的群聚性,帶領同伴前往屠宰場,而猶大羊最終也會被宰殺。」
「猶大羊被引入加拉帕戈斯群島,牠身上掛著 GPS,用衛星的定位來搜索羊群的位置,以便人類更進一步的剿滅,最終人類終於殺光了島上的山羊,而身為叛徒的猶大羊,也終將犧牲。」男人語畢。
夜幕即將邁進理髮廳的門簾,像一部掃描機,夕陽餘暉將店內的擺設都掃過,所有物品都丟失了原先的彩度,只剩下暖黃的色溫,桌上一把把金屬理髮剪反射出耀眼的光點,一如準心,瞄準在難以言喻的表情上,我雙眼直愣的瞅著鏡子,肅直的站在一張空蕩的理髮椅背後。
自從上次替那個男人理髮後,我再也沒見過那樣神秘的男人,或是聽誰提起過羊島的故事,就像做夢一樣,但卻無比真實,但那樣的故事實在有些荒誕,我也陸陸續續的替一些客人理髮,一度都想曾經開口提到羊島的事,卻又覺得彆扭、內心非常矛盾。
「老闆你看起來精神不太好,沒睡好嗎?」
「不過比起這個,你的手怎麼了?」某一個常客瞇著眼問到,他很想張開眼睛看,但可能有一些頭髮掉到眼睛裡面,只能半闔半睜,還流出了一點眼淚。
「手? 什麼手?」我回答到。
「滿手都是傷痕啊,而且看起來還很粗糙。」常客指著我的手說到。
「可能剪頭髮的時候不小心劃傷的吧,這工作常這樣。」我不以為意的說到。
「怎麼可能不小心劃傷的疤痕這麼深,好像還一路劃到手腕。」常客不解地說。
我也有些疑惑,但怎麼可能呢?怎麼可能無緣無故受傷,我特地將襯衫手腕扣子打開,想要證明常客只是看錯。
緩緩拉開的袖子,發現好幾道錯落的傷疤,從手腕一路延伸到掌心,切分開脈搏上的青筋,如暗紅色的河川逕流,反覆盈水乾涸後,結痂脫落後又增生,看起來像是曾經徒手攀登如此犀利的峭壁,又或是獨自與尖角猛獸拼搏留下的傷疤。
今天早早的關店了,又是快靠近黃昏的時刻,我站在店面頂樓的窗台抽菸,想起當初要離開理髮廳時的那天下午,店長也是這樣在窗台邊抽菸,找我做一個簡單的告別。
「小子,我一直覺得你像頭黑羊。」店長說到。
「黑羊?你說長相還是髮型?」我應到,還特別摸了一下自己的頭髮。
「不是指外貌,直覺的認為,又或是,嗯~性格吧?」店長眼神溫和,聲音低沈的說,不像是平常跟顧客說話的口氣。
「哈,是指不太合群的部分嗎?抱歉造成店長困擾了。」我刻意撇過頭說。
「你別誤會了,我並沒有覺得你這樣不好。」
「更進一步說,身為黑羊的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異端呢?又或者,你怎麼在與眾不同的眼光中,用自己的姿態活著。」店長把菸熄了,兩手交叉的靠在窗台欄杆,瞇著眼望向夕陽。
「我可能沒特別想過...但只是思考過別人是希望怎麼樣活著,來反觀自己的存在是怎樣的吧?坦白來說,我也沒太思考過自己。」我認自認平凡,不太知道自己是否是店長口中的黑羊,但,可以理解店長所說的格格不入的感覺,好像自己明明屬於這個族群,活得與種族不同的那種狀態。
「想起你第一天來店裡,全身血淋淋髒兮兮的,留著一頭不良的髮型,就像是一頭桀驁不馴的野獸。原本以為,勢必要有一場爭執,沒想到你卻突然跪下來求我收你為徒。」店長像是說著某個趣聞一樣的分享這件事。
「但那樣的你很特別,說實在的,我很羨慕你。」店長笑著說。
「特立獨行嗎?連混個不良都覺得被排擠,可能也是我軟弱的特色吧,覺得無法成為不良,只能覺得成為理髮師或許比較適合我」我說到。
「小子,我不覺得你軟弱。」
「選擇面對自己與種群的不同,並不是軟弱的人做的到的,所以大部分的人並沒有選擇,因此匯聚成羊群,而極少部分的人願意承擔『選擇』,成為了黑羊。」店長回應。
望著西邊,正是日落的方向,我努力搜尋,是不是有座,那樣子的金黃色燈塔,豎立在曾今的內海邊緣。
一抹沙黃夕陽無私的灑落光芒在整片大陸邊際,圍繞在工業區中,有座灰藍的煙囪,樹立在地勢較高得地方,夕陽餘暉的映照下,煙囪被炙燒出金黃色的外壁,飄散出的白色煙霧也被染黃,此時正當下班時間,一步步車輛從工業區緩緩駛出,車窗玻璃反射著極白的光點,好似一隻隻白羊在遠處竄行,整個城市正如一座島嶼,所有存在在島上的生靈,好像按照著某個規則航行著,停泊在指定的港口,但我僅僅是個遠觀者,對於平常人而言,稀鬆平常的日落和下班,對我來說卻像是羊群隨著時間推移,移動著,整片大陸彷彿海面,而白羊們活在名為城市的羊島上生活,而我,正如黑羊,靜靜的遠眺這侘寂的想像空間,最終將見證島上的黑夜,直到光再也分不清黑羊與白羊。我不希望奮力的抗拒社會,也無法坦然地擁抱人群,即使存在的矛盾感始終無法消弭,心態上卻是如此、如此的平靜。
羊島,DC, Oct.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