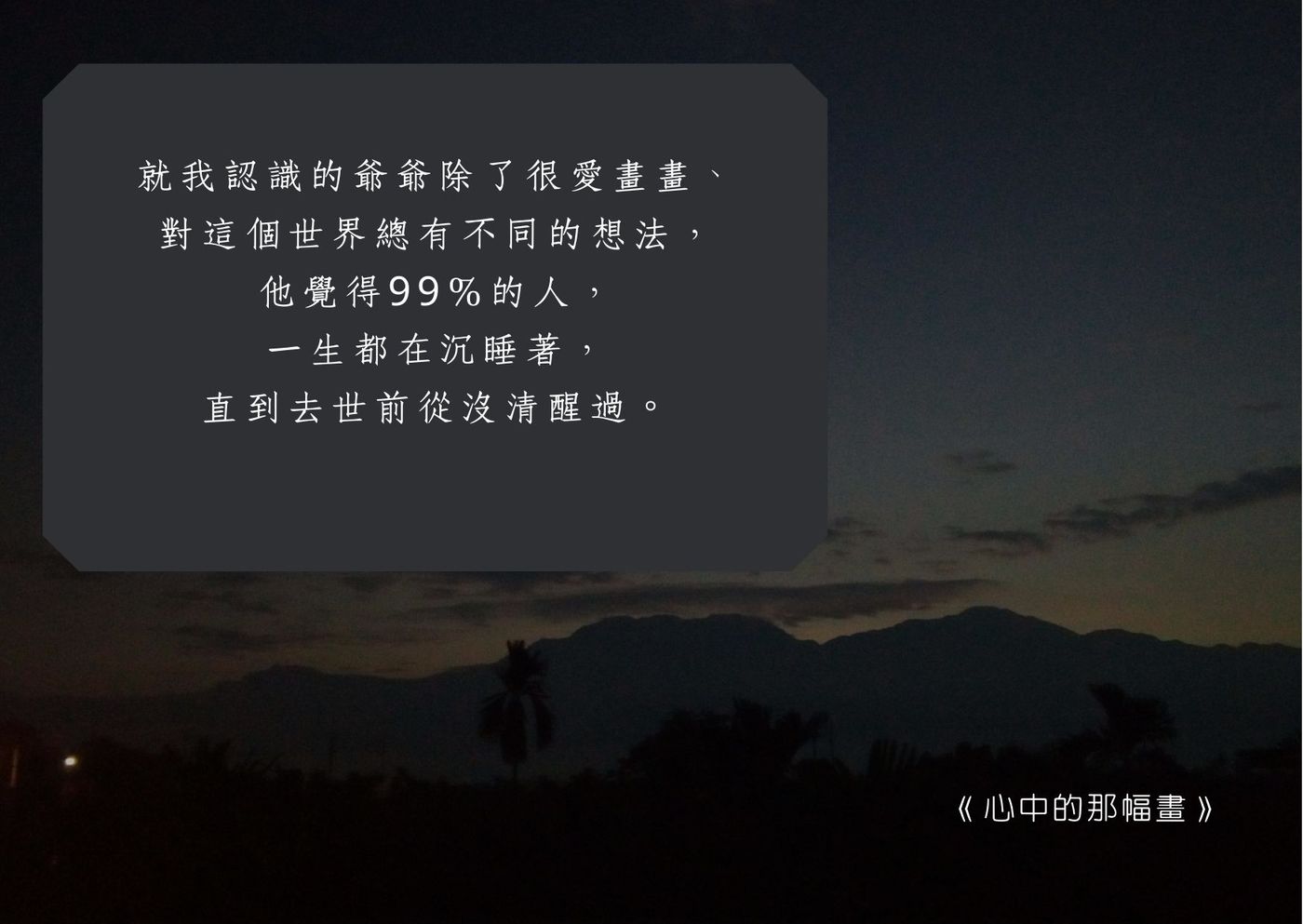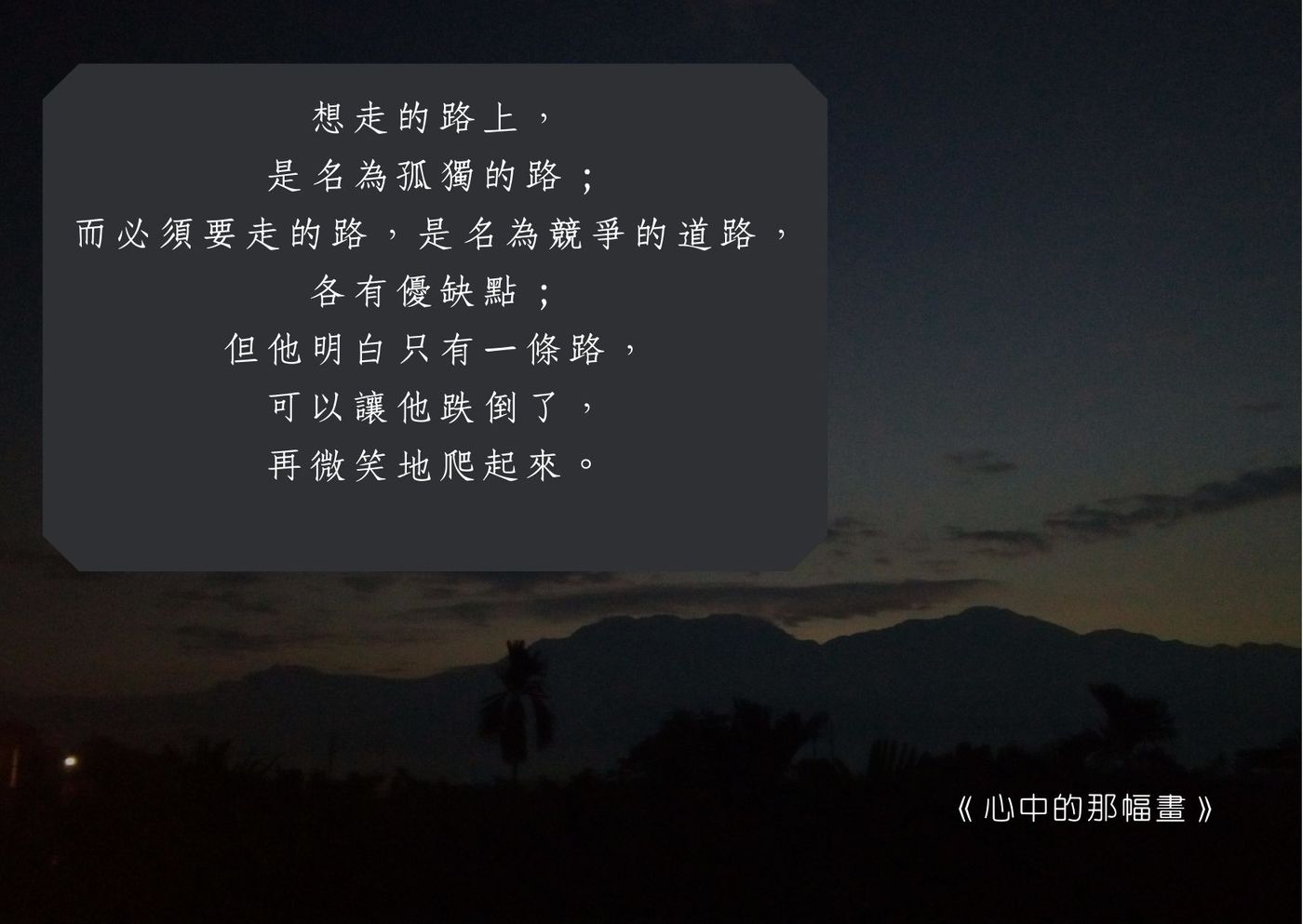我跟學弟認識是在他大一時。
同門課補修的我,碰巧發現他趁著午休在看動畫,沒有吃午餐,於是我上前搭話。
他說只是不餓,晚點再吃,便繼續埋首他的"命運石之門"。
剛好看過這部作品的我,便用它開啟了新話題。學弟眼前一亮,開始和我熱烈討論。
「你那麼懂,應該是ACGM社的人吧?」我說道。
他的表情卻突然沉下去,但很快地就回復成原來的笑臉。
「我沒有加社團耶,該說沒有動力嗎...」他靦腆的抓了抓頭。
學弟身材高高瘦瘦,一副斯文樣。皮膚偏白,不會有甚麼特殊穿搭出現,是個普通的人。
他說,家裡管教很嚴,禁止電子娛樂,每天頂多只有半小時電腦時間,而且常常拚死拚活完成作業,也只得到一句「很晚了,去睡覺吧。時間我明天再補給你。」讓他有些氣餒。
小時候被抓去上才藝班,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學些甚麼。如果抗拒,就會被罵「現在不多學一點,以後越來越忙就跟不上了!」「你要浪費我這個錢嗎?你不知道你爸要辛苦工作多久才能掙到這些錢?」「我是對你好,是為你著想。」
久而久之,原本就對與陌生人相處感到有壓力的學弟變得對「上課」有些恐懼。
國中的他是念升學取向的私校,課業壓力繁重。因緣際會下,他在才藝班接觸到了動漫,從此省吃儉用,只為了買輕小說作為收藏,算是生活中的一點樂趣。
「當時最開心的就是阿婆的100元贊助,或是從零錢和偷拿50塊錢。」我們都笑了起來。
但,也喜歡看書的媽媽看到輕小說卻十分反感,說是不入流的東西,要他不要再看,只能看青少年小說或推理小說之類他認可的書籍。像是賭氣似的,學弟繼續偷偷存錢買書,甚至會存多一點去買自學畫漫畫的書,除了課業以外,讓一直以來喜歡塗鴉的自己的能力也再進步些。
但某天,媽媽發現他的私藏書櫃,憤怒的把他叫過來賞了幾個巴掌。學弟只能跪著看著自己的書被一本本撕成碎片,倒進垃圾桶。
國三時,每天留校到9點。他也喜歡在課餘時間畫個小圖做為放鬆,後來被發現也是一頓罵。被抓包幾次後,他十分沮喪,開始害怕畫畫,覺得他一提起筆媽媽就會出現在他背後。
不過他也勉強擠進了第一志願的尾巴,「媽媽都是用心良苦。」
暑假時,媽媽說他喜歡畫畫,幫他報了素描課。學弟說想學漫畫,她則說素描是一切基礎。
一進門,發現都是國小或初中生,以畫畫為生涯目標努力的一群孩子。
媽媽覺得這種氛圍很適合學弟,但卻害慘了他。
身旁包圍著無數強者的環境,而且年紀都比自輕,讓學弟感到十分自卑。上完一期,就沒有後續了。
那種「難以望其項背」的絕望感,使畫畫從他的生命淡去。
有些運動都是相似情形,只是表達稍微有些意思,就會被超譯成想學,接著被拋進滿是專家的環境中,格格不入,處處顯拙。最後,他開始討厭與人互動。
「甚麼"不要害怕出糗",每次你犯一些低端錯誤在場大佬的臉色就會越來越難看你知道嗎。」
升上高中,相對開放的生活,媽媽也放手讓學弟自己準備課業。但被私校壓了三年,解放之後就是一盤散沙。不會排讀書計畫也不念書,每天只是直覺性的摸到很晚,根本沒做甚麼。以往的興趣也沒有再提,只是渾渾噩噩度日。
學測爆炸,指考爆炸,接著重考。
勉強考上了偏前段的科大,下定決心要好好努力。但像微積分之類的還是被當掉。
「班上的同學似乎都對這個領域有興趣,是有熱忱的東西。但對我來說就是地獄。」學弟說道。「我這時恍然大悟,為甚麼不去修自己喜歡的課呢?」
「那你做了甚麼?」
「想去加選設計系的課,想說跟畫畫有關,卻發現大學的課程早已是專業領域,以我的能力根本無法負荷。一個被壓制到放爛7年的興趣,還剩多少熱忱從0開始?」學弟聳肩。
他放棄了,回到自己熟悉卻不擅長的理科世界,試圖每天在各門課中找一點趣味。
「我沒有膽直接轉系,畢竟根本沒有看過他的運作方式,盲目只是死路一條,也沒有足夠的衝勁。」
每次在跟同學吃飯,他們在暢談理想和自己的努力時,學弟都會感到十分自卑。
「沒有目標沒有夢想,本分做不好還不知道自己喜歡甚麼,每天只是照著課表出現在課堂上上課。」學弟的表情再次淡下。「我不知道要怎麼做。想做一些事情卻常常被恐懼壓下來,但也不想再做自己不喜歡的事了。」
意外的,我得知了他有女友這件事情。
「她是我高中同學,算是支撐我重考壓力的偉大之人,也是少數會正面評價我的人,也是我這個漫無目的的人現在唯一還活著的理由。」學弟打趣著說道。
但幾個月後,聽到了分手的消息。女方似乎覺得對方不適合自己,想結束這段關係。
學弟似乎也很快答應了,還開玩笑說「你找到新男友後,我會把你的祕密全部抖給他。」
我為此又找學弟出來吃飯。
他的臉色一如往常,但抹上一絲惆悵。
「我早就知道我不適合她。她的目標明確、踏實努力前進,我這種人根本不能陪她走到最後,反而會成為她人生的汙點、絆腳石。這個世界上比我好的人多的是。」
學弟的情緒有些負面,我點了一些酒,緩和一下氣氛。
但學弟沒有多說些甚麼,只再跟我打了點屁就離開了。
三天後,學弟在自家房間燒炭自殺。
據說他當時是笑著死去的。遺書上只有兩個大字:「謝謝」。
連死去都如此安安靜靜,告別式也平平淡淡,只有一些親戚惋惜他太年輕不惜命,但在社會責任和道德義務落在自己身上前這時離開人世,也許是他最嚮往、最滿意的結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