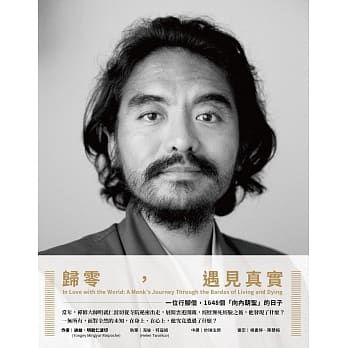📘學習範疇
死亡之後:一個長達五十年的瀕死經驗科學臨床研究
📝學習心得
這點很有趣,換句話說,瀕死經驗有可能是輪迴思想的起源。幾乎每位曾經有瀕死經驗的人,都相信某部分的自己在死亡後繼續存在。無論他們認為死後會發生什麼事,他們都不認為肉體的死亡是自己的結局。
大腦活動的降低,可能也削減了大腦的過濾能力,讓人經歷了神祕體驗。這和世界各地的靈性傳統一致。這些傳統利用窒息、閉氣、飢餓和長期的感官剝奪來引發神秘的體驗。
而宗教的修行法門,是否是在於降低大腦的活動,而想復現瀕死經驗呢?
我大學時有過瀕死經驗,確實瀕死經驗改變了我本身,在那之前我根本不愛讀書,在那之後則想在書中找到這特殊經驗的印證。
會接觸身心靈領域的,有的是遇上人生的煩憂、有的則是想驗證特殊經驗的解釋,又或者兩者皆具,瀕死經驗、禪修經驗、恐慌解離經驗,這幾種都有離體感,也的確如書中所寫,瀕死經驗常產生正面效果,而精神疾病則導致負面效果。
不過,如果這種離體感是在精神疾病解離症中可復現的,那麼這種「我可以離開身體而存在」的經驗有可能只是生理運作機制,解離症可以靠身心壓力而誘發,似乎跟苦行僧的修行方法類似?
換言之,以前說過修行的關鍵在於「有意識的受苦」,但是否會是透過微調身心受苦的壓力,來達成輕微解離的狀態呢?因為只要達成解離的狀態,就更能接受輪迴的思想,而輪迴的思想卻有可能是在前人解離狀態後寫出的理論?
再者,「離蘊我」是佛法所不承許的,這種解離的經驗似乎比較接近普遍的「常、一、自主的我(ātman)」,可是佛法認為沒有「離蘊的我」,那麼似乎否定了有個輪迴的主體,換句話說,認定有個輪迴的主體,是否就是會認為其「有自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