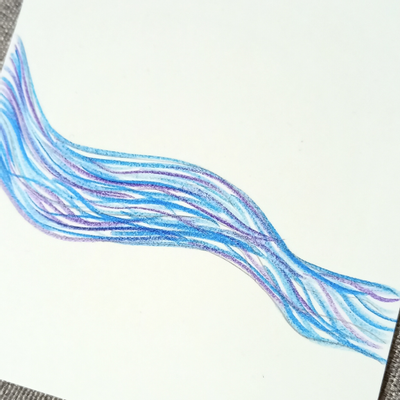十六歲時我開始聽陳昇,拷貝了一張沒有名字的專輯,裡面有個男人喃喃自語。
他說了沒有顏色的夢,說了滂沱大雨,說了迷路的候鳥,我聽著心都碎了,又聽到心慢慢痊癒。他說了遙遠的地方有個小村落,彼時我還不諳台語,覺得那首歌好美,知足而美,緩慢而美,因被世界遺忘而美。
彼時沒有想像過人生,更不知道有朝一日,我會時時經過這個小村落,它從現實浮現,倚在破碎充滿悽愴的公路旁,它有什麼樣的命運,而我們又怎麼在廣大的宇宙間牽引彼此。十六歲的海很藍,我牽著心愛女孩的手被粗魯的礁岩割破,夜裡我們反覆唱,反覆唱,唱姑姑在寒風中,唱新店溪的細漢仔,我總是一遍又一遍,像是吹在草原上的風。
彼時我選了個名字,後來在昇網延續著用,叫做南風。但有太多個南風,每個心還不能死去,雙手攀在世界邊緣的女孩,似乎都叫南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