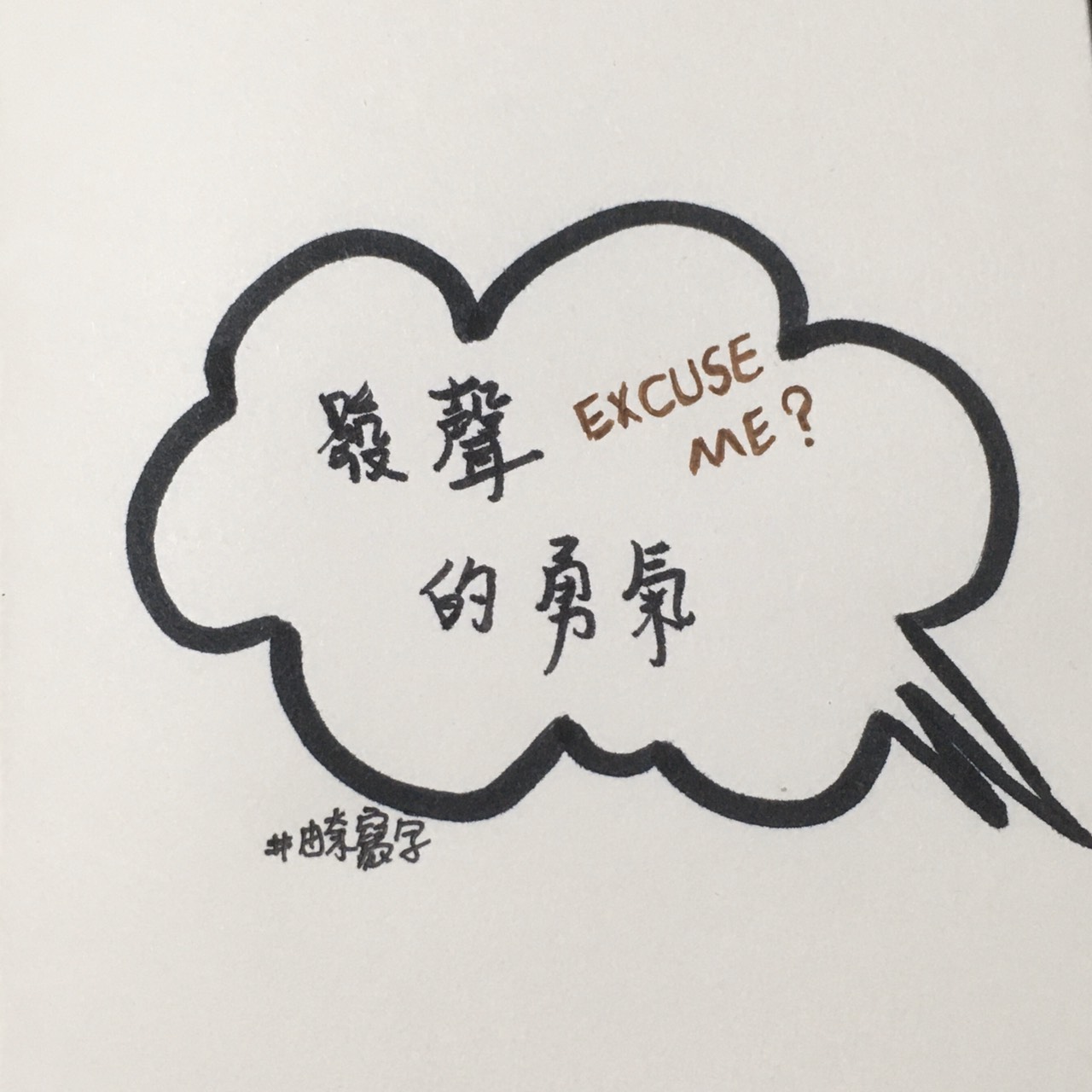二號觀察者
「我以前不理解,為什麼人非要打破自己所建立的規矩。」
「因為法規,我的業務內容相當明確,每天的排程也被安排妥當,根據種種指示,可以明確地跟隨上層所有安排,一切井然有序。但是,仍有不屑這套規定之人。」
「若是被抓到,是免不了或大或小的罰則—有個部門就是專門在記錄各種證據,以供舉證違法者的行為。當然,我也聽說不少地方的紀錄部門根本形同虛設,只能對各種違法行為默不作聲。可我不認為紀錄部門的運作情況對違法者的增減有什麼效果,例如我們這個據點,早已設立紀錄部門,卻對那些違規者沒有一點嚇阻,守法的仍守法、叛逆的仍叛逆。」
我曾好奇為何要違反以保障整體安全、和諧為目的的法規,但久而久之,我理解了—又或者是說我釋然了。
為數龐大的人群之所以要取個均質,正是因為當中有零零散散的不同訊號,取個中間值,讓所有人的犧牲在平均上能最小化。
每天看著密密麻麻的人、車,龐大的數據近乎令我可以判斷,每個判斷將逐漸累積為過去,而斷定過去就能決定未來,這道理我是清楚的,卻無法依此運行,畢竟我的工作是負責表現規範,讓大家能有個依據而已。
那些所謂
「請通行。」
能決定未來者,八成也是設立種種規範的人吧。
那些負責整合、建立規範者必然是少數;拒絕遵循現有規則、試著拆毀框架者想必也是少數。作為常態分佈的兩個極端,彼此一定有一些近乎默契的連結,你規範、他打破;你為了自己的方便—統治也好、管理也罷—而建立;他為了自己的方便—大義也好、自私也罷—而破壞。這城市裡大多數的人真可悲,任由極端兩邊的少數擺弄。
我釋然了,畢竟違反規則本來就是他們安排好的一部分,所以說,我那小小的無力感以及衍生而來的微不足道的
「行人請停止。」
罪惡感終
「行車注意,準備停止。」
於被化解
「行車請停止。」
了。
不過,我並不因這種「了卻感」所帶來的安逸而放棄做精神上的自我爭論,與之相反,我有了更多思考的餘裕,甚至為自己設計了許多精神上的小遊戲。那些娛樂已不再拘泥於分析的正確與否,只是單純的......自娛又或是自我滿足。
總之,穿梭的思緒間充滿了不完善的臆測與空想。
我開始猜想那些行經此處的人、車是分屬哪一類,是屬於那多數者還是極端中的任一側。當然,我的評判標準也參雜一些較為「世俗」的目光。
例如那些豪車華服者,甚至有交警、專車為其開道,多半是傾向於建立規則那一端,反之那些衣屩藍縷,普遍被認為無法在那諸多規則中安身者,較有可能屬於打破規則那側。當然,無論傾向哪一端,其實都有遵守規範者與對此不屑一顧人。
於是在多數與個案間可以來回擺盪—是不是位於建立規範那端的人們也能打破成規,而骨子裡便無法適應教條之人,也能對他遵守不了的框架肅然起敬。
我見過名車香馬肆無忌憚的橫行,或僥倖逃逸、或造成損害及傷亡;推著破爛推車的婆婆步履蹣跚,跟不上號誌,只能停在分隔島中等待下一個綠燈。所以說,這是多麼有趣啊!永遠沒有正確答案可以妥善地歸納他們
「請通行。」
,真好奇他們自己是否清楚這些。看!那個西裝鼻挺的男人,他始終盯著手機,從未抬頭看我的指示,待周遭的人隨著倒數—5、4、3、2—緩緩向前靠近,他便跟著向前踱步,其他人邁開或大或小、或快或慢的步伐向前—1,他就跟著抬起左腳、右腳、左腳。
倘若不去細看,還以為是個遵守規則的人。
但他其實不在乎,又或是說他預設了這些規章會給出一個安全的最大公約數,明白這個時刻該如何才能規避風險,要怎麼做才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我尋思,是不是有像他這樣的一群人,對諸多規範有
「行人請停止。」
著概略的
「行車注意,準備停止。」
認識,但
「行車請停止。」
從不在乎規範從何而來、為何而立。
「沒差,能夠符合我的利益就行了。」
當然,他們並非認同那些被創建、用以保障最大公約數的法則,而是只要能滿足自己就好。也可以這樣說,他們有自己的一套戒律—畢竟我深信無人能活在沒有規則的世界裡。
但我不會用自私來形容這類人—應該說大家對「自私」這個詞添加太多負面的情緒,過多的誤解與濫用累積成深鎖的眉頭,始終放不開。人的一切行動本來就是為了自我滿足,這是再正常不過的機能—是無法、更不需要去擺脫的。許多人都費盡心力地透過各種包裝去修飾,可到頭來仍是同樣的東西,換湯不換藥,頂多起個新名字。
這樣說好了,我常看到行人與行車之間有摩擦—本來想說的是「非物理上的」摩擦,但仔細想想,若發生了「物理上的」摩擦,通常也會伴隨口角、觀念上的摩擦,就拿昨天晚上的案例來說。
當時有位老先生正穿越馬路,防寒的厚重外套尺寸有些過大、不太合身,右手拄著拐杖的他,踏著細碎的腳步走在斑馬線上,有點像馬陸,儘管有著急促的節奏與綿延不斷的步伐,但幅度過小的間距令他如馬陸一般,只能急促地緩緩向前,身旁忙碌的行人來回穿梭,更凸
「請通行。」
顯了老先生的脫節與乏力。經過一番搏鬥,在下個指示將被給出之前,他終於走近人行道的另一端,大概剩一公尺不到的距離。可就在此時,一輛右轉的汽車不想被紅燈給困住,於是他在轉彎時選怎少採一點煞車,當然他也沒有順勢朝老先生撞上去,並逃之夭夭前往他所趕著抵達的地方—好吧!確實有些人就做出了這樣的選擇,但至少這位駕駛沒有這麼做,車子在距離老先生莫約半公尺左右處止住了,急煞的震動令整台車前後搖晃了一下,就在此刻,另一方向的同事剛好切換了指示,於是汽、機
「行人請停止。」
車洶湧而
「行車注意,準備停止。」
出,一齊
「行車請停止。」
壅塞於那台卡在轉角等候老先生通過的汽車後方或左右—因為當時內側車道恰巧有輛公車經過,所以才可以這麼完美的擠成一團,此時一位原本已經走上人行道上女子,回過頭上前攙扶那位老先生,陪著他緩緩向前,同時另一位男子也轉身走到那台被卡住的汽車,在車窗附近惡狠狠地瞪了那位駕駛一眼,最後老先生平安通過,壅塞也解除,各個角色逐一退場、散去,只有老先生仍拖著緩慢的步伐,最後一個走出這個舞台。
我們儘可能地仔細分析—我之所以說「儘可能」並不是因為害怕自己不夠仔細,但多少還是有出自謙虛而覺得自己或許仍有犯錯的機會,也許就在未來—而是因為我們可能沒有這個時間去做如此精細的釐清,大多數人都會指責那位汽車駕駛,並對那些攙扶他或是想為他出口氣的人給予讚賞,並且套上我們想討論的「自私」這一問題的話,那位汽車駕駛應該是自私的—普遍認為的自私,他為了一己之目的或滿足,把自己放在比老先生更優先的地位。
但若是換個角度思考,那對男女呢?他們會不會也只是出於某種信念而覺得那位駕駛應該要把老先生放在比自身更優位的地方,也許是法規、也許是個人喜好,但兩者之
「請通行。」
間似乎也沒什麼差別吧?正是因為他們認同—就算是無意識地認同—能在這樣的規範下順利地生活,在這個形狀的烏雲底下,他們渴望的、想要的東西並不會受到隔絕,也許順著規範走的同時,那些東西反而顯得不易取得,但同時也是一種保證,保證你只要經歷困難便可以得到,一種低風險投資。
也就是說,正是因為他們可以在這樣的規範下得到滿足—自我的滿足,所以他們順著規範的目光,用那不悅的、排斥的眼神去斥責那位駕駛。我們可以說,在這個情況劇下,那對男女可能得到一種間接或是直
「行人請停止。」
接的滿足
「行車注意,準備停止。」
,也可能
「行車請停止。」
同時都有,基於規範所隱含的保證而選擇順從,所以在這個看似與其自身不相關的時刻,其實正在侵犯他們所賴以維生的框架與依託,因此他們必須去捍衛,做出某些行動來抒發內在感受到的詆毀,然後對著異教徒宣洩,從而得到神性的滿足。
還有一種直接的滿足感,是出自於他們對這些規範的無知,出於無知,他們選擇了認同,甚至是喜歡,儘管那些規則不能夠保障他可以獲得什麼東西、任何東西,進而被填滿。相反地,這個規則的實行就是滿足的來源,某種近似薛西佛斯喜歡上將石頭推上山巔這件事一樣。
但我必須申明,我對他們這樣的「規範愛好者」以及薛西佛斯都無貶義,每個人都有權利享受自訂的幸福。
接下來可以大膽一些,用自我滿足的論點去看看那位老先生。當然,一定會有人覺得這是檢討受害者,畢竟那位老先生也不是刻意走這麼緩慢,有著不可抗拒的因素存在,不過我們先來確定一件事,那位老先生應該是知道自己行走不便的—若有忍不住想指責我的人,麻煩待我給出完整的分析,在他明知這些預設條件的情況下,他仍選擇通過這裡,不也是做出了某個選擇,因此也應該去承擔各種躲在規範後面的風
「請通行。」
險,當然,我清楚這條路也許是最近的一條回家路,又或者他沒錢搭車等等,可是這些用來闡述「沒有選擇」的形容,在我看來都只是象徵著他已做過了某些選擇的證據,然後無數抉擇不斷積累,直到這一刻,他選擇不遵守規範。
這說法並不荒謬,他的自我滿足就是要透過適時貶低某些規範才能被填滿。看似遵守指示,在通行的指示下來後才前進,但事實上他清楚自己在限定的時間裡根本來不及走到對面。
「無所謂,我要過去。」
他明白規範對他並不友善,若是完全順從,可能得繞上好大一圈
「行人請停止。」
才能達成
「行車注意,準備停止。」
他的目的
「行車請停止。」
,所以他在那些規範危及到自我滿足感時選擇無視,老實說,他們是高級玩家,知曉總有大多數人會選擇乖乖遵守規範,畢竟,當我們回頭看看這整幕演出,汽車駕駛人到底是沒有違規,反而是那位老先生在紅燈時仍未抵達人行道,進而導致路口短時間的阻塞,而那些看似熱心的人,一同走在斑馬線上的時候,也只是選擇穿過那位老先生,誰都沒有伸手攙扶,明明他的不方便一直都在,可是在規則備受到威脅前卻是誰也都沒有動作,這應證我的論點—沒有誰是真正在乎那位老先生的困境。
所以我可以打趣地說,唯有老先生是真正不遵守規範的人,但為了避免有任何人對我言詞有所誤解,容我特別解釋一下關於老先生的委屈。我雖然也只是依照規範行事、作業,但從未將之視為真理,一如我所說的,老先生為自我滿足而選擇不遵守規範,有些人道主義者會說:「真正的問題是出在那些規範上,他們為求最大『利益』而不優先選擇那些如老先生這樣生活有所不變之人。」
此刻又得自我開脫一番,我並不因此對現行規範有所批評,那些規則—誠如我先前所說—是由一些少數人所建立,試圖尋求一種最普遍、但也最滿足他們自己的規
「請通行。」
範。
正、反兩方的看法我都不以為意,所有人都只是為了自我滿足罷了,根本沒有什麼正確或錯誤。
但裝做超然抽離、事不關己一般,彷彿真能做個自以為是的絕對觀察者並不是我的目的—自己不過是個小齒輪這點我是清楚的,渺小的齒輪又怎麼可能做到置身事外呢?
我只是想對大家將「自我滿足」貶為「自私」一事做一些平反罷了,再者,這也只是從我那些小小自娛得來,一個微不足道的結論,在這個有規範卻無是非的架構下,我的空想與實在的規律是同樣的無足輕重。
乍看之下,我的釋然很
「行人請停止。」
像有一些
行車注意,準備停止。」
無奈的色
「行車請停止。」
澤。
確實,如果是那個曾經拘泥於表面的我,必定會瞧不起「釋然」這一回事,不過許多轉變往往要親身經歷、體驗後才能體現,最直接的改變莫過於這種觀念上的轉折。雖然我們往往很難去掌握那個切換的記號,通常都是用一些相當曖昧、模稜量可的形容詞來宣稱,將前後不同的延續狀態漆上各自的顏色。
這感覺就好比試圖於人、車在停止與行動的轉換間找到明確的節點。當你站在遠處,用餘光來確認時,好似真有一個啟動的片刻,但當你定神聚焦,又彷彿是無窮級數般不斷往後退,永遠抓不住其輪廓。
這也就是為什麼要把人們量化的原因吧!將之化為數字,整體化後凝結成一個龐大的結構,一個擁有輪廓—但也只有輪廓的宏偉神像,其內涵缺失,所以不會陷入永無終點的探尋之中,那些光怪陸離的煩惱就留到個人的時間去處理。
這就是為什麼我宣稱誰都無法脫離框架而活,倘若沒有這些加工物來拘束,落入那無可避面的無底洞時,豈不是連存在都難以維繫?
所以大家都活在各式各樣的規範中,時而順從、時而叛逆;打破規範這件事同時就是創造規範,多麼漂亮的循環。
看著人潮累積又消散,若不仔細觀察,誰都會以
「請通行。」
為他們是由複數個相同單子組成—一個龐大有機體,這一刻匯集,下一刻崩潰,而我在這反覆輪迴間取樂。
但誠如我說過的,我深知自己不是懸掛在一切之上的旁觀者,觀賞、分析的同時,我也隨之變化。
在那個追求平穩與效率的女子心裡,我酷愛唱反調,總是等到她接近後才改變指示,非要她一路不順遂;在那對濃情密意的年輕情侶眼中,我是不解風情的傢伙,永遠不懂他們此刻需要什麼—多一點擁抱的時間?還是不發一語的肩並肩。
啊!有看到那個衣著陳舊、留著凌亂長髮的男子嗎?我們來賭
「行人請停止。」
他會不會
行車注意,準備停止。」
闖紅燈。
「行車請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