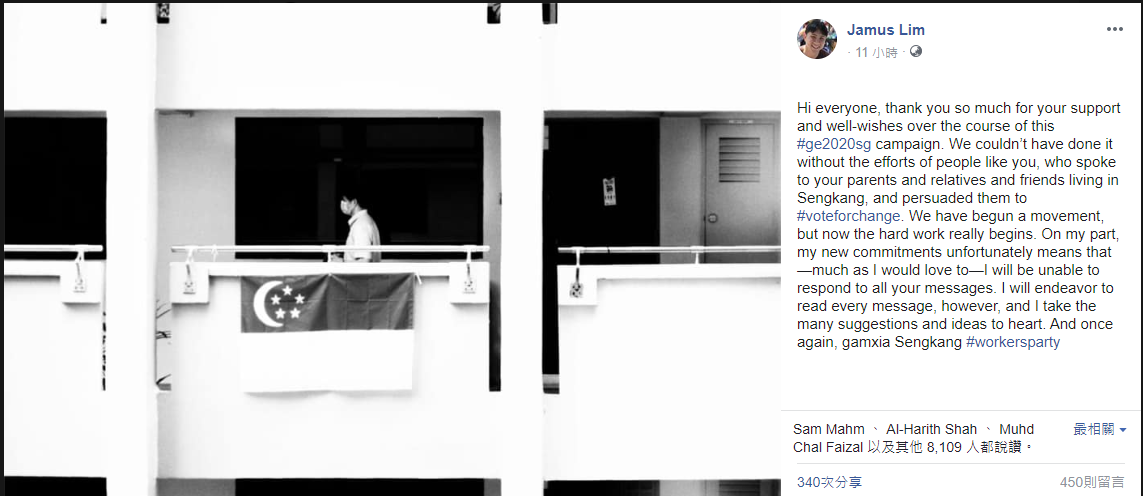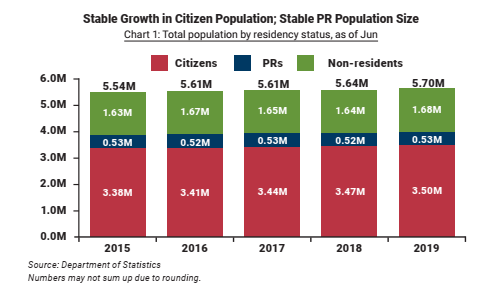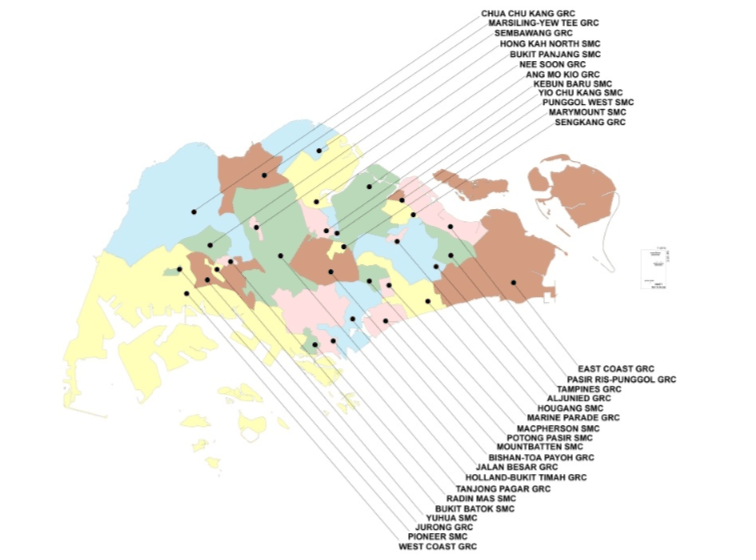反對黨應堅定承擔穩健制衡的重大責任
2004/03/21
張登及 蜂報刊於03/27
台灣的大選在驚濤駭浪中暫時告一段落,結果全世界都看得目瞪口呆,其戲劇性絲毫不亞於成龍電影的「奇蹟」。但現實是我們不能坐視台灣變成「情義之西西里島」。而且地域分化、認同撕裂、族群對立與其導致的人際互信和命運與共感的日趨崩潰,使得形式上符合一切民主標準的台灣,「情義」只能存在於政治認同一致的各個人群,而社會生活的全體則人情日益淡薄。只要技術上找不到犯規之處,各自捍衛的認同可以合理化任何權宜。連「視病如親」都可以變成因黨施藥和黨同伐異。誠實、反省、自制‐成為稀有品種和政治自殺,論證推理只須符合建構霸權論述的邏輯。
這種情勢已非一朝一夕,但最近的選舉政治使它變本加厲。許多曾廣受尊敬的人士提出多次沉痛呼籲, 換來的竟然是槍擊元首、陰謀漫天,甚至可能是一場無效的選舉。我們的社會還要因此付出多大的代價尚不可知,但至少筆者記得中共曾說,島內發生變亂就是犯台的前提之一。這或許可以解釋何以美國願冒干涉內政之不韙,公然要求約見我國總統參選人。因為台灣政治生態的趨勢,已經像是走向一條無法回頭的軌道上的火車,軌道另一端也有另一列拒絕暫停的赤色列車漸漸駛近。那赤色列車也想改頭換面,提升其「乘客」服務的品質,偶而也踩踩煞車,但國際政治結構的軌道就是在那裡。美國實力不足以改變軌道本身,又不願自己上車加碼,只能在軌道上放石頭或者向兩車駕駛吹哨、打旗。如此比喻台灣外部局勢並不誇張,近來多本西方專著,都說台灣是本世紀國際結構中最危險、最脆弱的地區。
悲劇性的台灣史與國際強權政治共同為這條歷史軌道奠基,所以僅僅歸咎幾個領導者曾經譁眾取寵、飆車冒險並不公允。國民既然已經將開車的主要使命做了委託,如何駕駛最少有各種成法可循。但不可能是所有乘客時時刻刻來到前台指手劃腳,自然要有另一個預備隊幫助大家監看情況。在駕駛團隊有負委託時做好啟動備案的準備。對一個國家來說,幫助監看而不是搶駕駛盤才是反對黨的重責大任,此使命之重,並不下於開車本身。
兩黨制是多數先進國家發展民主的基石,而在野黨職責就是扮演好預備隊和監察員的角色。現在台灣的最大問題不在於哪個駕駛團隊—執政黨獲得多少授權,甚至也不是授權程序有多少疑點瑕疵。今天選舉結果就算勝負雙方易位,奔車朽索的危局仍然存在。
問題癥結在於執政思維與競爭授權方式的同質化,正使台灣隱然走向長期一黨制的局面。而這個「新一黨制」與日本一九五五體制的差異在於異質面的凝固化,和疆界分明、根深蒂固的敵視。這很容易使得駕駛團隊沉溺於獨占與擴大同質性的支持,其視野將日趨固執狹小,自滿於在危險軌道上競速賣藝以取悅同質支持者。此時,監督者爭搶駕駛權則只會使過程搖晃不安,招致擾亂者的惡名,並被邊緣化為異質的局外人。不論對個別政黨興衰利害的關心,此種病態趨勢對全體社會而言都極為危險。一個在野黨‐變成恆定、異質的政治局外人的社會,領導團隊將失去制衡監督,其自由多元的品質將逐漸消失。面對外在環境艱難的局勢,更難以提出有助於逃離災難性軌道的創新方案。
現在在台灣,要甘於屈居制衡監督者極為困難。老實說,從解嚴至今,主要朝野政黨從沒有一天好好扮演過忠誠反對的制衡監督角色。歷屆主要在野黨派不是日夜苦思將對手鎖入異質包圍圈,就是天天想趕當時的駕駛員下車。這使得國民誤解制衡監督就是唱衰搗亂,造就了新一黨制的溫床。目前的反對黨在此次選舉中可說稍改以往反對文化的惡質作風,但在受到突發事件衝擊導致努力付諸東流後,出於未得澄清的疑點和引起的激憤,又萌生了抵制到底、趕人下車的想法。這只有再度加深部分民眾「搗亂唱衰」的印象,提早催生台灣「新一黨制」的降臨。反對黨自戕事小,無制衡的畸形民主與凝固化的對立橫行事大。
今天,全體國民以一半的選票授權執政黨繼續開車,也用一半的選票託付在野黨去監督這個駕駛技術和品格都不能令人滿意的執政黨。國民的授權過程有否受到非法方法之影響而造成結果之改變,自有裁判人員會去仲裁。
仲裁結果往往不盡如人意,但這就是歷史對現階段台灣命運的宣判。如果在野黨有遠見發現這個命運軌道末端藏著巨大的災難,也只應戒慎恐懼的面對並提出備案。因此可以說,這個責任甚至比執掌政權更為沉重艱鉅,特別需要以大包容、大智慧,建構具有競爭力和說服力的替代論述,堅定不移地抗拒將台灣多元民主鎖入同質化以對抗異端的危險趨勢,才能為民主的兩黨制和台灣前途保留一線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