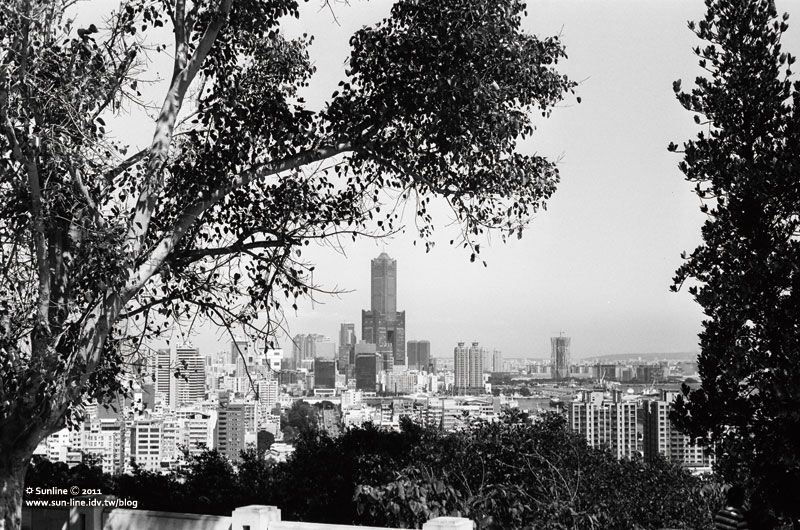書摘文字及圖片由臉譜出版提供
數位拍攝的可能性和極限
說到二〇一〇年當時,底片攝影的失勢已到了兵潰如山倒的階段。之所以答應接拍,是因為我想用自己的手去確認:到底數位攝影能拍出什麼程度的「戲劇」?能否拍出虛擬的世界?尤其怪談應該是最不適合數位攝影的劇種。因為無法全黑、又很難表現出氤氳效果。使用的機器是 CANON EOS 5D Mark Ⅱ 的數位攝影機,深度相對較淺、也有氤氳效果。如何呈現暗處對怪談而言很重要,我想挑戰看看。
例如晚上的戲。我要拍的畫面是:日式房屋的房間裡掛蚊帳,在昏暗的燈光下,浮現出夫婦的身影。麻煩的是房間不弄暗,看起來就不美。因為在明亮的房間裡看,電視畫面上會映照出自己所在的房間。但又不能要求觀眾「關起燈來看」,所以有點困難。
因為是數位所以理所當然,但我很不習慣用「資料」稱呼拍攝的東西。而且拍好的資料有些會打不開,不管用什麼方法測試,最後就是打不開。從此以後,為了確認資料能否打開,每拍完一個鏡頭就得將資料存入電腦,檢查能否播放。感覺實在是很浪費時間。
當然拍攝紀錄片時也多次使用過數位錄影,但因當時看得見錄影帶轉動,知道機器有在拍攝,所以感到安心。從底片到錄影帶,如今是記憶卡,存錄媒體的質感越變越輕巧,老實說我有點跟不上的感覺。放諸世界,勝負的關鍵也在於能否因應此一變化。
比方說用數位拍攝《挪威的森林》的陳英雄導演,他的想法就很明快。他說「許多人用數位拍攝犯的錯誤是想要模擬底片拍攝的質感,所以才會失敗」。也就是說,數位應該有數位的長處,不須對底片抱著念念不忘的鄉愁。他還說「我們其實是用數位式在觀看真實世界而非底片式,應要反映出那種感覺才對」。他認為應該有意圖地拍出平板而清晰的畫面。不過這是否符合《挪威的森林》的世界觀,我個人是有些存疑的。如果要實現他的想法,恐怕攝影師就不會找始終用底片攝影的李屏賓吧。
攝影機存在於中央的風景
EOS 5D Mark Ⅱ 的合格點在於好用和成本便宜。
比方說,應該比學生過去用的品質壓倒性好很多,至少能拍出清晰的影像吧。
但是攝影機也壓倒性輕很多。
儘管有優缺點,但因為攝影機沒有存在感,在自然拍攝兒童時,比起裝底片的大型攝影機會發出聲音轉動,所以能拍出自然的東西。是可以讓拍攝對象不會緊張、便於進行突擊式拍攝的機器。可是在移動攝影時,數位攝影機的輕巧感就會呈現在畫面上。
我不太想提精神論,然而需要三個人才搬得動的攝影機鎮守在拍攝現場正中央的風景,就像是被「這就是現場」附身的必要瞬間。我覺得攝影機還是應該具備某種程度的重量吧。
而且如神明附身的笨重攝影機,也有讓所有人意識集中的好處。由於 EOS 5D Mark Ⅱ 太小,只好將影像從攝影機拉到電腦螢幕讓大家看。不是攝影機和演員所在的地方,現場的意識必須集中到電腦螢幕上。這種事有好有壞,或許有的演員能從緊張感中獲得解放,另一方面現場所有人都集中在戲劇本身的好處也會逐漸消失。
拍好的東西瞬間成為電腦畫面或監控畫面,恐怕是受到某些寫真攝影師的影響吧。
為李相日導演的《惡人》、《大和殺無赦》、阪本順治的《老子拚了》、《顏》等掌鏡的笠松則通是代表日本的攝影師,他很擔憂「攝影師自己都不相信攝影機了」。
正是像笠松兄那樣傳統的攝影師,連自己的助理也不給看攝影機濾鏡。我剛當電影導演時,還曾猶豫該不該要求「拍出什麼畫面,給我看一下」。當時還沒有監控畫面可看。
大概電影現場除了攝影師以外的工作人員和演員都能輕易檢查監控畫面,在日本是從伊丹十三導演才開始有的吧。因為伊丹導演有電視現場的經驗,不算純粹的電影人,所以才會做出那種嘗試吧。
底片上映會自然變成3D!?
還有說到數位,會有「萬一有什麼,事後都能處理」的觀念。比方說,可以去除拍攝時不該入鏡的東西(稱為「抹除」)。固然很方便,但因為會削減對每一瞬間的集中力,那種一決勝負的張力感也跟著消失了,所以也是有好有壞。
聽說今後的數位攝影就算拍攝的東西都對準焦距,後製處理也能做到「只留下這個其他都變模糊」。搞不好攝影師將不再是一門專業。
的確說到個別畫面的品質,兩者的差距不大。不過現在的數位拷貝 (Digital Cinema Package) 放映不會有晃動。那是當然的,畫面完全不會晃動,但是笠松兄也說過「底片拷貝放映會有晃動,也就是說因為影像本身微妙地晃動,自然就成了 3D 影片」。就算是半開玩笑吧,他認為我們人眼看底片拷貝的影像會有立體感是拜底片會晃動的特性所賜。數位拷貝不會晃動,所以之後得戴上特殊眼鏡才能看到 3D 效果顯得很愚蠢。真是非常獨特的意見。
總之數位攝影仍處於過渡期,包含保存方法今後會如何發展,目前誰也不知道。因為我個人對於數位攝影的好處只覺得可壓低成本,所以趁著還能用底片拍攝希望能多拍幾部片。
《之後的日子》於同年的東京 FILMeX、鹿特丹影展、聖賽巴提斯影展也都有上映,當時的感受是實在看不出是「電影作品」。理由不是我在意的數位攝影,而是音效。拍攝時沒有考慮到戲院上映時的音量擴散程度與幅度,透過大銀幕看,感覺聲音被畫面埋住了出不來。
以電影來說,需要影片剪接兩天+成音 (MA) 一周。電視若一個小時的戲劇,則要影片剪接一天+MA 一天。電影必須立體地加上許多音效,那種花時間的方式和現場聲音的擴散方法,目前的電視劇不論在時間上和預算上都做不到。
因為電視播放的音域固定,就算錄下低喃或腳步聲,除非事先放大,否則播出時會被切掉。大的聲音也是一樣。明明原本想表現的不是聲音強弱而是遠近,由於電視音效的特性而無法達到。如果今後音響系統優秀的電視能普及一般家庭,或許立體音效的電視劇也有到來的一天。
「觀察」角色使其立體化
固然選擇主題的方式和過去一樣,但作品主體跟我過去的作品相比,感覺娛樂性變得比較高。如果說過去是將重心放在每一個鏡頭的描寫,故事性沒有前進的鏡頭只要感覺有趣就留下;這一次則是讓故事的輪廓變得清晰,主角的個性從一開頭就讓人看清楚,再慢慢地施壓看他如何因應,企圖用正統的戲劇方式堆砌。所有的鏡頭都是為了貢獻劇情的發展,讓故事情節一路往前走。也就是說,我抑制了紀錄片式的手法。
同時還為每個主要角色安排了有關「血」和「時間」之爭的決定性台詞。例如福山演的野野宮良多是「果然還是這樣嗎」、Lily Franky 演的齋木雄大是「時間……,孩子要的是時間」、良多父親的繼室說「就算是夫妻相處久了,也會變得很像」等就是。
良多的角色也為了努力扮演被期待的父親形象而教跟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兒子拿筷子的方法、買露營用具等;另一方面,他很瞧不起對方家庭的父親居然提到錢,卻又忍不住對本人說「憑什麼一個賣電器的可以跟我們說那種話」,顯示出一種遲鈍。我隨時想著要如何描繪出這種擁有雙重性的立體人物。自己最討厭的地方、不願讓人看到的地方,回溯記憶時老是被挖掘出來。同時我也在觀察福山本人的個性,想著「如果是他在這個時候會說些什麼」,讓角色立體化。創作者需要記憶、觀察和想像力等三大利器,以這部電影來說觀察尤其重要。
實際上有拍了但沒用到的鏡頭。那是良多來接離家出走的兒子時,雄大對他說「養育小孩不能當個投手,必須是捕手」的台詞。福山演的父親良多是隨自己喜好投球的投手型人物。Lily 演的雄大則是不管孩子投什麼球過來都接住的捕手型人物。兩種完全不同的個性用一句台詞給點明。因為雄大有點太帥了,只好給刪掉。
意外的是,福山本人做為演員也是捕手型人物。他的溝通能力很好,可以配合對方的演技入戲,彈性十足。因為見面之前還以為他的表演方式十分明快,所以覺得很有幫助,也很驚喜。
因為做為被拍攝者,他怎麼拍都美得像幅畫,所以我特別留意將他最美的側臉安排在讓人印象最深刻的鏡頭裡。
受惠於選角的現場
可能前面我也說過「選角決定了作品八成的好壞」,《我的意外爸爸》就擁有十分均衡的角色配置。
我在演員確定以後,除了童星外會想像演員的聲音調整劇本。中間會有好幾次一起讀劇本的彩排,可以隨時修改說話方式、改變語尾等,等於是為演員量身訂做角色。
即便到了最後定稿,自己心中還是只有六十分。在兩個家庭見面的現場,我讓他們分別進不同的休息室,觀察他們在裡面如何吃便當、如何打發等待的時間,然後反映在劇本上。雄大那句「你知道 Spider-Man 蜘蛛嗎」的台詞,就是 Lily 本人為了緩和童星緊張的情緒對他說的話,被我直接拿來取用。
我真的常常受惠於選角的協助,這一回就有兩次比較大的受惠情形。
一次是受到拍攝對象的牽引,讓角色變得更具魅力。其實初稿中,雄大的角色很惹人嫌、雄大妻子緣是缺乏知性美的人。可是選定由 Lily 和真木陽子來演,正式開拍後,因為演員本身的人格特質和味道,使得角色變得更具深度。
其中最顯著的是,由於良多在購物商城自以為是地提議「我可以兩個(兒子)都接過來養」,雄大怒斥「你想用錢買孩子嗎」。我的意象中是要重重地怒嗆,可是 Lily 卻是軟弱地坐在長椅上怒斥。這時可以看見雄大的猶豫、他過往的人生。演出的過程中,著地點突然改變,對我而言那就是拍戲的樂趣所在,所以是讓我很高興的一場戲。
還有一次是針對劇本,他們提出率直的意見。
其實事先我就有告訴他們「劇本中有覺得不妥的台詞,請盡量說出意見」。那是一場因此而死裡復活的戲。
那場戲是在家中玩露營遊戲的隔天早晨,良多看著養育六年兒子慶太的照片,不由自主地哭了。剛好之前夫妻在陽台的戲拍到好鏡頭,我覺得沒有必要再錦上添花,就從劇本上刪掉那場戲。不料真木和 Lily 提出意見說「那場戲還是要有比較好吧」。我問福山的看法,他說「留與不留都聽導演的。不過有的話,接下來的戲比較好演,不如先拍起來再做判斷吧」,就這樣起死回生了。
還有真木演的緣對良多說的台詞「只在乎像不像,表示你是缺乏為人父親感受的男人」本來也被刪掉了,因為真木說「我想說那句台詞」,所以又放了進去。
過去我一直認為作品是「對話」。是為了某人而做、寫下想要說給對方聽的話。設定好那種交流,我開始寫劇本、進行拍攝。可是《我的意外爸爸》是以「自問自答」的方式做出來的。我是在自己的腳邊挖洞,不知不覺將自己親身經驗的小故事給過度投射在主角身上。
尤其是拍攝中抓不準作品和自己的距離,已分不清那場戲或台詞是否有意思,以致將不確定情況下寫好的劇本帶到現場後又刪掉的情形一直延續到殺青為止。
因此我很感謝演員們都能客觀地在一旁看著,讓我受惠良多。
▍ 是枝裕和《我在拍電影時思考的事》 購書連結 http://bit.ly/2sW4jSr

【釀電影】2018年 6月號(訂閱方案請看這裡)
《一直在等回家的人》——是枝裕和專題
〈是枝裕和:死亡與重生的日本美學〉by 馬欣
〈是枝裕和:日常生活的魔術師〉by 吳曉樂
〈《比海還深》:在一切仍願意相信的時候,拚命相信〉by 施彥如
《釀影評》專欄
〈《犬之島》:我聽得見你。〉by 香功堂主
〈《瞞天過海:八面玲瓏》——女孩說:「看起來好好玩,我也想玩⋯⋯」〉by L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