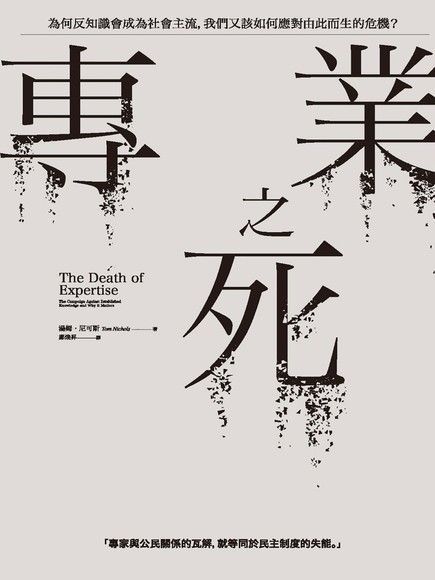「無知在美國是一門邪教,而且源遠流長。反智像一道綿延不絕的線,蜿蜒貫穿著我們生活中的政治與文化面,至於滋養著這條線的謬誤觀念,則是:民主就等於「我再無知,也可以跟博學的你平起平坐」──艾西莫夫(Isaac Asimov)
§ 本書要告訴你什麼
在後方的章節裡,我會介紹這個問題的幾種病灶,其中有些扎根於人性,有些是美國人特有的毛病,更有些是現代人、特別是有錢人免不了的文明病。
在第一章裡,我會討論「專家」的定義,還有就是專家與素人間的衝突是否真的是種新奇的玩意兒。到底怎樣才叫作專家?遇到自身背景或經驗值以外的困難決定,你會去找誰給建議呢?(萬一你覺得自己從來不需要任何人的意見,那恭喜你,就是你這種人讓我覺得這本書非寫不可)。在第二章,我會探討的是在美國,專家與公民間的對話,乃至於任何兩者之間的對話,何以會變得如此貧乏?大家不要自己騙自己,任何人只要一說起自己看重的事情,特別是講到自身深信不疑的信念與價值,我們都會輕則討人厭,重責讓人生氣到完全不想賞臉。社會上不少專家與客戶間的合作關係會出現阻礙與問題,經常都是因為基本的人性弱點在作祟,而在第二章裡,我們會首先來思考一下有哪些「天險」會妨礙雙向的溝通與理解。這樣思考過之後,我們便能仔細地去觀察二十一世紀許多特別的問題。
比方說,我們都吃過一種問題的苦頭,那就是「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這種偏誤指的是人只會接受與自己成見相同,也就是能「確認」自己成見的資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生活經驗、成見、恐懼,甚至於是精神病,而這些包袱都會阻礙我們接納專家的建議。有人認為特定的號碼很吉利,任憑你是諾貝爾獎等級的數學家也沒辦法改變他的迷信;有人覺得搭飛機很危險,太空人或戰鬥機飛行員再怎麼拍胸脯保證也沒辦法安撫他的恐懼。而我們當中還有些人,雖然這麼說不太客氣,但就是資質不夠好,所以連自己錯了也不知道。這跟你是好人壞人沒關係,五音不全或畫畫是小學程度的人可多了。而就跟是有人是音痴,有人畫畫超醜一樣,很多人的能力斷點在於他們感覺不到自己的學識落於人後,他們沒意會到自己的邏輯有多說不通。
教育原本的功能就是要讓我們體認到「確認偏誤」的存在,讓我們知道自身的學識有不足之處,進而能成為一個更有品質,更理性的公民。很不幸地我們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大學生跟家長都把大學當成一種差異性不大,讀哪間都一樣的商品。所以在第三章,我會討論何以高教普及會很弔詭地讓很多人以為自己變聰明了,但其實從學店裡買到的只是難稱有用的學位,外加由虛名撐起的一個幻象,那就是很多人大學畢業就覺得自己是知識分子了。學生的立場不再是求學者,而成了被教育產業追捧的消費者。由此他們學到的頂多是皮毛,但自信卻高漲得不得了。更糟糕的是他們沒有培養出批判性思考能力。少了思考能力,他們自然也就無法繼續學習,也無法評估各種複雜的議題來擔任一位合格的選民。
在科技與通訊管道日新月異的現代,人類知識的進步與傳播可以說突飛猛進,但這也有個壞處是讓人類的劣根性被放大展現出來。專業之死,固然不能全部怪到網路的頭上,但網路是罪魁禍首也是不爭的事實,至少在二十一世紀是如此。在第四章,我會檢視網路這個自古騰堡發明西方活字印刷以來,人類最大的知識來源。我會討論這個網路如何從一個捍衛知識體系的平台,變成了一個讓知識體系遭到炮轟的殺戮戰場。網路絕對是人類知識的寶庫,但偽知識的擴散與流竄也是網路所造成。網路不僅讓人變笨,還讓我們變壞:獨自一人在鍵盤前面,人就會戰,就會酸,沒有人要理性討論,也沒有誰願意聽誰說話。
在自由開放的社會裡,記者理應是無知與學習衝撞時的公正裁判,但現下的媒體已經不再是屬於新聞界,而是變成了「藝能界」。畢竟有需求就有供給,大家要娛樂,主播與記者就給你娛樂。沒有人想針對嚴肅的議題認真討論,那大家就來胡扯,就來鬼混。但這樣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呢?關於這個令人冷汗直流的疑問,我們會在第五章加以討論。
曾經我們對媒體的期望是給我們以真相,以新知,讓我們得以辨別真偽。我們曾期望媒體能深入淺出地讓我們掌握重要議題,畢竟大家平常為了生活,並沒有那麼多時間與精力去追蹤天下事。但如今進入到資訊時代,專業的記者也面臨了全新的挑戰。比起五十年前,記者不僅有二十四小時的播放時間要填,有永遠塞不滿的報章版面要塞,同時消費者還期望你要馬不停蹄地一直更新,一直更新。
在這個腥風血雨、高度競爭的媒體環境裡,編輯與製作人已經沒有耐心或本錢讓記者去培養專業,或是長期累積對一個議題的深入了解。同時我們也看不到有證據顯示多數閱聽人想知道那麼多細節。專家因此常被斷章取義,只被擷取一些精采或聳動的發言,甚至於除非必要,媒體根本懶得去訪問專家。任何人只要跟新聞界有一丁點淵源,都會知道報導一定要拍觀眾的馬屁,一定要夠甜膩或夠有娛樂性,否則陰晴不定的閱聽人隨時可以滑鼠點一點,遙控器按一下,多的是不需要大腦思考的內容在網頁或別的頻道上等他們大駕光臨。
專家不是不會錯,甚至於他們有時候還會非常錯,事實上他們時不時會錯得離譜,然後把事情弄得難以收拾。想捍衛專業在二十一世紀美國的地位,我們就得有迎來這一狗票爛攤子的心理準備:沙利竇邁(thalidomide)從害喜藥變成害人生出畸形兒的毒藥、讓無敵美軍深陷泥淖的越戰、在眾目睽睽下爆炸的太空梭挑戰者號,乃至於有專家警告過說吃蛋會完蛋(等下書放下你完全可以去吃茶葉蛋啦,雞蛋已經從誤傳的不健康食物清單上除名了)。專家會說我們不能因噎廢食,就像我們不能只記得一次空難,而忘記了難以計數且平安起降的飛行時數。專家會這麼說,我完全可以理解,而且他們說的基本上也沒有錯,問題是再多次的平安起降,也不能抹滅空難會發生的事實,而且很多空難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專家出了差錯。
所以在第六章,我要探討的便是專家為什麼會出錯,專家是怎麼出的錯。專家有很多種錯可以出。有些專家是存心惡意詐騙,有些專家是沒有惡意的過度自信,更有些專家是吃燒餅掉芝麻而已,畢竟專家也是人,而是人就會出包。但我們之所以必須了解專家犯錯的過程與原因,其理由有兩個方面。首先是了解專家為何犯錯跟如何犯錯,身為公民的我們才知道該如何消化並運用專家的建議;再者,知道專家犯錯的前因後果,大眾才好評估專家提出的自律措施,並合理地放心讓專家去做事。少了這一層了解,專家的失誤就只會引發隔空放話輿論的混戰,到時候專家會動輒得咎而感到受辱,而一般民眾卻只能擔心害怕如入五里霧中。
最後在結論的部分,我會揭露專業之死對我來說最大的威脅:專業地位的崩潰會危及美國民主的根基。美國是一個民主共和國,共和國裡我們會選出代表來替眾人做決定。問題是,民意代表不可能什麼都懂,所以他們必須仰賴專業人士來擔任他們的幕僚。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專家跟決策者常常不是同一批人。把這兩種人混為一談,那就是在耗損專家、公民與政治領袖間的三方互信,而很不幸地美國人就老是在做這種事情。
專家的職責就是提供專業意見,而民意代表或官員的工作就是決斷。想判斷專家給的意見優不優,想判斷民代或官員的決策好不好,民眾必須對特定議題有相當的了解。這當然不代表美國人人都得去當政策專家,但要是大家對切身議題連基本的了解都沒有,那就等於是自斷手腳,在自身權益的維護上自毀長城。選民要是對重要政策完全沒有追蹤掌握的能力,那就會讓自己暴露在兩種風險之下。要嘛民主制度會被無知的民粹政客綁架,要嘛溫水煮青蛙,民主會慢慢地、悄悄地變質成威權政體,控制在技術官僚的手裡。
在民主社會裡,專家也有很重要的責任得負,但這幾十年來他們都一直逃避著這項責任。曾經,公共知識分子會(經常與記者一道)努力讓重要的議題為大眾所了解,而如今,受過高等教育的菁英只會在小圈圈裡相濡以沫。這當然也多少得怪公民的態度不夠好,畢竟發問與質問還是有差別的,但公民的態度不好,不代表專家可以丟盔卸甲,把自己的職責丟在一旁,他們依舊有責任服務社會,把同為社會一員的公民們視為要服務的對象,而不是一群幼稚鬼。
換句話說,專家有責任提供教育,選民有責任學習。話說到底,不論專業人士能給多少建議,真正能決定國家大政走向的仍是廣大的群眾。只有選民可以在從各種會對他們家庭與國家產生影響的選項中挑出一個,也只有他們可以為這些選擇的最終後果負起責任。
但專家的義務就是要善加輔助大眾做成決定,而這也就是我寫這本書的原因。
▍美國亞馬遜書店2017年度非虛構類好書、長踞知識論/哲學類暢銷榜 ▍
為什麼網際網路開放、高等教育普及、新聞媒體蓬勃發展,
卻讓當代社會鄙視專業、陷入前所未有的反智思潮?
本書將帶我們反思「專業」的意義,
爬梳專家與公民的關係在當代何以崩解,並找回民主社會中兩者應有的相處之道。
城邦花園│https://goo.gl/iTjgyJ
博客來│https://goo.gl/fcPcgD #選書
讀冊│https://goo.gl/Gb6eb7
金石堂│https://goo.gl/TcrsSJ
誠品│https://goo.gl/AXLy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