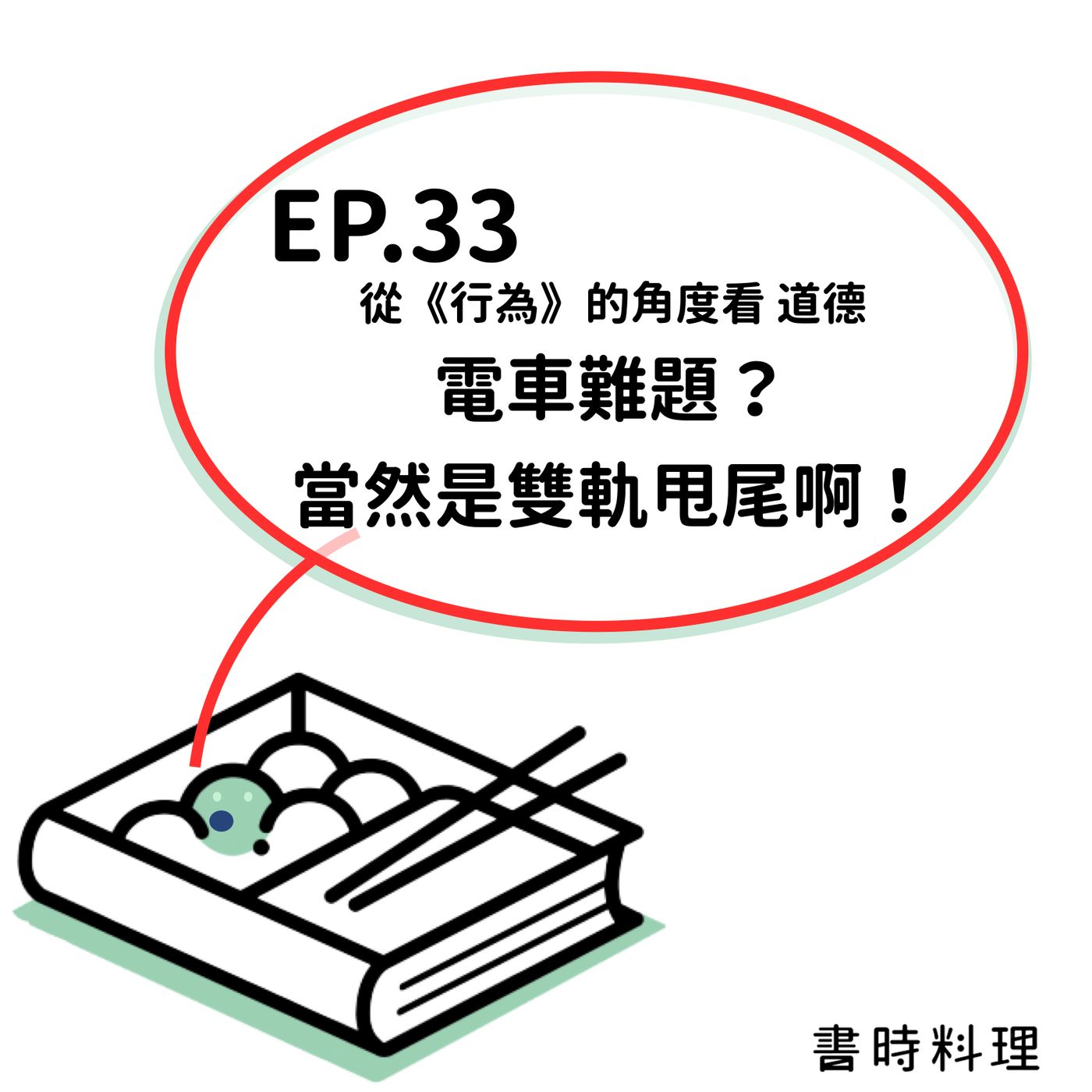談過了效益主義與康德,當然就要來看德行論。就整體角度,德行論是對抗傳統的「行為倫理學」,也就是為了對抗效益主義與康德式倫理學所產生的新理論流派。你不懂「行為倫理學」,就無法真正弄懂德行論,然而就算懂「行為倫理學」,你可能也弄不懂德行論。
為了集中焦點,以下我就只探討麥金泰的德行論。在台灣的應用倫理競賽中,最常被引用的德行論,就是麥金泰的理論,這是因為麥金泰的中文資料最多,理論體系也比其他德行論者完整,幾乎可以用在所有應用倫理學議題之上。
雖然我也是麥金泰派,不過我要強調,麥金泰的理論也有缺點,我在其他系列文章中也曾多次強調過這一點。他的理論可能產生嚴重的問題,但在解釋許多社會現象時,特別是指出大多數人的道德價值想法時,他的理論仍非常好用。有時還像吃了無敵星星一樣的強大。基本面
麥金泰式德行論有明確的系統結構。他認為在人類的合作活動中,行為者只要具備德行以追求該活動的卓越標準,就能獲得潛藏在該活動中的內在善(內在價值),這種內在善就是「不可量化」的幸福感;而只要在多種人類活動中獲得這種幸福感,那整體人生就會是幸福的。
這個理論有個特點,就是帶有道德缺陷的普通人,也能獲得不錯的價值成果。像是賣麵的,也許算不上廚師,但只要他好好賣麵,努力追求賣麵的卓越標準,像是衛生、效率等等,並且具備賣麵所需的德行,如精確、忍耐、誠實,就算他沒有賺大錢,沒有成為賣麵界的一哥一姊,他還是能在這種活動中獲得成就感、榮耀感等內在善。只要不斷累績這種正面的價值感受,最後整體人生就會是幸福的。
如果沒辦法在賣麵的活動中感受到內在善,那可能是因為他不具備相關的德行,又或是沒在追求該活動的卓越標準;而只要他具備德行追求卓越標準,就「一定」能獲得內在善。所以重點就在於「德行」和「卓越標準」分別是什麼。
一個活動的卓越標準,通常是由該活動的「卓越行動者」所奠定的,他們不見得是全方位的強者,但在該活動的某個向度有不錯的技術表現,或是曾獲得高度的內在價值,因此廣被推崇。而做為這個活動的新進參與者,可以學習這些前輩所留下來的標準來提升自我。
當然,絕大多數的活動參與者都不可能「達到」卓越標準,因此麥金泰認為,只要不斷「追求」這個標準,就能產出內在善。像是你不可能像專業的搞笑藝人那麼會講笑話,但你只要努力試著學習他們的技巧,持續精進自己,你就能獲得講笑話專屬的內在善。
而「德行」的定義就比較麻煩了。麥金泰認為從古到今的德行定義並不一致,包括的範圍也不太相同,各社群的核心德行也可能不一樣。基本上,他似乎認為「德行」就是能幫助你在追求卓越標準時獲得內在價值的「那種好習慣」或「那種好特質」,但他也認為德行就是內在價值與卓越標準。
這會讓他的理論變得模糊不清:行為者應該具備德行來追求德行(卓越標準)以獲得德行(內在價值)。
因此我在這邊建議一種較簡單的理解方法,你就把「德行」看成那些能協助你追求目標的良善人格特質,相對的「惡行」就是會阻礙你達成目標的那些負面習慣或特性。請記得,在這定義之下,德行並不一定是道德德行,也可能是沒有太多道德意味的良善特質,像是「創新」。
優缺點
接著就來看到麥金泰德行論的優缺點。我還是只談應用時的優缺點。
麥金泰理論的第一個優點,就是系統非常簡單,就德行、卓越標準、內在善這三大要素而已,你只要在所應用的個案與議題中快速找出其中涉及的德行、卓越標準與內在善,就能很快找出當前的問題之所在(最常見的錯,就是誤判這三者),並提出解決方案。
也因為這系統非常簡單,不只分析者可以很快上手,聆聽者(包括對手與客觀第三方)也都能很快進入狀況,在訴求廣泛認同時會很有幫助。
第二個優點,是這理論的詮釋空間很大,容易舉例說明,從生活瑣事到國家大政都能套用。你睡覺會有睡覺專屬的德行、卓越標準與內在善,開車會有開車專屬的德行、卓越標準與內在善,最專業的技藝職人會有他們的德行、卓越標準與內在善,技術最爛的牌友也有其對應的德行、卓越標準與內在善。
只要是人類社會合作活動,這理論就能套用。最專業的倫理學學者們甚至還在爭論黑猩猩或海豚能否套用(如果能套用,那牠們也會有牠們的幸福,人類在規劃空間時就應該考量其需求),有些科幻電影也會利用這個理論體系來設計賽博龐克的世界觀。
第三個優點,是其焦點不在於單一行動的道德對錯,而是人格健全所帶來幸福,因此較不具有攻擊性。德行論者又被稱為「行為者倫理學」,比較看重整體與長期的人格養成,認為單次行為就算有對錯,往往也不是決定性的,人可以改過並追求卓越來提升自我。
因此「行為倫理學」常在單一行動的對錯陷入激烈爭辯,而德行論會繞過當下爭端,由長期視野來提供建議,通常可以讓討論跳出鬼打牆。
第四個優點,是內在善可分享、共融,通常會比訴求「個人成聖」的理論要更有吸引力。內在善是可以分享的,像是國家代表隊獲勝時的榮耀感與成就感,而這種經驗基本上大多數人都有過,所以訴求內在善,會讓人有「啥都沒幹也能賺到」的額外獎勵感,也就比較容易推廣。
再來要看到的是麥金泰理論的缺點。第一個要談的就是他最嚴重的問題「邪惡實踐」。我們可能具備德行追求卓越標準,並且在活動中獲得內在善,因而覺得人生是幸福的;但我們所參與的活動,就他人來看可能大有問題,像是納粹大屠殺。這種「自爽卻害人」的活動,就被稱為「邪惡實踐」。
麥金泰的理論沒辦法確認哪些實踐是邪惡實踐,他能說明納粹殺人為何會覺得幸福,卻沒辦法有效區別並預防這一切。後來的麥金泰派學者認為「邪惡實踐」會造成社群的崩解,因此無法長期存在,但他們沒有辦法主動促進這個除弊過程,只能等著「邪惡實踐」自己垮掉。
麥金泰式德行論者的第二個缺點是從第一個延伸而來。他們相信這個世界就是不斷走向卓越,當下的社會理論上也就會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卓越的狀態;但因為有邪惡實踐存在,因此麥金泰式德行論者也很難確認現下的狀況是否為「最卓越的狀態」或「邁向長期卓越過程中的暫時小低谷」。
這很容易被批評者攻擊為「偽倫理學」,因為麥金泰式德行論者判定為正確的行為模式,很可能在將來被另一批麥金泰式德行論者判定為「邪惡實踐」,理由單純就是「被其他更卓越的實踐淘汰了」。那麥金泰式德行論者就永遠只能當個詮釋者,而不會是提出解決方案的指導者。
麥金泰式德行論的第三個弱點,就是不易解決高難度個案。在多數的狀況下,麥金泰理論都非常好用,但碰到高衝突性的個案或思想實驗,麥金泰派雖然能批判其他理論,卻無法提出更好的建議,往往只是說:「當事人如果具備德行,就會知道在那個狀況下該怎麼做。」
像電車問題,麥金泰派會批評康德派與效益主義的推理方法都有問題,但當別人反問應該怎麼做才好時,麥金泰派會說:「怎麼做都是對的,因為責任並不在他身上。」「如果是真實狀況,因為還會有各種其他條件,具備良好人格的當事人一瞬間就會知道怎麼做。」
但仔細看看就會發現,這種建議等於是沒有任何建議,頂多就是讓「現下」的「聆聽者」解除道德思辨的壓力,但對處於道德爭議之中,急需解決方案的「當事人」沒有太大幫助。或說其幫助和「鼓掌加油」差不多。
訣竅
接著就來看運用麥金泰式德行論處理「醫療倫理學」議題時的訣竅,我一樣也是列出兩點。
第一個訣竅,是在推論時,要記得把幸福的定義權留給對方。因為麥金泰式德行論的王牌就是「內在善」這種可以共享的幸福感,而可以共享的前提,就是人家想要這種幸福感。
所以如果是企圖說服病患與家屬,那你所訴求的內在善就是要病患與家屬能共享的,理論上就不會是「醫療從業人員的成就感」,而是「重生的光輝」或「尊嚴的死亡」之類的。
如果是醫院職工內部的情境,那就不能訴求「共體時艱」或「傳統聲譽」,因為那不見得是隨時可能離職的約聘人員會在意的價值。你要訴求的可能是團隊「分工合作的向心力」或「領導者比其他人犧牲更多的壯烈感」。
若是像公衛議題,要訴求廣泛社會大眾的支持或認同呢?那就應該要訴求「健康身心」這種詮釋空間很大的價值概念,強調健康身心是實踐其他人生目標的前提。
而運用麥金泰式德行論的第二訣竅,就是緊扣「好人做好事」,以良好人格來解決問題,而不是用規範理論硬去破解困境。
大多數倫理難題或道德兩難都會把當事人的情境「均質化」,討論者不知道當事人的出身背景和個人條件,所以只能假設當事人是「社會平均人」,這就會讓問題限縮到只能透過道德規範才能解決。如果道德規範之間有矛盾,那就麻煩了。
麥金泰式德行論不太講道德規範,而是強調在社會生活中展現德行以培養人格,只要有良善的人格,大多數的難題都可以透過個人實踐智慧來解決;整個環境與制度也應該以培養人格為前提,而不是單純為了解決眼前的道德問題來設計。像是碰到醫院內部的勞資爭議,重點就不只在於解決眼前的衝突,而是指向「為何管理階層未意識到基層處境?」或「為何基層看不見醫院經營的挑戰與困局?」
要注意「培養人格」並非「進行倫理教育」,許多採德行論為解決方案的個案分析都搞錯了這點。培養人格是建立一個能鼓勵關懷他人的情境(所以德行倫理學又稱關懷倫理學),而倫理教育在台灣往往淪為上課算學分,對於改善人格幫助相當有限。
實作
最後來看議題分析。我設定的議題是和之前一樣的假個案:「某公立醫院的婦產科病床使用率經常未達20%,而醫院附設的產後護理之家,即月子中心的床位,則是自開幕以來就一直不足,考量空間利用效率、民眾需求以及醫院獲利,因此申請將一半的婦產科病床的空間轉為產後護理之家運用。」
麥金泰式德行論可能提出這樣的論述C:「建議將此提案提交上級主管單位,由其邀集其他公立醫院與學者專家進行討論,尋求共識。公立醫院雖有賺錢的考量,但因為公共財,應做出一定的犧牲,為社會帶來更多可共享的不可量化價值。院內空間分配的理想規劃也就應由更多相關人等共同會商,以免局限於個人或小群體的偏見或利益考量。透過這樣的討論過程,也可以讓與會者瞭解到多元想法,進而體察其社會責任與真正的有意義的目標。」
論述C能掌握到麥金泰式德行論的優點,像是提及德行(「犧牲」),追求卓越標準(避免小群體偏見),與內在善(不可量化價值);此外也由個人或小群體跨出到整體共識,訴求共享的幸福。
論述C也能避免麥金泰式德行論的部分缺點:不講出具體解決方案,就能避免誤踩邪惡實踐的地雷。但問題也在於精明的批判者會質疑協商過程如果遲遲提不出結論,又該怎麼辦。
麥金泰派可能會抗辯說,這種論辯過程也是種追求卓越的過程,就算沒達到特定目的,一樣可以產出專屬於論辯的內在善:床位問題沒解決,但大家在討論過程中學到很多溝通技巧,甚至因為進行了暢快的溝通而感到滿足。而批評者是否會對這種說法感到滿意,就難說了。
而在兩個訣竅的部分,論述C運用了第一種,把幸福定義權留給外人,並隱喻了第二種,就是這個討論過程會有助於人格的提升。
看完以上的說明,你可能會認為德行論有點虛,講難聽點,就是在踢皮球。但你應該也會發現,這不就是台灣人做事的方法嗎?
沒錯,這是因為台灣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在思考許多事物時,會採取類似德行論的角度。雖然台灣人的這一套不是現代西方德行論,也更不會是道德系統明確的麥金泰式德行論,不過因為有這樣的前置條件,台灣人對於麥金泰理論的接受度也就比較高,特別是那種在表面上「不想斤斤計較錢,打算呈現大聖人形象」的社會人士。
德行論是有市場的,然而,這不代表它能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