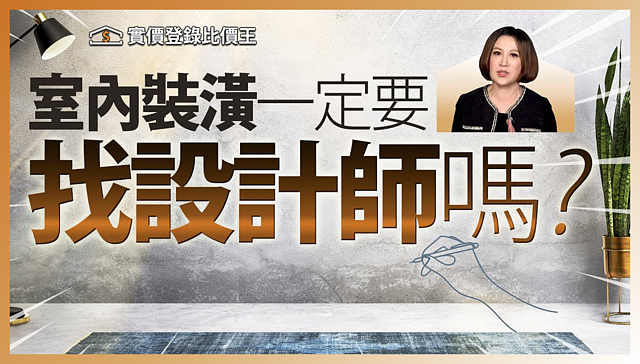慟|聽說.困獸
閱讀時間約 2 分鐘
腦海中開始看見自己割腕;左手手腕不自覺的感到疼痛,血液順著手腕滴落的畫面如在眼前。我開始強烈不安,焦躁地不知該如何是好,害怕而恐懼使一切顯得慌亂。於是我開始撥打電話求助,一通又一通的轉入語音,最後我忍不住真的拿起美工刀朝手腕刻劃。不管怎麼努力,美工刀好像就是無法割得夠深;鮮血裂開流出,儘管血量比在手臂上自殘還要更多,但與腦海中的畫面仍有極大差距。我依然焦躁,焦躁的不懂為什麼無法流出更多的鮮血,不安的在房裡來回踱步,手上則是繼續撥打電話求助。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但其實我並沒有想要自殘,就只是單純想看到很多很多的鮮血。我順著手腕的血管割著,但要割裂血管遠比我腦海中的畫面來的困難。很想大叫,很想大哭,但是我只有不安的焦躁,慌張的不知該如何是好。鮮血流出如此有限讓我不知所措,我並不想傷害自己,我只想看到腦海中的畫面,因此只割了三刀就放棄自殘,因為我發現我無法讓鮮血如想像中奔流。電話總算撥通,我對著教會的姊姊語無倫次,而她也不知道該如何幫助我,對談呈現一陣慌亂。
如同旋風襲擊,一切的情緒來的既強且急,但消失的速度也比我能理解的範圍還要快。彷彿突然恢復理智,拿起面紙擦拭鮮血與乾涸的血塊,愣愣而無法理解自己究竟在做些什麼。確定止血後拿了鑰匙隨即騎車出門買藥水消毒擦拭,情緒麻木但仍感到刺痛侵襲,困惑不懂適才發生的全部,只知道盡快把美工刀收好不再多想。
「沒事,什麼事也沒有,一切真的都很好。」我反覆在心裡安慰自己,但看著左手腕上的傷痕卻永遠也無法說服自己。而我選擇遮掩,穿著過大的長袖上衣試圖掩蓋傷痕;我看不到,爸媽看不到,沒有任何人看得到。遮掩讓一切似乎真的都沒發生,逃避不想面對自己,但卻在敲打電腦鍵盤的同時不斷感覺到傷口傳來的陣陣刺痛,不斷提醒著我永遠無法欺騙自己。
洗手時,傷口在流水下用疼痛抗議,而我試圖洗淨罪惡,用水與香皂讓抗議的喧鬧更加強烈。我不知道是思緒麻木了疼痛,還是疼痛麻木了我的思緒;但不管如何洗刷,卻怎麼也無法潔淨我扭曲黑暗的靈魂,還給我嬰孩純潔的生命。我輕撫已經微微紅腫的傷痕,靜靜感覺這仍是我的身體、我的靈魂、我的生命。輕撫著,感覺著,靜默著,用唇輕輕親吻著。
「我愛妳,仍然愛妳,但我仍會傷害妳。」閉上雙眼,我輕吻著傷痕,在心裡對自己說著。
而我永遠也不懂到底什麼是愛。
64會員
320內容數
生活如同雲霄飛車,但也讓我共享喜樂與淚水。期待藉由這系列的文章,讓我們能更友善地看待精神疾病的親友。我無法代表精神疾病,也無法代表躁鬱症;但我相信每個人同心攜手,社會標籤與刻板印象將被溫柔的挪去;讓杜鵑鳥能自由翱翔、飛越杜鵑窩。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