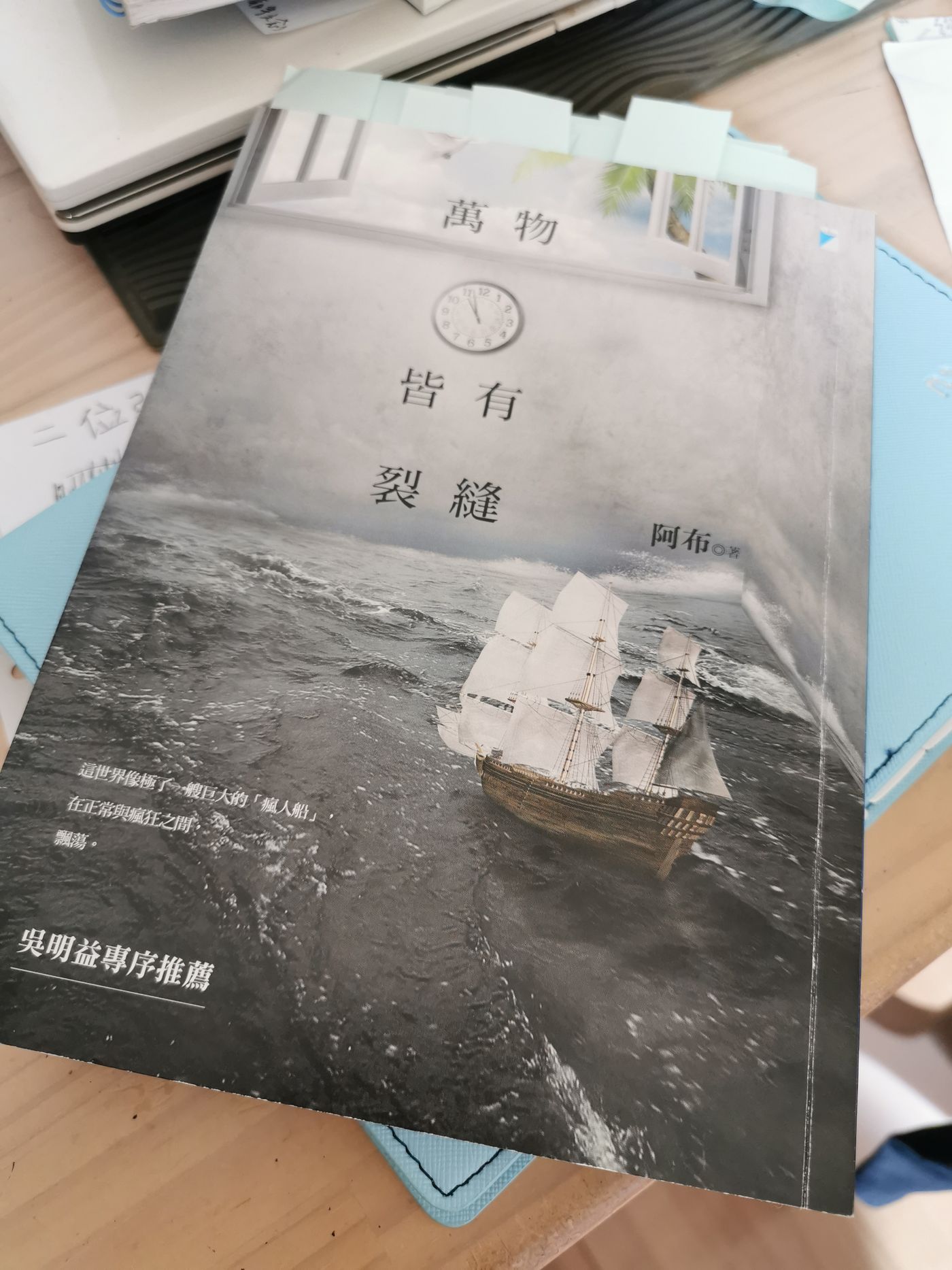最近姐姐放學回來,總是會在便當裡剩一些飯菜,說吃不完。我確認一下份量,如果剩的比較多,還是會要求她盡量吃完。姐姐邊用鐵湯匙,刮便當的不銹鋼內層,想要把飯粒耙乾淨。我聽著金屬相互碰觸刮耙,那尖銳刺耳的聲音,總讓我渾身起雞皮疙瘩,央求姐姐手裡落下的湯匙輕一點。
我念國小的時候,學校有提供營養午餐,剛開始吃很新鮮,吃久了對於挑嘴的我,總有這不喜歡那不愛的菜色,不敢違背老師下達要吃完的聖旨,不是吃得很痛苦,便是私下偷偷的要求打菜的同學,這少一點那多一點,希望這短暫的午餐時光,能安然的完成「吃完」這項任務,食物到底好不好吃,對當時的我並不重要。
到了國中,學校沒有了營養午餐,只有代訂便當的服務,看似選擇很多,但每個台幣50元以下的便當,換來通常都是咖哩飯,黑胡椒牛肉飯等等,看過去就是一大陀黃黃的,或是黑黑的醬汁,覆蓋在飯菜上,光用看的食欲就減了大半,更遑論美不美味,常常我只吃了三分之一,便趁老師不注意,通通餵給了餿水桶。我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央求母親為我準備便當。說是準備便當,其實就是前一晚的飯菜,但母親的好手藝人人皆知,總是會費盡心思,想一些適合帶便當的菜色。每到中午,忍受著蒸飯箱加熱時,各種食物夾雜的難聞氣味,尋尋覓覓自己的便當盒。說也奇怪,大家的便當一起蒸,機器加熱混雜的氣味令人作嘔,但翻開自己的便當盒,撲鼻而來的飯菜香,卻令我食指大動,一口接著一口,享受著只有自己有的美味便當。
嫌代訂便當難吃的絕對不只我一個,所以帶便當的同學也不少,每到中午時刻,我總是開心的享用媽媽牌便當,又得忍受著四面八方鐵湯匙刮便當盒的刺耳聲音,那聲音就像能深入我的體內,在我身體裡流竄,刮耙我的血管和內臟。我總是不停的撫摸自己的臉頰和雙臂,希望能減緩一點自己的不適。
每天的中午時分,我總得輕輕下手,品嚐母親準備的便當,小心翼翼的讓湯匙與便當的接觸面降到最低,一方面還要忍著迎面而來,排山倒海的耙飯刮除聲將我包圍,我壓抑著自己滿身的雞皮疙瘩,快樂卻又痛苦著。
帶便當的日子,從國中延續到高中。母親的便當依然美味,榮登班上最想打游擊的便當之一,聽著四面八方的同學的扒飯聲音襲擊,我忍著顫抖,驕傲的展示自己的便當,邊央求同學吃飯不要這麼大聲。
「蛤?!妳會怕這個聲音喔!為什麼啊?」然後繼續肆無忌憚的大力扒飯。到最後,我已漸漸麻痺,學著習慣處在尖銳刺耳的聲音之中,而不被吞噬淹沒。
帶便當的日子,早已離我遠去許多年。直到自己的女兒上小學,要帶便當去學校用餐,我才又想起自己曾經這麼厭惡這個聲音,卻又如此懷念那些日子,那些與同學分享炫耀的,一個個餐盒,那些每個夜晚,母親揮汗烹煮的佳餚,以及永遠忘不了的,屬於母親的飯菜香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