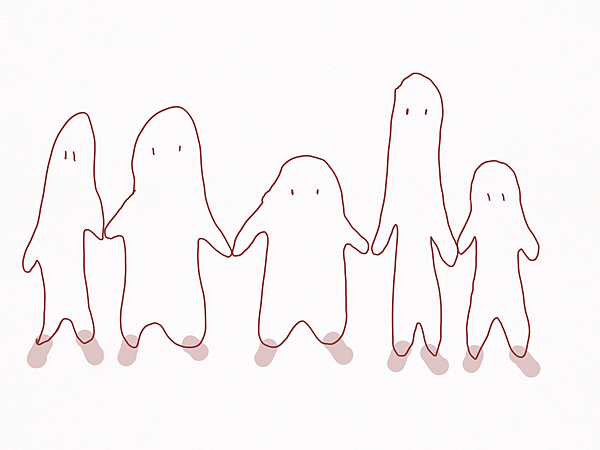「在他生病之前,其實還沒真正生病的時候,就有一段相處上的困難,格格不入、很奇怪、講不通,那個時間依我的case,長達十幾年,找不到任何的原因,怎麼調整,都是我們在調整,他很自我。等到發現他病發的時候,我反而鬆了一口氣!有一個答案,他就是這樣子的人,所以他今天才會生病。原來他其實已經在生病了!我對其他孩子講,他之前就已經生病了!!但是說疾病的名稱太化約了,這化約也同時的壓迫到康復者身上。那個汙名的東西如果沒有自己拿掉,根本沒有辦法。」
照顧者對於生病的人,往往有很多複雜、錯綜難解的心情。身為最親近的人,他們也同樣面對著周圍環境中別人對於疾病的污名和指責。醫療現場要接住的不只是病人,還有他們的照顧者。相較起絕症,家人得到精神病的宣告可能更複雜、而且必須面對更長的照顧時間。不能瞭解照顧者的心情及複雜,只簡單的用「疾病」和「藥物」來標籤。在這樣的脈落下,診斷確認很容易粗暴,但是無助於家屬曾經/正在面對的創傷。照顧者的自白裡,除了在醫療端的挫折,更挫敗的是社會資源雖在協助精神障礙者,資源的配置不當、與實際狀況無法接軌,讓這些資源入不了家門。照顧者及其家庭往往成為精障者的當然唯一最後的資源,照顧者在多重的擠壓變形下在生活。因此我們協力了幾群跨組織、跨群體的照顧者,成立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希望不只是電話,未來更進入家的現場,讓支持進入家門,讓家庭照顧者得著力量,直接在家的現場進行培力工作,把家庭照顧者不僅是被以服務對象看待,而是視為行動中的夥伴。不只是引入資源,更是在創造家庭內外的社會網絡-家庭與家庭間相互支持、家庭中發展出的社會關係。
畢竟,就像一位照顧者整理自己一路的歷程,她是這樣回應的:「怎麼去說,怎麼去表達愛,怎麼去表達感受,那種韌性與執著,那種所以我們現在正走在什麼樣的路,以及感覺,我覺得有時候就是讓別人看到這樣的照顧者,一路想做什麼,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就可以傳達給社會大眾,或者傳達給其他家屬知道有怎麼樣的可能性!培力家屬,我要面對的還有什麼?除了疾病外?實際現場的經驗那個東西能不能夠被寫下來,被說出來,然後被教導出來,被傳授出來,這樣那我覺得它會形成一個照顧者的語言。我覺得照顧者語言的重要性其實是,還給我們的經驗,用我們的方式詮釋,讓我們自己有工作默契,讓有的醫療的語言,它可以重新再修整,那這是很長遠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