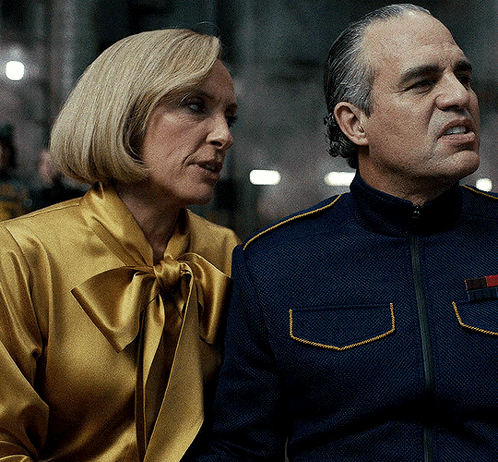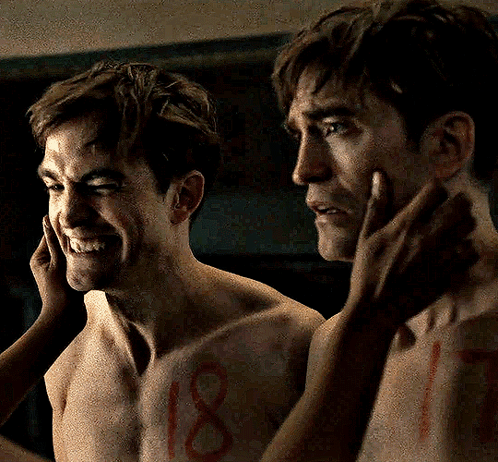大家好,我是主力寫書評偶爾協槓聊聊電影和戲劇的哈斯。
連假期間跟老公看完《米奇17號》,比我預期還要精采,所以文思泉湧的來來分享我喜歡和認為值得分析的幾個點🎬
1.多元種族下的「地母系」女主角
近來大陸網路開始出現一種新標籤:「地母系」。它是對抗主流幼態審美的一種文化反撲,象徵母性、包容與穩定的力量。
娜夏(Nasha)正是一個典型的「地母系」代表。她是警備人員中的佼佼者,不僅在艦隊中擁有影響力,還能調度足夠資源同時供養兩個米奇。在馬歇爾激怒她之後,她毅然發動革命並成為新領袖。儘管她偶爾展現出情緒化的一面,拒絕凱(Kai)共享伴侶的條件致使談判崩裂,但她同時能包容不同版本的米奇,並讓米奇 17 號與 18 號達成和解——「娜夏的話有種神奇的魔力,讓人想相信她」(By 米奇)。
更重要的是,明知米奇會不斷復活,娜夏卻在沒有被打印資格的情況下,甘願冒險穿上防護服陪伴他走完死亡。伴侶不斷離去是極大的折磨,她卻從未抱怨。
這樣的她除了代表真愛,她的形象也與馬歇爾形成鮮明對比。導演巧妙地透過兩人交錯的命運與表現,呼應「誰才配成為王」這一核心命題。即便娜夏最後接掌權力,大家依然直呼她的名字,而非以冷漠的姓氏相稱——這正說明了她的人格魅力來自於平等與信任。
這也賦予女主一個新的面貌,他們不需要總是善良恭儉,退讓等待奇蹟,可以有人格缺陷並勇敢爭取。

2.馬歇爾(Marshall)的政治邪教
馬歇爾初看之下可能讓人覺得是個草率成事、毫無威嚴的指揮官:健忘、口誤、不斷誤稱支持者為「教會」信徒,看起來更像是個被推上檯面的棋子而非執棋者。
但仔細想想,他其實是高階級中的「失敗者」。正是因為選戰落敗,他才走上殖民之路,企圖在異地重建權力幻象。影片中不乏暗示:除了親衛隊首領雷斯頓(Preston),艦上的大多數人其實並不認同馬歇爾的主張,只是虛應故事、表面附和,直到利益衝突出現時才會搬出他的「金句」當擋箭牌。
這點說明了什麼?大多數人其實是清醒的,但為了離開地球這個爛攤子,他們選擇妥協、選擇服從。哪怕這套制度不合理、設計不良、政策讓人遍體鱗傷,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米奇也一樣,只想混口飯吃。
也正因如此,飛船才會處處透露出設計不良的痕跡、奇怪的管路轉折、不足的防護系統。更諷刺的是,在這個「失敗者聯盟」中,只要你有能力,無論人種或品格,都有可能被錄取——才導致「多元族群」。
3.忒休斯之船(Ship of Theseus)
米奇17號與18號性格截然不同,原因是打印事故造成的差異嗎?
我認為不完全如此。18 號在觀看 17 號的記憶後,發現即便過著懦弱又低調的生活,依然無法得到善待,因此選擇以更冷靜成熟、甚至心狠手辣的姿態登場。他延續了 17 號的記憶,卻選擇走上截然不同的路。這樣的性格轉變,也正符合「忒休斯之船」的哲學命題:當一個人某部分被更換後,他還是原來的那個人嗎?
影片最後透過米奇之口告訴我們,每個米奇都是獨立的個體,即便擁有相同的記憶,他們的生命依然各自為政。但我同時認為,他們的內核仍是一致的,只是在面對不同命運與情境時,各自展現出不同面相:18 號選擇與馬歇爾玉石俱焚,17 號則在夢魘中挺身而出。
性格差異同樣體現在重新打印出來的 Gemma 身上。即便外觀完全重現,她卻剪去長髮——一個微妙卻明確的自我選擇。
如果套用佛洛伊德的心理結構來看,17 號明顯扮演「自我」的角色,負責處理現實的應對;18 號看似沉溺於慾望(性愛、毒品),彷彿是「本我」,但事實上他也展現了冷靜理性與道德判斷,更接近「超我」——如他對母親死亡的理性分析,以及計算精密地對付提姆時的行動。

4.所以說那個醬汁呢?
或許有人會好奇,為什麼伊兒法(Ylfa)如此著迷於「醬汁」?
這裡其實藏著一個社會階級的密碼。太空中大多數人吃的是壓縮食物,像菊花茶這樣的原型食物極其稀少,因此能慢熬出一碗醬汁,不只是品味,更是地位的象徵。馬歇爾刻意多次強調這點,正是要劃清他與普通艦員的界線。
那他們不怕引發不滿甚至叛變嗎?或許怕,但有其他的東西凌駕在此之上。
因為炫富的精髓就在於「要讓別人看到」。真正的享受,不是自己偷著樂,而是讓旁人看見、忌妒、渴望。這些眼光才是權力的調味料,也是馬歇爾唯一掌握得住的東西。
換句話說,他追求權力,並不是為了造福群體,而是為了被看到、被承認——這樣的領袖,無疑是空殼。
題外話,宣傳活動中也是提供不同的醬汁供民眾選擇,而電影是否是我們這些觀眾人生的醬汁?
5.死亡是什麼感覺?
關於死掉以後的問題,米奇其實是無法回答的。因為重新復活的個體只能從上次存檔處接續。這也點出一個生物演化上的現實:衰老與死亡是物種得以延續的機制,資源應該流向年輕個體,才能讓基因更多樣。這點在《天地創造設計部》有詳述。
我們多數人不願意衰老、死亡,在於必須面對虛無。但有時死掉也是一種一筆勾銷解脫,必須永生永世以一個身分活下去反而是一種折磨。
我覺得故事最後炸毀打印機讓米奇回復到一條命狀態,去映照同一演員的作品《暮光之城》多少有點惡趣味。

補充:小說與導演風格的差異
稍微查閱了小說介紹。
我認為奉俊昊導演會想翻拍這部小說不無道理,奉導演和原作兩者都有對社會議題的探討,同時具有黑色幽默。但原著是把時間序列切碎不停回憶,導演則主要順時間現地拍攝,使觀眾更容易將 1 到 17 號視為同一個「人」。
但這種辛辣切割殘酷社會卻又用黑色幽默輕輕帶過的風格,註定不是所有人都買單。因為導演沒有給出一個對於困境的解法,或是一個救世主力挽狂瀾,也沒有「轉機」;他只是不斷拋出問題,讓我們面對那份無力、那份困惑。或者用一連串的失控推展故事。
但他真的沒給出答案嗎?
我認為有。他選擇在喜劇包裹下,送出一份極其沈重的現實觀察。這部片像一道湯,要耐心咀嚼、慢慢熬,才能品出在喜劇下的辛辣與悲哀。就如同片中關於哲學的問題,我們可以直接禁用打印機——這樣就無需討論靈魂、記憶、意識與人性的本質;但我們也可以選擇深挖,鍛鍊自己面對荒謬世界時仍能思辨的力量。
你可以把這部電影當作一場科幻娛樂看完就忘,也可以,讓它喚醒你某種正在沉睡或刻意避而不談的情感。

我的其他影視分析
1.《正港分局》—— 在《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後,毛毛白死了
2.Netflix《最後通牒:酷兒的愛The Ultimatum: Queer L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