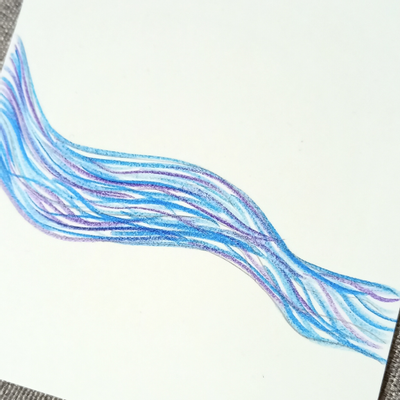夏日午後的河濱,是接近地獄般的存在。
柏油被陽光灼得微微顫抖,空氣黏稠得像沒攪勻的蜂蜜。
我原本只是打算跑個十公里,順便接受某種戶外三溫暖式的懲罰。卻沒想到,這趟慢跑會改變我對音樂、聲音,甚至這個城市的看法。事情就這麼開始了.
她出現得毫無預警,就像都市傳說中那些介於實體與虛幻之間的角色。
從遠處的自行車道疾馳而來,像是灌滿怒氣的疾風撕開了我午後的慵懶。
她穿著亮黃色運動衫,頂著一副反光墨鏡—那種只有便利商店架上才會出現的款式。車沒啥聲音,但她自己唱得震天價響,是一首熟悉的流行歌。
那歌我很喜歡,旋律應該悅耳,歌詞應該溫柔。
但她加速而來的某個瞬間,我確定:『走音了!』
非常明顯、毫不遮掩的走音。像是有人把CD的音軌偷偷用指甲刮了一下那樣。
在我意識過來之前,已經忍不住大喊:「You're out of tune, dummy!」
不知道為什麼我用了這麼孩子氣的語氣-還用英文,也不知道她是否聽見。但她真的停下來了。急煞,一瞬間像時光被壓成一塊硬糖。
歌聲沒有停.
然後我發現:音準變正常了。
歌聲恢復成我記憶中的版本,準確無誤。
我的腦中此時蹦出一個詞:都卜勒效應。
高中物理課本上某個角落的幽靈爬了出來,吹著口哨一邊朝我點頭示意。
音速約為每秒340公尺,而那騎士的速度大概是時速20公里—也就是5.56公尺每秒。當她迎面而來時,聲波被擠壓;遠離時,聲波被拉長。這些看不見的壓縮與拉伸,在耳朵裡造成約3%的頻率差。
八度音之間的頻率差是兩倍。一個半音約是6%的變化。
換句話說,剛剛奔馳而過的瞬間,歌聲的音高偏移了大約半個半音—不多不少,剛好讓整首歌聽起來像是在犯錯。
那是一種非自然的錯位感。
音符不再停留在該停的地方,就像有人偷偷把日記裡的句點換成了逗號;你知道哪裡怪怪的,但又說不上來是哪裡。那種違和感,像是在嘴裡咬到碎沙。
突然意識到:這種都普勒效應導致的走音用 distorted 才對!
那騎士朝我點點頭,又眨了眨眼,像是『你終於搞懂了!』的心領神會。
然後她再度向我飛馳而來,還唱著同一首歌。
我下意識的驚慌躲閃,腦袋卻不受控的發現:這次沒有走音。
唱得準極了,就像某種本能的音準補償.
「奔馳的音樂天才?」我喃喃地說。
她彷彿預判了我的預判,甚至預先計算了我們之間的相對速度;她算計了一切,還有那驚人的聲帶-補償得如此自然,如此從容。
交錯瞬間,她向我揮了揮手,就這樣舉重若輕的帶著歌聲繼續前行。穿過午後陽光的顫抖,穿過熱氣與幻覺,消失在下一個轉彎。
我呆愣在原地,在這個以科技著稱的城市,感到無以名狀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