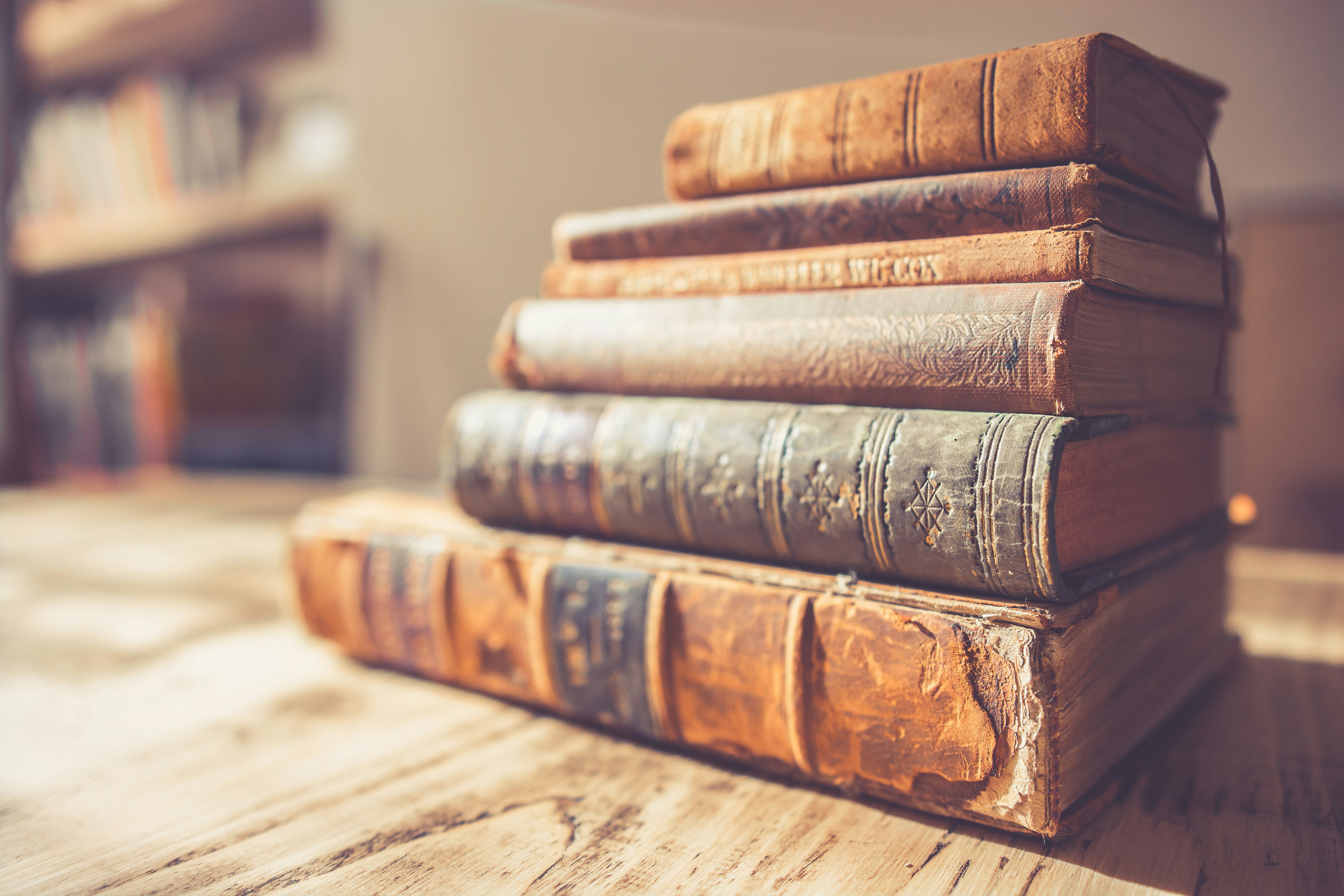【初稿寫於2023年12月,2025年6月修稿,文中仍保留部分當初敘事時序】
文言文的公共爭論稍歇,我想從一個公眾討論很少碰觸到的層面談一下。這個層面較不涉及課綱政策等技術爭論,而是想談文言文本身在當代文明中較深層的意義。這涉及東西文明的跨科研究,包括哲學、史學、美學、社會學、人類學甚至法律政治與經濟,然而網路書寫畢竟不是學術寫作,因此我會略去許多知識細節,搭配自己的心得體悟,扼要地說。
從赤壁賦談起
先從我最近(2023)一項與文言文有關的生活經歷談起。兩週前我造訪故宮,觀覽本季的重磅展出──久未現身的蘇軾名作〈前赤壁賦〉真跡。書法部分且不多論,就造文設詞而言,前赤壁賦寫得真好,經典名句密度極高,幾乎遍佈全篇:「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正襟危坐」、「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寄蜉蝣於天地,渺浮海之一粟」(後世流變為「渺滄海之一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於我皆無盡也」、「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洗盞更酌」、「杯盤狼藉」、「不知東方之既白」。逐句誦讀,只感一股擋不住的超絕之風隨著字句撲身而來,直教讀者見天地、見蒼生,見自己。這樣的大化文章,如何成就?
我得說,非文言文難經營出此等氣象與境界。
文言字句具有「聲形凝鍊」、「排比對稱」的視聽特性,此等物性特徵可透過人類的身心耦合機制帶出「直通對象」又「與物同觀」的獨特審美感與節奏感──我們讀文言文不只看其字,也誦其聲,搖頭晃腦或許誇張了些,但是你誦讀像赤壁賦、滕王閣序、岳陽樓記、唐詩宋詞等篇章時,頭頸身姿是很自然就能隨其音節而律動的,其所呈現的氣韻起伏、物我相契、悠闊氣象與浩遠意境,白話文很難表現。隨便挑其中一句試著改寫成白話文即知。這不是說白話文寫不出前赤壁賦傳達的某些感受與道理,而是無法完全重現文言文的「整體效應」,那是把存在體悟、審美感受與文辭音貌整個結合在一起的身心效應。
譬如很簡單的開頭「清風徐來,水波不興」這句,用的字跟詞都是「凝鍊」的,也就是凝聚在一起如同精鍊過一般,並且因著每句字數相同而有韻律感。改寫成白話文就是把凝鍊的字詞「展開」、「稀釋」,譬如可以寫成「清風緩緩拂過,水面平靜無波」,這還不是大白話,若再白話/展開一點,可寫成「清爽柔和的風,緩緩地吹過來,水面仍然平靜,一點波紋都沒有」。仔細觀察,所謂展開、稀釋,就是用更多的字詞去填補少量字詞,這包括名詞、形容詞的多字化,還有副詞、連接詞及語助詞的顯性化。形象地說,文言文是密實地紮在一塊兒,白話文是加水加料把它揉開。
白話文跟「語文拼音化」(language化)有關
從現代主流心智角度看,文言文就是因為字太少、全黏在一起,所以詞意曖昧、語意不清,不像白話文(模仿拼音語文)有明確的主語賓語、時態標示、主動被動、限定子句及繫詞介詞等表達結構,可以達成「清晰溝通」目標。這就是「語言=溝通=工具」這項語言觀的擁護者之所以排斥文言文而推崇白話文的關鍵。要詳細闡述這種語言觀的問題,牽涉到現代世界的文明預設與存在哲學,無法在一兩篇寫作中說清楚,未來有機會再談。在此,僅先簡要地說明:主流語文觀是偏向「工具化、形式化、抽離化、理性化、原子化、功能化、欲望化、資本化、心物二元化、強人類中心性」的語文觀。在這種語文觀下,拼音語文及白話文的價值當然遠勝文言文,因為前者以「心靈對世界的分解擺布」及「意念之間的明晰界分」作為語符建構及詞句組織的原理,藉此「形現世界」或「開顯世界」,這正是(西方)「現代文明」的演進基軸。白話文是接近拼音語文的「分化」、「拆解」跟「組裝」的分析性語文,文言文則是更貼近漢字固有「整全」、「直觀」及「氣韻」特性的綜合性語文。
由於白話文的用字遣詞、語句結構、音節韻律都較疏而鬆,它所媒合或形構出來的身心感受跟文言文不同。白話文是接近拼音語系的語文模態(導因於西方的全球擴張),拼音模態的特色是字符並不直接來自世界的感官形貌(象形,譬如「日/月」)與直觀關係(指事,譬如上/下),而只是話語聲音的紀錄符號(譬如英語用26個字母拼出各種跟外在世界沒有直接對應關係的聲音符碼),這也就是為什麼西方語文被稱為表音文字而漢字被稱為表意文字的原因。表音語文是抽離於世界形貌又回過頭重組世界形貌的,這種抽離與重組就是締造「觀念」(idea)、「概念」(concept)與「邏輯」(logos/logic)的基礎。
這裡有必要說明一下,「語」跟「文」本來是兩種東西。前者是聲音媒介,後者是視覺媒介。像「英語」這樣的語言系統,是使用拼音文字來記述其發聲,即「英文」。「漢語」則對應「漢字」或「漢文」(字跟文的區別就不細談了)。拼音語在語言學上被稱為「屈折語」,相對於漢語之為「孤立語」。但應注意,拼音「文字」是高度附屬於拼音「語言」(language)的,基本上它的文字系統全是為了記述發音,所以西方語文是「語音中心主義」,現今一般人所理解的「語言」,基本上就是來自「language」這個語跟文沒有明顯區別的概念,這是西方中心的語言典範觀。相對的,漢字(視覺)跟漢語(聽覺)則是可分的,它本來不是西方那種「language」,但在「現代化」(全球西方化)過程中,漢語文明一直有股力量想把自己language化。基本上,當今世界除了漢語文系統,其他稍有規模的語文幾乎都是屈折語及拼音系統(註1),所以,漢語文可以說是抗衡「人類開顯世界之話語系統全面lanuage化」的最後堡壘。而古文或文言文便是比白話文保留了更多漢語文原初特質的珍貴遺產。
「屈折語/孤立語」開顯世界的不同模態
我們稍微深入一點談世界開顯(即身心狀態)問題。19世紀德國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對拼音語文及漢語文進行了深度對照考察。這是支有歷史及文明比較意識的學術流派,跟20世紀後主導全球的那種以形式邏輯做普遍語法學研究的語言哲學不同,後者是以印歐的語法結構來壟斷人類對世界的理解。
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展中,洪堡特(Humboldt)堪稱是開創性人物,他在研究了世界主要語言後,發現漢語非常特別,只是將具有實質意義的概念詞排列起來,而不像屈折語運用詞類的區分把我們對世界的理解轉化成有機的思想結構,洪堡特認為這使得漢語的世界理解必然受限於現象世界的不確定性,無法達到思想的純粹觀念性、以及精神的自由主宰性。可是漢語文明卻能達到相當高度,這令他十分困惑。經過再三研究,他確立了漢語的非語音中心特性──不像拼音文字只是拼音語言的記述符號(文字本身沒有獨立意義),漢字與漢語是相輔相成的,漢字雖不是字母文字或音節文字,卻仍能以表音的圖象來實現聲音文字的作用(形聲字);但漢字又同時是概念文字,因為它的文字圖象部分,一開始就包含著對它所標記的對象之真實呈現作用(象形指事)。這就是漢字的音義同構性質──「漢字」本身就是「漢語」開顯世界的一個環節,而非純粹記音符號。
雖然歷史比較語言學擁有跨文明視野,但終究還是脫離不了西方優越的心態。像洪堡特就還是認為:人類精神的自由表現,在於它能以語言的聲音系統來轉化外在的對象世界(我用我喉嚨及口舌發出的聲音與音節的組合來表徵外部對象),以成為它自己的觀念性世界。簡單說,就是人類語言應該要能脫離外在現象世界的束縛,用人類自己決定的樣態去建構一個外在世界。很明顯,洪堡特的語言觀是極為典型的西方主義及強人類中心主義,也就是極度強調能動性。這種存在哲學或世界觀認為「人」是一切存在物的軸心,整個世界乃至宇宙的樣貌應該由人主動去建構/開顯出來,天地萬物都要繞著人類打轉。東方的存在哲學與世界觀則非如此,而是把人跟天地萬物置於比較相近相融的位置,這種「天人相合」精神是一種非人類中心或弱人類中心主義,由此發展出來的符號媒介系統比較能「直通對象」又「與物同觀」。換言之,歷史比較語言學依舊難脫三種印歐語言本位的偏見:1. 語音中心主義,2. 主知主義,與 3. 邏各斯中心主義。
另一位踵繼洪堡特的語言學家史坦塔爾(Steinthal)則指出,漢語並不是一種由形式性思維所主導的語言類型,它的表達是由思考內容本身的關係性所規定的。亦即在根詞組中的表象連結,並不是透過將對象世界分析成個別的基本單位,再由語法依思想的知性行動加以綜合而成,而是依對象對於心理感受的重要性,以心理學的價值認定,將事物之間的表象關係以詞組的方式表達出來。我們常說傳統華人不是用「邏輯」思考,而是用「情理」思考,語文模態的差異在此扮演了不可忽視的因素(註2)。這些語言特性其實不只有語言學或哲學意義,還可以反映在許多不同學科所關注的議題上,譬如在法律、政治及社會領域的研究中,「邏輯模式」未必優於「情理模式」。這部分牽涉更深廣的分析,就先不多談了,重點是藉此彰顯「拼音語/language」的真理體制與典範迷思──白話文正是這種典範的產物。這便是本文副標題「突圍language帝國、開顯另一方天地」旨趣所在。
下面我們就來談談古文/文言文對一般人更有直接意義的面向:存在美學。
審美境界
漢字的基本構造為象形指示,是對天地自然的觀物取象,這種根源於取象分類的取法乎天地自然的生發理路,本身就是能指與所指合一的文字,觀其象而得其意,不像印歐語系拼音文字以各種字尾、時態、賓主變化,尤其是be動詞之存有式聯繫,來對比搭連出意義,這是一種能指與所指分開的語言。人類的身心狀態與意識模式是緊貼在語文上的,漢字獨樹一格的構造理路,衍生出象其物宜、天人相應等整體直觀把握的感知模式,加上文言文又著力發揮了漢字單體單音的特性而布置出聲形對仗的韻律節奏,這整套文字特性經營出一種邏輯性語文(拼音語文/language)所難以達到的審美感受與美學境界。像「山」、「日」等字,幾乎就是自然物的直觀形現,說出「白日依山盡」的同時,畫面與身心整體的覺觀是同時出現的。但把這句話用英語或白話文表達,多了符號間的邏輯搭連及曲折蔓衍,感受便隔了一層。章太炎曾謂:「單音語人所歷時短,複音語人所歷時長。是故複音語人,聲餘於念,意中章句,其成則遲;單音語人,聲與念稱,意中章句,其成則速。」巧妙地道出了單音單體的漢字文言文較之多音曲體的拼音邏輯文特出之處。遺憾的是,近代以來席捲全球的西方現代性,卻把後面這種語言所拱出來的身心模式論述成比前者更進步更優越。文言文從此蒙上了落後無用的形象。
我寫這篇小文,便是想翻轉人們習慣的西方現代性語文觀(language觀),指出白話文言之別,並非僅止於輿論所聚焦的那些實用性、溝通方便等工具理性之爭,而是涉及更大的人類文明與存在哲學問題。在全球被一致language化的時代,身為傳承漢語文的社群,我們應該對文言文保有更開闊的眼界以及更大的自覺性。這並非要大家成為文言文高手,而是對文言文具備基本的賞析素養與感受能力。當我們具備了這種基本素養與能力,就掌握了不同於白話文/邏輯文的世界開顯媒介與審美路徑。於是我們便能在漫漫人生路上,擁有了一項解脫邏輯符碼與工具理性枷鎖的珍貴資產──我們不再只能依循西方現代性設下的存在美學而無止盡地投身於技術支撐出來的自我創設漩渦中,也不再只能糾纏於資本主義為我們編織好的金錢及欲望之無邊羅網中,而是能隨時在日常生活的靈光一閃或心念一動間,拾取一段文言佳句,昇現一篇華雅辭章,領受古典書寫所散發的跌宕姿態、萬千氣象與天地美學,怡然度過悠悠歲月。
就像這樣: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論語)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易經)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陶淵明.桃花源記)
~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王羲之.蘭亭集序)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吳均.與宋元思書)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王勃.滕王閣序)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李白.行路難)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蘇軾.定風波)
~衆裏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辛棄疾.青玉案)
~胸藏邱壑,城市不異山林;興寄煙霞,閻浮有如蓬島。(張潮.幽夢影)
~酒罷問君三語,為誰開,茶花滿路。王孫落魄,怎生消得,楊枝玉露。敝屣榮華,浮雲 生死,此身何懼。教單于折箭,六軍辟易,奮英雄怒!(金庸.天龍八部回目.水龍吟)
註1:精確一點應該說:世界上現存較有規模的語文,除了漢字是音意同構外,其他幾乎都是表音文字,包括印歐「拼音」文字,及日文假名與彝族的「音節」文字。不過拼音文字仍是最具宰制力的主流,因此本文敘事從簡,就不贅述音節文字了。
註2:關於德國歷史語言學派對拚音語文及漢語文更詳細深入的觀點梳理,可參閱林遠澤〈從洪堡特語言哲學傳統論在漢語中的漢字思維〉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