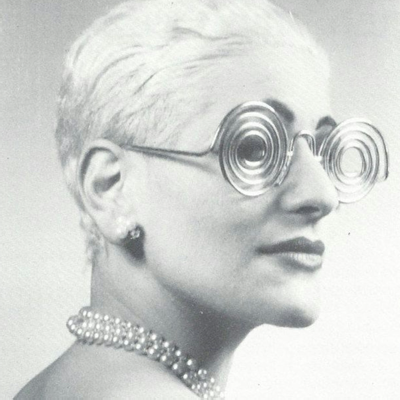致謝 Savoir|影樂書年代誌 刊登本文:https://www.savoirtw.org/article/4859 (&picture credit)
常見到在不同場合,例如煙火秀、音樂表演、演唱會等等,會有人拿起手機拍攝,甚至錄下全程的影片,每每讓我好奇,到底是為誰?為什麼而拍?真的會找時間回顧再看一次嗎?或許相片多半會有,只不過長達數十分鐘的表演,除非是官方錄製的影像,否則難以想見回顧看完。雖然有些人這樣做只不過是為了上傳到社群,告訴大家:「嘿!我在做這件事!」,似乎是存在於他人的觀看中—或說是在他人的觀看中存在。然而,攝影的過程無論如何用心,必將無法觸及真實。
曝光一小時、晃動器材,都是以世界的一部分—空間、時間—為攝影客體,使用濾鏡也是一樣的,即是以現實的對象為拍攝標的,如此先有基底才可能經由濾鏡加工,就像先有食物才可能有食品一般。但是,我們到底能不能在攝影的過程中觸碰到真實?或者,攝影正好是將我們排除於真實之外的活動媒介?
荒木經惟所遵行的紀實攝影以捕捉人類的本質,「無論廣告或任何事物,所謂的創造,都必須以紀實攝影為起點;而所謂的紀實攝影,就是捕捉人類的本質。...我有一個很老式的信念,認為只有真實之物才能夠創造同樣的真實之物。所以首要之務,就是撫臀、吶喊,以剝除虛假的外殼。」(荒木經惟著,彭盈真譯,《寫真的話》,頁181-182,木馬文化出版,2009.02)然而,在我們以五感去接觸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接觸到了一個對象(物、事、人),在這個當下我們所接觸到的是這個對象的真理,我們也經由感官獲取了關於這個對象的知識。(於此,暫且不論感官的誤導性,因為攝影無法處理知識論上經驗方式的問題)
然而,這個瞬間的真實,只有這個瞬間是「真實」。
當我們拿起相機—或是所有其他攝影器材,我們透過鏡頭看到—如果這能稱為看到的話—攝影的對象,當然原先我們經由感官去獲取該對象的知識—去認知到該物體的存在,物體與眼睛之間也有著各式各樣的介質,但這些並不阻礙於光線經由眼球的構造成像於視網膜上。然而,相機阻絕於眼球與物體之間,就像是離開房間後的房間椅子還在不在房間的問題一樣,亦即,我們如何「知道」椅子還在房間裡?問題的懸解並不會因為牆面改成玻璃材質而獲得解決,而這就如同透過相機的鏡面去觀看一般。
空間層面的問題以外,時間層面亦有其疑難。換言之,空間的問題或許能被不透過鏡頭觀看並進行攝影給解決,但時間的問題則否。上述所說的真實是以「瞬間的」這個形容詞來特定,換句話說,這裡的真實所具有的知識是被時、空間給限定的,而會採取如此狹義的定義,並非便宜地為達致結論而為,卻是因著實際上攝影經常有著「留下當刻的_」(底線可填上例如美好、景象、殘酷等等語詞)如此的普遍印象,才有如此定性真實的概念的必要性。
也就是說,某個瞬間的真實,在人體生理極限的限制下,縱使在極快速的時間按下快門讓光成像於媒體上,該影像仍然與那「某個瞬間的真實」有所不同,亦即,攝影固然是試圖捕捉「某個瞬間的真實」,但實際上其所能做到的,永遠是一個對於「下一刻瞬間的真實」進行捕捉的嘗試。這裡使用嘗試、企圖來修飾攝影的行動,正是因為無論是某個瞬間或是下一刻,攝影的對象自身與攝影的對象的影像,並非理所當然地不證自明。
攝影活動中的真理距離正是時間差,是機制的極限,無論是人體生理的機制,又或許是機械運作的機制。換句話說,快門無論是千分、萬分之若干,攝影成像的快門運作所需的時間,是一個永恆地阻絕了個體經由相機與攝影獲取(瞬間的)真實的知識的障礙。總而言之,在這裡能整理出的是與「(瞬間的)真實」有所不同的,不僅是「下一個瞬間的真實」,還有著「下一個瞬間的真實的影像」,其間並非皆同。
那我們使用相機攝影產生的影像,又是什麼?
相機的成像與視網膜的成像是相似的,因此我們可以假設相機的成像是另一個人所「看到」的,如同前述暫且擱置感官獲取知識的可信度問題,以此作為前提進行討論時,問題會是既然我們無法看見別人所看見的,那麼我們怎麼「知道」相機所看見的會是我們在同一時刻同一位置所看見的(尤其該時刻轉瞬即逝)?這就像即便撇除空間上的障礙讓兩個主體在同一個物理位置也在同一個時間上觀看同一個物體,我們也無法確知這兩個主體所獲取到的關於該物體的知識是相同的。
再者,我們所能獲取關於相機看到什麼的媒介,是經由相機所形成的影像,然而這個影像與攝影的對象自身並未符應已如前述,我們既無法確知相機的影像等同於相機攝影的物體自身,就不可能經由攝影所形成的去接觸到真實。
惟,相片總被認為是種「紀實」。這種象徵意義正是以相片作為言說所創生的,桑塔格這麼說過:「它於黑暗中亮起,經由許多人分享,然後從眼前消失。與文字記錄相反—文章是以其思想、典故和詞藻的複雜去吸引小眾或大眾—照片只有一種語言,而且是說給所有人聽。」(Susan Sontag著,陳耀成譯,《旁觀他人之痛苦》,頁31,麥田出版,2016.01,三版一刷)然而,相片所形成的真實是被創造出來的,是科學、機械的運作下的真理產製過程,進而,這種真實是一種被動態所形成的集體幻覺。攝影不僅是經由鏡頭的框架去圈劃出我們要捕捉—同時排除—的而已,也就是說不僅是「詮釋」現實,詮釋的前提是有被詮釋的對象存在,攝影卻更是去「創造」真實。因為,攝影是在這個活動完成後,宣稱了(瞬間的)真實的存在。
即便從詮釋的觀點而言,攝影—shoot—射擊,已讓使用相機攝影所具有去決定現實的權力特質十分顯明,也就是對特定物事意義的詮釋壟斷使得影像具有暴力性格,即攝影者將自身對物事的詮釋強加給他人。但是,這裡的論述所說的是,攝影不僅是詮釋現實—真實,更是去創造真實—現實。那麼,這將比意義強賦更加地暴虐,因為攝影的真理產製過程是如此的言說宣稱:這才是真實。如此地不可動搖、如此地被所有人給接受、如此地不被質疑,如同 1+1=2 的邏輯真理,甚至連質疑者就如同心神異常的偏差者一般,但是,攝影的紀實性是否如此真切?
或許,經由攝影術所產製出的各種成品,例如電影、電視、劇集、相片等等,其實都並不是真實?尤其,人類社會所充斥著的無數媒體,甚至可以說不可計數的媒體正是人類社會的今日,我們所生活其中的這被媒體所建構的世界,會否只不過是個巨大的群體全息投影(Hologram)?
這就是攝影的矛盾:宣稱了真實,也阻礙了真實。而我們就這麼一直地相信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