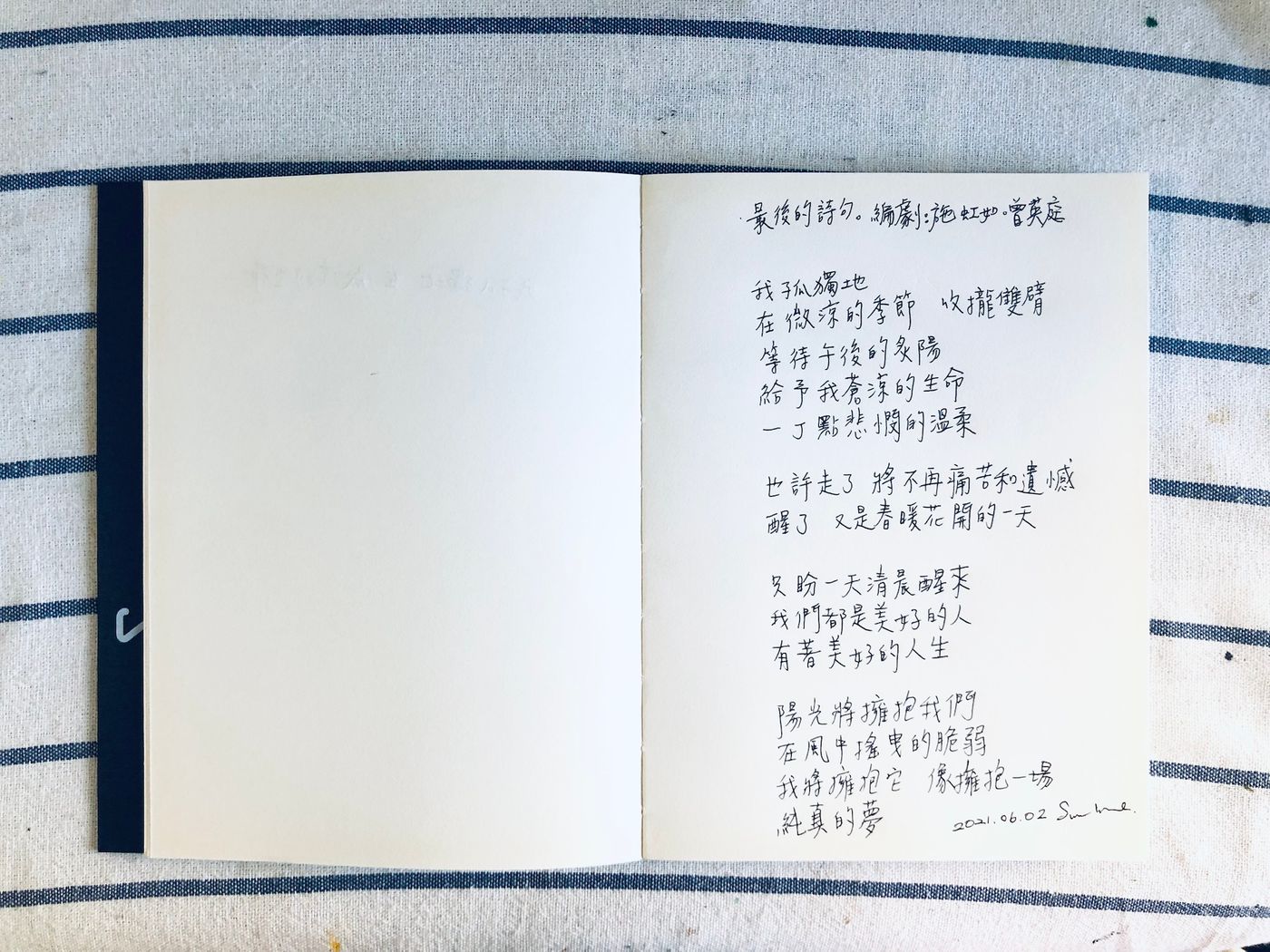夏日太耀眼了,晚上六點多的天色,還是燦若鎏金,像是把記憶燃燒殆盡那樣激情;低頭寫了一天稿時,忽然被滿天的艷色所驚動,原本冷調銀白的鐵窗,雕上了帝國的輝煌,彷彿只要一開窗,就能得見滿室瑰寶。
都說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但鄉村裡的向晚總有天長地久之感,大概是看天吃飯的農人,沒那麼多細緻的悲喜,只有田推著田,天連著天,空氣中瀰漫著烤甘蔗的炭香氣;幾隻夜鷹蓄勢待發,雖是求偶,大概總不遂心,老在太陽下山前哀哀的試起音來,又在黎明前筋疲力盡的默聲,情到深處,總歸無聲。
日薄西山的景象,不免叫人幽怨思鄉,但哪裡是我的故鄉呢?小鎮如歌如畫,人情醇美近似桃花源,反倒是那記憶裡的北地荒城,樓橫著樓,人隔著人,霓虹冷艷如刀光,劈殺一顆顆涉世未深的心,也容不下春天,所以我才背著身,一路走到這裡,不說再見或不見。於是知道,那是回首的方向,縱然,半生寂寥。
1984年,待產的母親坐在床上,電視螢幕唱起八點檔電視主題曲「最難忘的人」,這戲我自然沒見過,只知道是女孩周旋在生父與養父間的悲傷故事,過些日子,母親生下了我,也是一個在人生中不停尋找父親典範的女孩;「最難忘的人」的閩南語版本是「黃昏的故鄉」,叫著我,叫著我,黃昏的故鄉不時塊叫我……我想起在河畔等待淡水暮色的歲月,看渡頭餘落日,山映斜陽天接水,那裡並不快樂,但,那裡有我的鄉愁。
,歌詞創作者林夕曾說,因為喜歡夢的簡體字「梦」,才取「林中夕陽」的意境為名;一生若夢,林間昏鴉都知道歸巢,而我們卻在滾滾紅塵裡半夢半醒,誰問過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