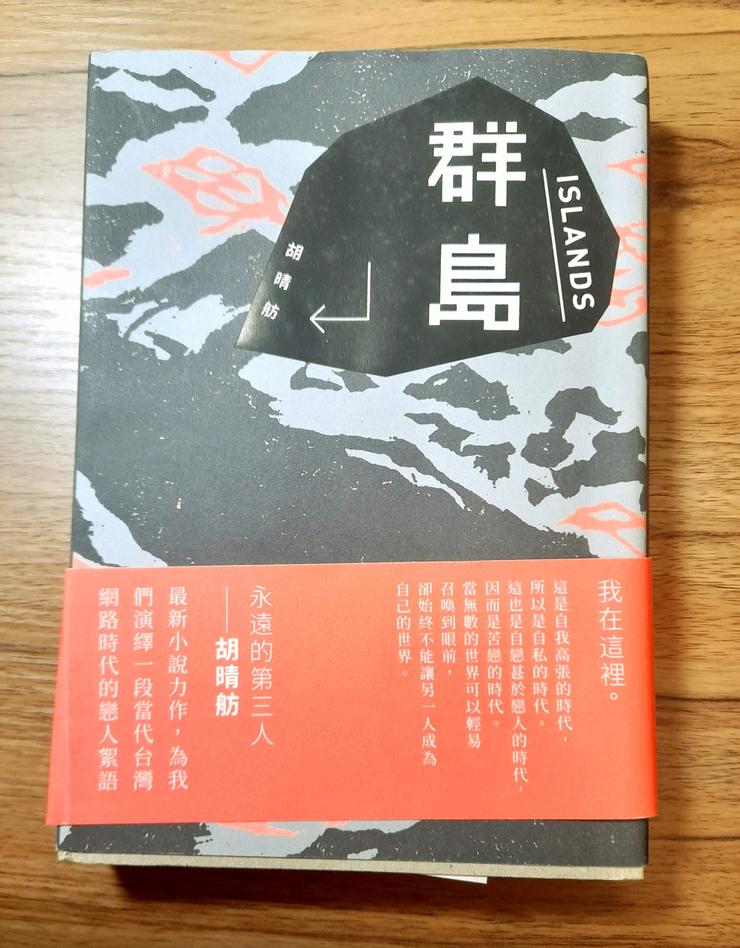2019啟明冬季書評大賽首獎
漆黑之中,只有水,溫暖,聲音。洞穿真相的清醒者,口吻練達通透如君王,行動卻孱弱如嬰兒,飄忽如遊魂。
這是《堅果殼》(Nutshell)迷人之處,大膽,別出心裁,誘引讀者跟隨這陣敘事聲腔了解真相,一層層剝開人心的暗幕。作者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出入語言的功力令人驚嘆,刻意製造敘事限制,抹消視覺,整個故事全以聲音構成,胚胎在母體內「傾聽」一切,極端靈敏地捕捉各種訊息碎片,尤著迷於人們對色彩、光澤、外貌、的形容詞,喧囂暈眩,東拼西湊,迫不及待通過他人的眼睛,勾勒出一個世界的倒影。胚胎憑著無限想像,馳騁在自己的意識國度,做開疆闢土的王,不時對這個還未親眼目睹的世界冷嘲熱諷,獨特聲腔形成張力:稚嫩,老練,赤裸,荒謬,愛,與恨,冷靜而節制,纏綿卻憂傷,聚攏為一個未出世孩子的面容。一枚小小胚胎,伸展手腳,卻撞上子宮壁,
我在這裡,在某個女人的肚子裡,上下顛倒,耐心地抱著胳臂,等待、等待,同時揣想我是在誰的肚子裡,為的又是什麼。
在一個被倒置的世界,等待出生,或死亡,或任何的悲喜劇,他無所不在,實際卻不存在,像多餘的遊魂,還沒誕生便開始飄盪,強烈深沉的無力感,受棄絕的傷害,形成生命最初的印記,嵌入靈魂。這是《堅果殼》的高度諷刺,作為《哈姆雷特》(Hamlet)的現代變奏,將王后與小叔合謀毒殺國王、王子復仇的悲劇,轉譯成卡在子宮動彈不得的胚胎,得知叔父與母親殺害父親的整起計畫,並未合謀,卻被迫參與其中。讀者直覺地跟隨王子,聆聽(且嗜血地期待著)這樁謀殺,見證人物各懷鬼胎,自說自話,在流暢的敘事之中,我們不禁要問:一枚胚胎,想法怎會如此老練?隔著母體取得的資訊,究竟遺漏了什麼?以及,他所拼湊的「真相」代表事實,或許也是自說自話,偏頗地複製了誰的觀點?
在懸疑驚悚的謀殺故事之外,伊恩・麥克尤恩的深層提問是:我們所認知的「真相」,究竟是什麼?人的思考,真能完整而獨立嗎?胚胎王子在溫暖母體內,被羊膜包覆著,書名比喻就像一枚「堅果殼」,薄脆,而難以穿透,他依賴各種雜亂、碎片化的資訊辨識世界,聆聽到的話題無所不包,小至個人的家庭醜聞,大到民生、經濟、政治、戰爭各種包山包海的評論,範圍橫跨遙遠的歐、美、亞、非洲,他得知一切,卻從未親眼所見。這枚堅果殼,宛如微型的現代社會。
《堅果殼》延續《哈姆雷特》對正義、真相、生命價值等探討,以現代世界觀重新架構:在一個民主社會裡,訊息紛陳,過於喧囂,人們卻像身處暗室,看不見事情的全貌,在思想與行動面前,軟弱無力,小說中隨處可見原著的變形。
哈姆雷特從父王鬼魂的口中得知母后與叔父共謀的真相,
天啊,要不是我做了許多噩夢,即便被關在一個堅果殼裡,我都能自命為擁有無限空間的君王。
他自命不凡,擁有思想、高貴純潔的心靈,卻因世俗的醜惡蒙塵,To be or not to be的沉痛自問,是對命運控訴。在巨大陰謀面前,哈姆雷特遲疑著,自己該做什麼、當在「正義」中扮演何種角色──默默忍受命運暴虐的毒箭,或挺身反抗人世間無涯的苦難,通過鬥爭把它們掃清,這兩種行為之中,哪一種更高貴?復仇,將帶來正義,或為生者平添永遠的不平靜?他心中怒火熊熊燃燒,卻因關係的矛盾而退縮,父王鬼魂譴責他的不作為,使其深受罪疚痛苦折磨,近乎發狂。他對母親既愛且恨,在一次意外中誤殺了無辜之人,最終,哈姆雷特要償還自己的無心之罪,大仇得報的那一刻,他通過死亡,彰顯人間無可動搖的公理正義。
《哈姆雷特》的兩難,既是社會的,也是個人的。高貴的王子,在人世擔負正義的責任,所走的每一步,都在思想與行動間拉扯,即便犯下「不做決定」的錯,也出於自身意志──命運實不可控,但哈姆雷特仍是自己身體的主宰(因而必得為誤殺行動償罪),完成屬於他的英雄試煉。他的生,與死,引人同情、警惕或唾罵,完完全全應驗著哈姆雷特式的悲劇。
《堅果殼》的無力感之深,足以否定存在意義。伊恩・麥克尤恩將王子置換成胚胎,剝除浩蕩之氣,不受期待的生命,連命名都不需要,他想歸屬於父母,卻在出生前就失去了歸屬權,即便喃喃自語著仇恨或愛,無人在意他的原諒或不原諒,更諷刺的是,就連最卑微的復仇──自殺都做不到,即便如此,胚胎王子仍為自己是否應當行動苦惱不已,顯得可笑而荒謬。
除了他,故事裡每個人都目標明確,說著各自的「非如此不可」,一句慾望的魔咒。然而,關係的錯綜複雜、情感曖昧游移,沖淡了這句話的力道──楚笛與約翰分居,藉口需要空間,實則與克勞德圖謀不軌,又遲遲無法提起勇氣毒殺親夫,她在昔日與今日的愛人面前,語氣都不堅定。約翰愛楚笛,明知她與克勞德偷情卻裝傻,礙於情面不撕破臉,心口不一地為楚笛念詩。克勞德是貪婪平庸的地產商,慾望著兄長的妻子,他的言行,乃至於對愛都充滿算計。他們拙劣地「扮演」設定好的角色,卻處處嫌疑,小說的緊湊驚悚,不在謀殺本身,而更大量體現在人際互動裡,我們看見人物間愛恨夾纏,既欲望,又想從對方身邊逃開,明明騷動不安,還強裝沒事,寒暄吃飯,畸戀、亂倫、病態被壓抑在暗處,人們把自己塞進被規範的社會角色裡,互動頻繁,實則空洞疏離,關係的徒具形式,讓「非如此不可」成為世紀大謊。
這齣精心設計的劇本,是伊恩・麥克尤恩機靈的表演,大膽挑戰故事的平衡感,讓每個人,同時擔任另一個角色的變形,戲中之戲,映照人心的暗面。
克勞德與約翰,是最鮮明的對照。約翰彬彬有禮,浪漫多情,這名詩人彷彿舊社會中,理想主義的老派紳士。克勞德是地產商,強取豪奪,市儈、愚昧、利慾薰心,除了賺錢樣樣不及約翰,卻是現實中的「人生勝利組」,弒兄、佔據兄嫂、變賣房產的極端行動,意在爭權,彌補童年的缺失,證明自己能夠取代兄長。在變質的感情戲裡,楚笛一直掌控大局,直到愛蘿蒂的摻入,徹底引發她的緊張──相比於只有外表美麗無辜,內在罪惡腐敗的她,這名女詩人深具涵養,擁有真正的美麗,聰明,成熟,楚笛面對愛蘿蒂時,感受到被「篡位」。小說設計兩對情侶同桌吃飯,高下立判──克勞德與楚笛,就像約翰與愛蘿蒂的鏡中投影,仿製不成,在精神、才華、外型,甚至交往正當性,處處矮人一截,誘引出自卑、私慾、嫉妒、競爭、野心等暗面,情感的不正當,讓謀殺有了正當理由。
胚胎王子,以詩人約翰為自我的理想原型,父的存在,使「我」的生命成形,成為「正是」,因而他是血統高貴、具有理想的國王,父子以基因組相連,是命定、必然、不可違逆的。儘管如此,血緣的理所當然,卻非情感的理所當然,約翰從未考慮爭取他的撫養權──命定、必然、不可違逆的血脈竟遭無視,徹底否定了「我」!最終,這對父子為同樣遭到放逐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無所不在,實際卻不存在的胚胎,與生時軟弱、死後才具有重量的父親,都成了飄盪在人世的孤魂,畸零的存在。王子最深的恐懼,是克勞德──那平庸的俗夫,弒父娶母的仇人,亂倫的叔父──將取代高貴的血脈,成為他虛假的父親,等同宣告「我」的身世是徹底的贗品,王座失去神聖性。
角色之間潛在照映,每個人,都是某個人的原型,卻也無意識地扮演他人,意圖取代,在戲劇性的一刻,悚然發現自己的存在只是仿製品。這是作者的玩笑,整部故事本身即是語言遊戲──堅果殼,Nutshell,又有「簡而言之」的意思,一語雙關地帶出簡化《哈姆雷特》的企圖,搬動、拆解原著設定,成為零碎、失重、徒具形式的語言符碼,看似仿製,實則竄改──英雄人物失去神性,諷刺現代社會沒有偉大的悲劇,人們自我標舉,特異獨行,卻只是複述某種潮流,文化,價值的贗品。到頭來,這部經典的仿品,比經典更真實而諷刺地,貼近現代的種種荒謬生活感。
回到《堅果殼》核心問題,我們所認知的「真相」,究竟是什麼?人的思考,真能完整而獨立嗎?胚胎王子評論時,是近乎超然的存在,但他沒有目睹,沒有名字,為什麼能無所不知,彷彿已活過了千百年?小說描述,他是隔著肚皮,從廣播、電視得知的,意識先於出世,老練的評論,其實也只是複述社會的集體意識。
王子看穿密謀,理應帶來光明,卻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嬰兒,睥睨口吻讓人聯想到現代社會熱愛嘲諷,卻毫不作為的人們。《堅果殼》穿插大量瑣碎資訊,敘述與劇情不直接相關的外圍世界,對緊迫的謀殺造成中斷,讀者在那些段落感受到節奏的拖沓,這種沉悶,如實刻劃現代生活:廣播、電視、各種媒體傳遞爆炸的資訊量,卻成為生活中聽過即忘、不具意義的符碼,人們對世界的想像仍單薄扁平,這些資訊充其量不過是社交場合高談闊論的話題。
至此,我們看出伊恩・麥克尤恩的隱憂:民主社會的人們,正在面向多元的世界,還是活在一個訊息被無形之手掐住的,過於喧囂的暗室?那是政府、財閥、有心人士的操控,或者是自我的偏見,在暗室裡顧影自憐,尋找同溫層取暖而不作為?
先是哀愁,再來是正義,然後是意義。其他則是一片渾沌。
這是否代表伊恩・麥克尤恩對未來悲觀,徹底通向虛無的預言?
小說維持一貫的戲謔,不置可否,卻又帶點狡黠地,以精心調控的節奏,舉重若輕,在最後一刻將王子推向命運──既無法自毀,王子以「出生」為復仇,戳破羊膜的阻隔,將自己推離母體,罪惡的索多瑪城。見光的一刻,他終於看見母親的美麗面容,與父親形容得如出一轍,就這一眼,代價是更長久的監禁,主動地,迎向已知的悲傷身世。我們難以期待事情會有轉機,這或者帶有另一層悲觀:突破一層堅果殼,還有許許多多,被無形之手阻絕的暗室,無時無刻監控著人們的意識。即便如此,王子直面命運,或好或壞,他終究選擇了一次行動。巨大的犧牲,起自一個極其微小的動作,貫徹意志的一刻,迎來的也可能是自我的毀滅,或遭到社會更深的棄逐,一切不為人知,而這,是民主社會中理想之人如今擔負著的,無可迴避的命運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