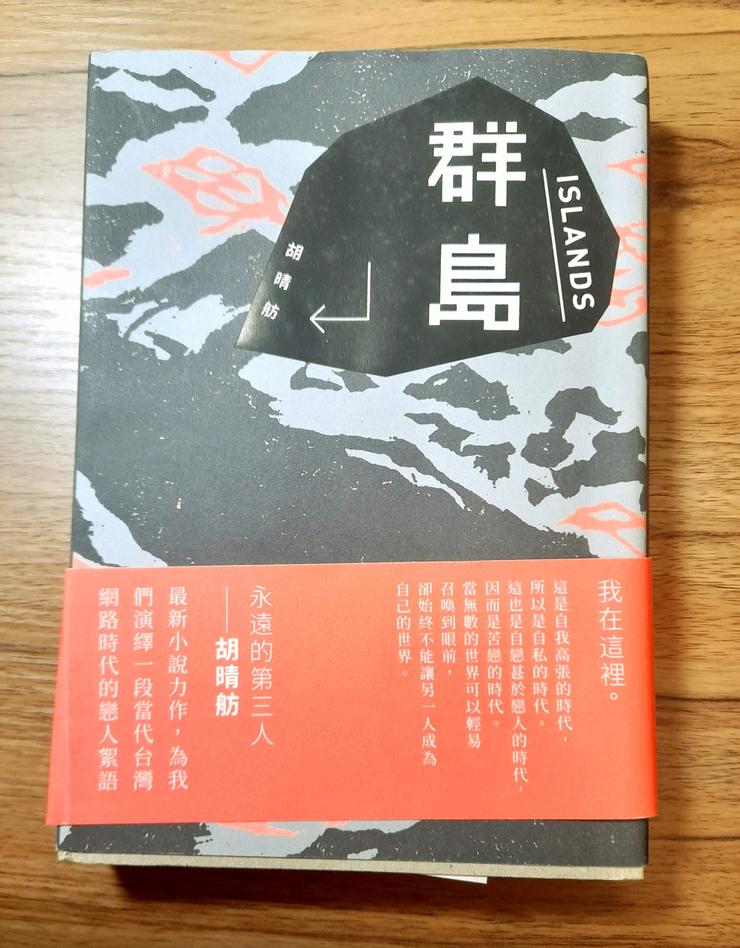【戰爭主題策展】
戰爭看似遙遠,但來襲時往往猝不及防,打斷所有熟悉的生活軌跡。這與後疫情時期的此刻一樣,疫情爆發後才發現再自然不過的日常如此脆弱。日常生活中細小的斷裂,讓我們明白熟悉的日子是再也回不去的。戰爭/疫情後的「非常」,成為我們的日常。
歪文系、癮君子、嘎拉嬉皮三位創作者共同發起「戰爭」主題策展,分別以文學、影劇、ACG等不同領域的作品,勾勒出我們眼中的戰爭圖像。戰爭不只有前線的磅礡與英雄,它也從細微瑣碎處滲透進常民生活。除了本文,以下是這次的策展合作文章,歡迎與我們一起用不同的視角,看見「戰爭」:
炮火隆隆焦土還冒著熱氣,遍地是受傷流血的身軀,如果有希望,寄託在領軍終結戰事的英雄身上。這些是我們在歷史記錄得到的,戰爭印象,似乎距離這個和平時代有點遙遠了。然而,「經歷戰爭」的方式不是只有從軍,不同身分與年齡層的人用各自的方式活著,在他們的回憶之中,更貼近戰爭的描述或許是:從微小地方開始,感受到生活出現裂痕,日常的秩序好像再也無法回復,然後意識到,翻天覆地的破壞。個人的生命歷程被中斷,先於國家,先於時代。
《安妮日記》就是這樣的一本書,寫得誠實,所以殘忍。女孩安妮描述自己在戰時藏匿的感受,呈現出官方敘述中看不到的另一面,這在當前尤受重視,2015年《戰爭沒有女人的臉:169個被掩蓋的女性聲音》、2018年《倖存的女孩:我被俘虜、以及逃離伊斯蘭國的日子》等震驚世界之作,也都以「個人」視角出發,寫出一般人感受到戰爭真正的「破壞」。《安妮日記》於二戰期間寫成,被說是「改變世界的10本書」之一,讓我們看見個人臉容之於時代,如此真實。
「密室」的存在
《安妮日記》一開始並不為出版而作,它是戰時荷蘭猶太裔少女躲避納粹藏匿期間(1942-1944)所寫,出自安妮‧法蘭克之手。為了躲避被徵召到集中營的厄運,安妮在13-15歲期間與家人和其他猶太人躲在父親原本工作處的地下密室裡,寫下這本「與自己對話」的日記。
最初,戰爭對於這名少女來說,是不得不的告別,但你來不及說再見。集中營徵召令寄達的那天,安妮與家人離開原本的家,把愛貓留下,來不及也不被允許和正在約會的男孩說聲再見......製造逃亡的假象遷入密室後,他們從此生活在地下,自由在街上行走的記憶與安妮的童年一起遠離,就連開窗透氣也要注意時間、避開眼線,這是新的日常:
我想這棟屋子永遠不會給我家的感覺,倒也不是討厭這裡,住在這裡更像在某間奇怪的小旅店度假,這樣想有點怪,但藏匿的生活就是這麼一回事。密室很適合躲藏,雖然潮濕,地板傾斜,但在全阿姆斯特丹恐怕找不到更舒適的藏身處,不,在全荷蘭都找不到。(安妮‧法蘭克《安妮日記》,2013年皇冠出版,P33)
我們不管做什麼,都很害怕鄰居聽見或看到。我們第一天就立刻動手縫窗簾,其實那哪叫窗簾,只是碎布,什麼形狀、布料和花色都有,我和爸爸笨手笨腳,縫得歪七扭八,然後把這些藝術品用圖釘釘在窗戶上,等到不再躲藏才能拆下來。(P34)
逼仄的空間,侷促的視線,限制人的行動也打碎想像,安妮一家靠著父親公司裡幾個知情的好心人接濟,偷偷送來物資並在黑市中介交易食物,讓他們能簡單烹煮。由於公司仍正常運作,每天都有工人進出,他們過著「不能發出聲音」的日子,一點風吹草動都提心吊膽。「共享」密室的還有范普一家人、杜瑟爾醫生等,8個人努力重建生活秩序,安排可使用空間的範圍、時間、餘興和節日儀式等。
然而患難生活並不溫馨,安妮在日記裡誠實記錄她的心聲,原本互有好印象的幾家人自從被禁閉在狹小空間,生活的摩擦讓他們對彼此失去耐性。可是,戰時不存在「自我」的表達權力,他們被迫成為緊密牽連的共同體,隨著戰爭逼緊,人性自私也被逼了出來,比如范普一家總是藉機佔據食物資源,幾戶人動不動埋怨、吵架等,卻又無路可退、動彈不得,一邊怨懟一邊互相依賴,矛盾地一天天把日子過下去。
什麼時候能走出密室?走出密室之後,日子會怎樣繼續下去?這是安妮,也是藏匿者奢侈的自問。「密室」宛如整個時代的縮影,與隨時監控、搜捕、轟炸的外在壓力形成對應,不知道什麼時候有解放的可能。
戰爭如何轟炸我
在密室中,看不清外界,對於安妮而言,戰爭一直以生活微小的斷裂持續逼近,最終帶來翻天覆地的破壞。
旁觀他人苦難的罪惡感席捲而來,儘管那帶有一點不得不的冷漠。在納粹監控之下,人們出於自保或利益等去做加害者或旁觀者的紀錄不少見,而這本日記揭露出另一種面貌──受害者生存艱難,即便沒有互相分化,也被迫自私些,安妮描述自己得知其他人被帶走時的反應:
無論做什麼,我都忍不住想起那些走了的人。我意識到自己正在大笑時,就會想起這麼開心是可恥的。但,難道我就該整天哭嗎?這我又做不到。低迷的氣氛終究會過去。(P71)
我們沒什麼改變,想的事也一樣沒什麼變化,像旋轉木馬,從猶太人轉到食物,從食物轉到政治。說到猶太人,對了,我昨天從窗簾偷看時,看到兩名猶太人,覺得好像看到世界七大奇觀之一。我心中浮現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好像我向當局告發他們,此刻正在偷窺他們的不幸。(P77)
人們被迫連成共同體,窺見彼此私生活的暗面,卻又必須互相依存。而安妮有著敏感心靈,本就對周圍環境有強烈的感知,加上年紀最小,比起其他人顯得適應不良、神經兮兮,她的青春叛逆與戰時的「集體意識」格格不入──這種情境容不下太多「個人」聲音,地下密室又是不見光的存在,因而安妮的敏感天性引起群體焦慮,處處受批評,范普太太就說過安妮的不聽話會「害死我們所有人」。
從眾,是戰爭中最安全的做法,個人臉孔被抹平、犧牲是常見的,可是安妮是個正在成長中的少女,她的「社會化」因此變得艱難、無標準可依循,而成長不可能重來,這場戰爭的代價之於安妮,是錯失被理解、陪伴的機會,與母親關係的破裂亦是。等到戰爭結束,滿目瘡痍的城市可以重建,個人生命史缺失的部分卻不能重來。
或許是有意填補密室生活中言說自己的匱乏,這本日記以個人角度感受著一個時代的破壞,讓我想到《往事並不如煙》紀錄文革期間,羅儀鳳怕被清算,丟掉所有進口高跟鞋,又用熱水澆死滿園玫瑰的一幕。時代的暴力,有時看上去也不過是逼著一個人親手澆死她心愛的玫瑰,但那場面之可怕,讓你確切感受到暴力無所不在,不允許誰擁有多一點點的思想或空間,自由那麼微不足道,活著彷彿就只是呼吸本身。
愛與黑暗
黑暗籠罩之下,安妮卻展現出生命光亮的一面。
這本日記誠實寫下許多抱怨和批評,出自她對人事的判斷,自信地表達「安妮如何看待世界」本身。與納粹搜捕對照,她寫下冒死協助他們的好心人,溫暖的面容;安妮痛罵范普太太自私可笑,又以另一種抽離眼光看待這件事;她埋怨父母對自己的忽視,明知會傷害母親卻也不願說謊假裝愛她,與父親爭執時發出自省。這是一個在成長之中,尚未定型的眼光,她想著:那些,或許都是人類的脆弱面。戰火轟炸,安妮靜靜感受著城市仍在呼吸,外面有許多新鮮的生命,以及,自己蛻變中的身體。
隨著這段期間的相處,安妮與范普家的兒子彼得戀愛。她寫下對身體的好奇,愛欲烈火燃燒,恍惚猛爆,在那之中一種生命熱情被釋放,此時安妮個人的聲音、面貌重新立體了起來,對自己的身體,愛,和性的掌控欲望,讓她以女性的身分重新看待自身,相對於周圍大人的保守,她大膽地感覺這一切,意識到自己與戀人有能力互相理解,並快樂起來。這顆敏感心靈,於此脫離種種批評的聲音,重新看見了自身能量:在集體意識被放大的氛圍下,她的格格不入不過也只是被放大了而已。安妮頭腦清晰,或許有著善感而緊張的性格,因為記憶著痛苦,卻也比起旁人更強烈地感受到快樂與希望。
安妮期待著未來,她能準確說出自己作為一名青少年,相對於大人來說更不自信──因為大人已經長成了,他們摸索過世界的樣子,青少年卻不是,尤其在戰爭之中,他們比起大人更不清楚自己的未來會變得如何。但是,經歷了這些黑暗,安妮仍堅持愛,道出信念與希望,在密室小空間裡不是只有死亡,也有愛欲和生之喜悅,最後她說出在戰後想成為一名記者與作家的期待,用文字書寫個人的面貌,反抗時代的暴力。
結語
最終,密室遭到搜捕,成員被送往集中營。和平在幾年後到來了,只是安妮沒能活過這場戰爭。
《安妮日記》是在戰後由她的父親(法蘭克家唯一倖存者)為完成女兒遺願集結出版成,這位傷痛的父親沒有再去追查,到底是誰出賣了他們。那間密室在戰後仍被保存,閱讀這本日記時,感受到這名少女的真實情緒,不論愛恨欲望都那麼強烈,書末得知安妮的結局,於讀者是很震動的事情。
以個人經歷書寫戰爭的作品,近年來越被重視,比如2015年諾貝爾獎得主Алексиевич С. А.系列作《戰爭沒有女人的臉:169個被掩蓋的女性聲音》報導二戰時期女人們前一晚還穿著高跟鞋想像結婚,隔天即投身戰場,這些曾經的「女兵」存在卻在戰後的官方敘述中銷聲匿跡。2018年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Nadia Murad《倖存的女孩:我被俘虜、以及逃離伊斯蘭國的日子》以自傳揭露ISIS俘虜性奴、實行種族滅絕的暴行。幾本作品很巧合地都是女性執筆,我們得以看見更多「女性」在戰爭中的真實處境,填補了過去敘述的大段空白,也可以發現,當代很有回歸「個人」視角去還原、重現「真實」的意圖,意在打破過往描述戰爭史的宏大敘述──那經常是經過美化的版本,刻意營造戰爭英雄的存在去「挽救」國家形象,以國族想像帶過暴力的成分,但對劫後餘生的人而言,官方敘述經常與他們的記憶不一致。生命是沒有辦法「補償」的,國家的歷史,與個體生命史之間,又要怎樣去比較輕重呢?
有時候,接收到戰爭的資訊,是某年某月戰役中出現多少犧牲者,那樣的一行數字會讓人驚悚,卻沒辦法太深刻地共感。但一本日記,一部自傳,或許多微小身影的報導集結,讓我們看見一個活生生的面容與生存痕跡,在戰爭之下那樣輕易地被抹消,力道絲毫不減於幾千萬人的死亡,在那一刻人類才忽然意識到,個人生命之重,從不只是幾百億分之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