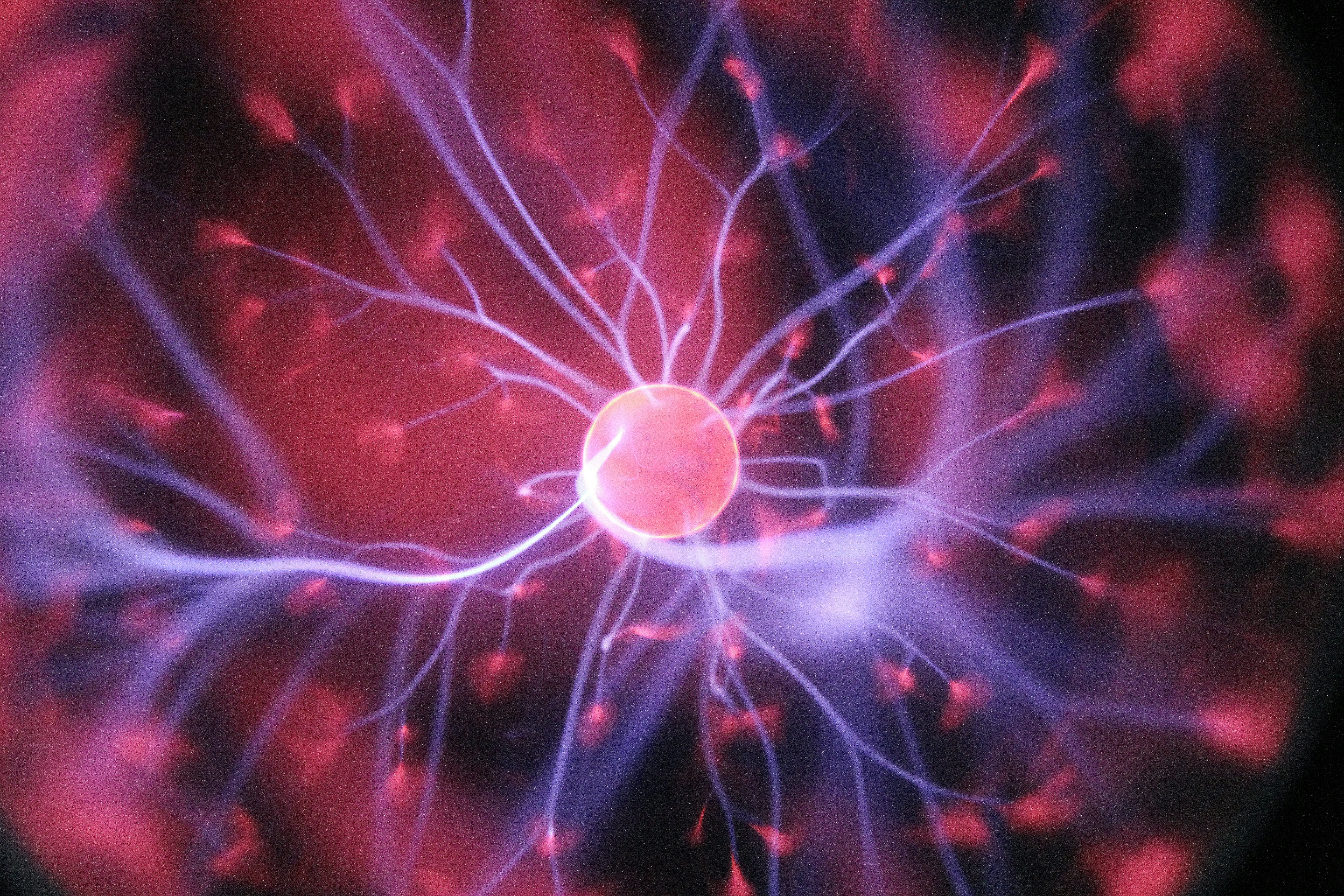你的就是我的,你的偷吃也可以是我的炮友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那天我偷用了一個曖昧一陣子的對象(應該算準男友了吧)的備用鑰匙潛進他房間(他之前自己告訴我的)想做晚餐給他一個驚喜,結果卻看到他隨意掛在椅子上面的內褲。
一條緊身寬字母褲頭的三角內褲。自然而然就拿起來聞,其實我是想確認這是新的或是穿過,但聞到上面他的體味還是自動勃起,我發誓我完全沒有往邪惡的那方面去想但還是起反應,他的味道真的讓我迷戀(所以才會跟他曖昧這麼久),忍不住就到沙發上邊聞他的味道想說打個手槍打完認真做菜。
我幾乎才剛把手握在我的陰莖還沒搓幾下,就聽到敲門聲。
敲門?慘了我到底有沒鎖門?不太確定我慌慌張張把褲子穿好時心想不對啊,怎麼會是敲門而不是開門?就在這麼想之際,門就被打開了,打開門的那個男人和我四目交接,我們兩個人都萬分驚訝,瞪看著對方,傻在當場。
「你是...?」
「你...是?」
我們兩個都同時問出這句話。我腦袋迴路瞬間過載百轉千迴後,好像意識到這是怎樣的狀況了。而他也是。收起驚訝,這個帶點斯文的眼鏡男孩露出的略為尷尬的神色,「那...Justin應該不在...」他不像是在問我,而是在確認他的認知是否無誤。
「他...嗯...」我不知該點頭或搖頭,我是本來不該出現在這的人。
「不好意思...打擾了...」
「等等...」我忽然覺得做人應該要厚道點,或者只是因為長相跟氣質的緣故,我邀請他進來。我根本也不是這公寓的主人到底是憑什麼我也不知道。
我們尬聊了幾句,我知道他注意到我褲襠極不自然的隆起,而我注意到他褲襠也是,大概本想到這邊做些什麼,而我剛好也正在做些什麼被打斷,我意識到這微妙的氣氛,心想不然就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做到底,把他撲倒在沙發上。
他愣愣盯著我時我的唇就貼了上去,軟軟的,嫩嫩的,觸感很好,對照褲襠硬邦邦的隆起則有極大反差。他身上不知為何有種牛奶的香味,讓我忍不住在他脖子上多吸了幾口,心想這曖昧對象平時吃得很好嘛。
到這裡,我幾乎已經認定這眼鏡男孩就是曖昧對象的某個炮友之類的。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他直接到這邊來,而且帶著他的勃起。所以我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曖昧對象的曖昧對象當成菜挾來配,你吃過的東西我也要吃吃看的意思,這樣誰都不吃虧。
我跟曖昧對象都是vers熱衷互幹,可能遇上彼此之前都是偏一居多,但兩人都想幹對方也想被對方幹這樣,而且幾乎像是儀式一樣,每次做都一定要插也被插才算完整。
我不知道這個眼鏡男孩角色是什麼,但就是適合撲倒的對象,適合撲倒,然後扒掉褲子不脫上衣的插入,他散發著那種氛圍。我猜他還是學生,性經驗不能說非常豐富(但也不是處男,至少不是只跟曖昧對象做過而已)。
當我插入的時候,我看他忍叫忍得很辛苦,就索性將曖昧對象的原味內褲塞他的嘴,這樣他就可以放肆由聲帶發出嗚嗚叫而不怕會被人聽見。(其實是我覺得這樣塞他內褲很性感,尤其那條內褲上的味道他可能也很熟悉)
我可能稍微有點報仇的意味而肏得有點大力。我吃味的不是曖昧對象背著我偷吃(還沒在一起其實嚴格說算也不算),而是他偷吃這麼優質的菜不跟我分享。我們幾乎分享了生活上的大小事,就像雙胞胎那樣,我幹他,他也幹我,我被幹,他也享受被我幹,所以我才覺得我們也許能夠交往也說不定,但他果然還是藏有秘密不跟我說,可能是怕因此被我佔有。
那我只好把他的炮友大力肏成變成我屌棒的形狀,讓他像記憶金屬一樣享受並記得我的撞擊,佔有他的炮友等於又與他分享了一件事情。
愈是大力操幹,眼鏡男孩就像奶油溶化成一灘牛奶,渾身散發更濃郁的乳香,被我幹得叫天不應的軟趴,只有本來勃起的那根粗屌還是硬得不斷泌汁,因為不斷被前列腺擠奶。
因為我覺得要是拿掉內褲他可能真的會嗷叫音量過大,所以中場休息我才肯拿下在耳邊問他一句「喜歡嘛」,他沒回我只是在我肩膀附近像是跑完馬拉松式的喘著大氣。
「所以他都怎麼幹你?」
我看不出眼鏡男孩的臉是在表達你是在問什麼蠢問題,或者這種問題怎麼可能答的出來,又或者他只是被我幹到腦袋無法正常運轉,空虛的屁眼期待我繼續把他的精華榨乾到一滴不剩為止,所以我只好如他所願,用手摀住他那嫩嫩的嘴唇,繼續讓他體驗爽上加爽,把曖昧對象的也加倍奉還給他。
我們真的是名符其實的水乳交融。我的汗水跟他的乳香融合到了一起,到最後已經分不出是誰的汗臭或誰的乳香,我喜歡跟對方做愛的時候做到這樣淋漓盡致的地步,榨乾對方也絞盡自己,直到極限才肯罷休。
因為沒有被幹,前列腺感覺空蕩蕩的,少了什麼頂在那裡,感覺就像是沒有列車通過的站,沒有和尚撞的鐘一樣,讓我不用刻意也自動延遲了好久時間都無法射精。
我想像著平時曖昧對象那樣把他那根很容易頂到點的,紋理分明的巨大按摩棒正在後面抽插著我的屁眼前列腺,那就像是扳機或是我身體的開關,唯有這樣想像著我才能慢慢進入高潮的的階段,明明幹著眼前這眼鏡男孩已經讓我這麼爽了還是不夠。
最後拔出來射了他滿臉滿嘴,他吸著我搏動著屌的臉更加性感。我看著被射得一塌糊塗的他,我卻好像沒有因此而得到滿足。
我問他要不要射出來他沒有回答。我無言幫他擦拭他的身體,我們之間的氛圍有點像他被強姦過後的尷尬。
誰知道就在這時候,曖昧對象回來了,他開門進來,傻眼地看著我倆(已經整裝的差不多)。
「WTF?」曖昧對象看著我的嘴型是這樣,他只是沒有發出聲音。
「...學長,那個...」眼鏡男孩慌張的站起身,「書...我,我是來拿書的....」
「啊,我忘了,啊抱歉,書現在不在這。」
「那,那我先回去了,你下次再拿給我吧!」眼鏡男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閃離這公寓。
曖昧對象盯著我看就像是警察逮住嫌疑犯,被他這樣盯著我是有點怯懦,而且旁邊放著那條內褲上面還沾有我劇烈氣味的體液更顯突兀。
這回換他撲倒在我身上。
「説!你怎麼在這?!」
「我...來做晚飯給你吃啊。」
「那晚飯呢?」他壞壞的一瞥。
「還沒做...」
「都做完了吧!哼?」他在我身上左聞右嗅像隻警犬在查緝毒品。「洨味好濃喔掯...」
「哪、哪有!」
「那這是什麼?」他拎起那條濕黏黏的內褲,「阿痾這上面都是些什麼?我不記得我今天早上有夢遺啊?」
「......下次打槍的內褲要收好。」
「這明明是你的洨味!」他把那散發濃烈氣味的布料湊近我的鼻尖。味道濃郁是否代表我身體健康?
「....你對學弟做了什麼?」
「什麼學弟...那不是你炮友嘛?」我索性也不演了,直接攤牌對質。
「什麼炮友啊...?那我學弟好嗎...」
他的眼神有點飄移我都看得出來。我默不做聲擺態等他心虛。
「好啦好啦。是有想吃但我發誓我真的還沒有做任何事,倒是你剛『幹』了什麼好事啊?」
「App上認識的學弟叫洨弟,吸搖洨,二聲洨。」
「我只是還沒跟你分享而已嘛。然後你就吃掉了。」
「...今天要是你在家你不會吃?」
他搖搖頭。
「賣gay。」
「如果他不小心彎腰,我又不小心下體撞到他...」
「就像撿肥皂那樣...」
「嗯,譬如説他彎腰撿考古題剛好屁股撞到我雞雞之類的。」
「臭雞雞。」
「你還敢說我。」
「我們臭味相投。」
我這才發現我又硬了,奇妙的褲襠頂著微妙的位置。然後我們接吻,我又變得更硬了。
「你GG又ininder。你好色。」
我無語,因為連我自己也覺得我自己真的好色。才剛大尬完眼鏡男孩轉眼之間卻又變得硬梆梆。簡直棒槌嘛。
「可是我就喜歡你好色。」
而且剛剛尬人那陣從前列腺深處的空虛,漸漸從括約肌屁眼蔓延出來,我的屁眼確實的在期待某種東西,某種曖昧對象身上才給得了的魯莽巨物。
我們深深的吻,用舌頭互相交換唾液,他口中的薄荷味弄得我滿嘴都是,我們濕吻到甚至連嘴唇都濡濕了。
「下次把學弟約來,我想幹你一邊幹他,也想幹他的時候一邊被你幹。」他在我耳邊低語同樣也是我想說的話,然後把舌頭鑽進我的耳朵裡,像條貪婪的小蛇。我把手伸進他的褲襠去撫摸下面那隻同樣貪婪的大蛇,在黑色草叢中已然甦醒。
★地方Justin需要您抖內汁持→ 打賞文字這邊請
方格子圖文→ 點此,並歡淫付費訂閱男性愉悅跟上新作
Twitter→ 男性愉悅
為什麼會看到廣告
6.2K會員
722內容數
這棟大樓似乎有著各形各色、各種不同的「房間」?身為Justininder,你忽然興起那種想要一一探索的好奇。喂⋯⋯不會吧,這、這未免也太刺激⋯⋯微微的不安油然而生,卻又無法遏止,那潛藏在心底的原始渴望。你,並不寂寞,我們一定是共享了什麼,才會在這裡出沒。雖然還有點害羞,但既然夜幕早已落下,就一起來玩吧!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