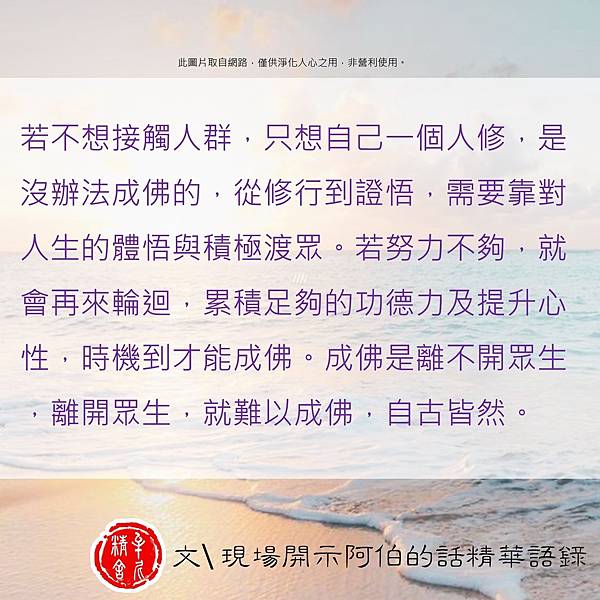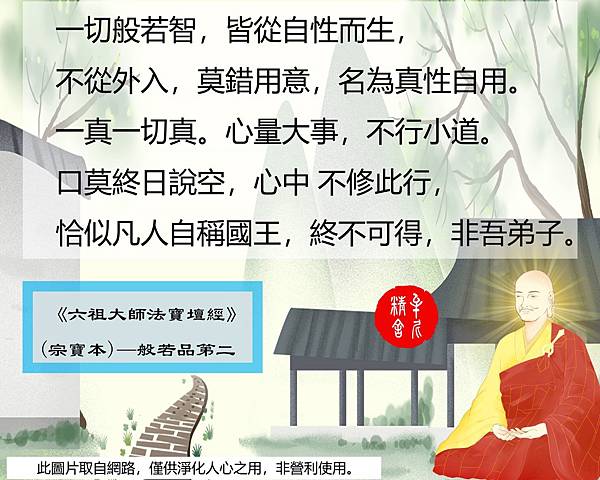我什麼時候想過放棄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我每天都想著要放棄。放棄創作;放棄吃東西的慾望;放棄每天喝兩千CC的水;放棄追求人際關係的穩定與家庭的溫暖;放棄打開房門出去曬曬太陽感受世界的暖意;放棄去尋找許久未見的麵包店的老朋友;放棄像大學時那樣,一個衝動就跑去搭公車上陽明山爬山路;放棄求生;放棄思考;放棄理解自己的內心深處存在多少個「自我」。
我的人生每天一天都在放棄,因為我的人生每一天都被否定。當然,有一半的否定是自就學時期受「外力」給予的;另一半則在我二十歲成年後,我架空了「外力」、想像它依舊持續對我遞送著「否定」。
要一個每天都在尋求放棄的人,換張臉鼓勵人什麼的,沒什麼說服力。偏偏我是那種忍著情緒去鼓勵別人的人。
二十年前的某一天,我大概六歲。我跟家人去了某位親戚家作客一個下午。在他們家,大人都在聊天,小孩無所事事,除了得忍著耐心等候「二、三小時的長聊」而且不得有怨言,說得好像小孩能夠忍受一樣,怎麼當初不買個機器就好?還好,當時的我天性白目,於是忍了沒多久就發出抱怨,要他們好歹給我幾張圖畫紙讓我畫圖吧?
很順利,我得到了幾張撕下來的日曆紙,拿著鉛筆、用背面的空白開始畫圖。
我很喜歡世紀帝國這款遊戲。每天回到家打開電腦,我都一定要玩到世紀帝國。世紀帝國的迷人之處,就在於那以中古世紀為背景的遊戲設計,讓我從此對西方歷史著迷不已;也因此,當時畫圖時我就想著要畫一幅牆上滿是不列顛長弓兵射箭、防禦外敵來襲的戰爭場景;我首先畫了一面牆,牆上有旗幟、有窗戶、有城門,城垣前站滿了拿弓的士兵;他們在射箭,射向底下穿著盔甲的敵軍,死的死,逃的逃,衝鋒的繼續衝鋒,我很滿意。
雀躍的我,把這張圖拿給爸爸看,然後想著等等要把它畫得更盛大、更凌亂。結果爸爸說:「你城牆都畫歪了,畫錯了。」回到桌子前,我不畫了。不想畫。我就讓畫紙待在桌子上,不去碰,直到離開親戚家為止,都不想帶走它。
我滿意的畫作,在被評價之後我就把它當成垃圾看待。
我的城牆真的畫歪了嗎?對。
這幅畫真的是垃圾嗎?不對。
以小孩子的繪圖能力,畫得簡陋、畫得潦草,其實都合情合理。沒有小孩子生下來天身就會畫圖的,何況還要畫得像是某些繪圖網站上的大神們一樣畫得好──畫得如何,需要的是練習,沒錯;想要畫得更好,需要的是懂得自省與被檢討的心態,對;但,對於小孩子脾氣的我來說,那時候我的解讀很單一、很純粹。爸爸說「不好」,那它就是「不好」。我應該要拋棄「不好」;在我的解讀裡它是一個指令,不是期望。沒人告訴我在認識到自己的不好之後該怎麼解決這個不好,沒人告訴我希望我接下來該怎麼做。我不懂得應對,不懂得調適,所以我自暴自棄,把這幅圖給放棄了,隨意放置,有關它的記憶,一直到很久以後的未來才被回想起來,也就是現在,然後我早就不畫圖了。
不過,真正決定我不繼續畫圖的理由,其實跟這段童年沒什麼關係。主要還是在升上國中之後,就學壓力變大了,每天的日程只有讀書跟讀書,玩電腦成了最好的發洩。我也在這個階段完全忘了畫圖的愉快,畢竟學校告訴了我「考試是為了升學」,它有個目標。我畫圖沒有追求的目標,也就沒想過要投入更多心力去練習它。循序漸進下,我的思考邏輯受到大人教育的約束變得偏窄。「沒意義的事情就盡快放棄」是他們在教育過程裡不斷傳達給我的訊息。我吃下了,吸收了,也造就現在破損不堪的我。
所以一直到大學畢業後,我的「前方」依舊存在著一種幻覺。這個幻覺總是在警醒我,要讀書,要考試,有升學壓力,有必須完成的義務。
明明都出社會了,讀什麼書?考什麼試?別鬧了。
偏偏,它就是存在著。每天趁我無防備之際跑來打擾我,讓我的身心陷入緊繃,腦袋意志無故追尋起幻覺製造的虛假目標,然後鼓催身體快點為它做點什麼,否則我會被淘汰。
此外,它還不斷叫我放棄這個,放棄那個。
這些都是過去了。即便時至今日,我偶爾還是深受其苦,但我已能自行調解各種沒來由的緊張感與使命感,然後告訴自己「它們是假的,不要理會」。你當下想完成的、現在想要做的、你喜愛的,那麼就去完成它、實現它,已經沒有人阻礙你了。
我每天都想著要放棄。但也每天都想著不要放棄。
嗨!我是Moonrogu!希望你喜歡我的文字與觀點。如果你希望讀到更多我的作品、隨時與我互動,歡迎加入以下連結追蹤我:
《奇幻寫作事:想像世界的創作旅程》
299元,單次購買、永久閱讀!
《奇幻寫作事:想像世界的創作旅程》囊括了我自身對奇幻的理解與觀點,以及作為奇幻小說家對寫作的看法。如果你也是對奇幻感到好奇、有興趣的朋友,歡迎訂閱購買《奇幻寫作事:想像世界的創作旅程》,一起與我探討奇幻的有趣之處吧!
拍手五下,輕鬆支持我繼續創作
↓↓↓↓
為什麼會看到廣告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