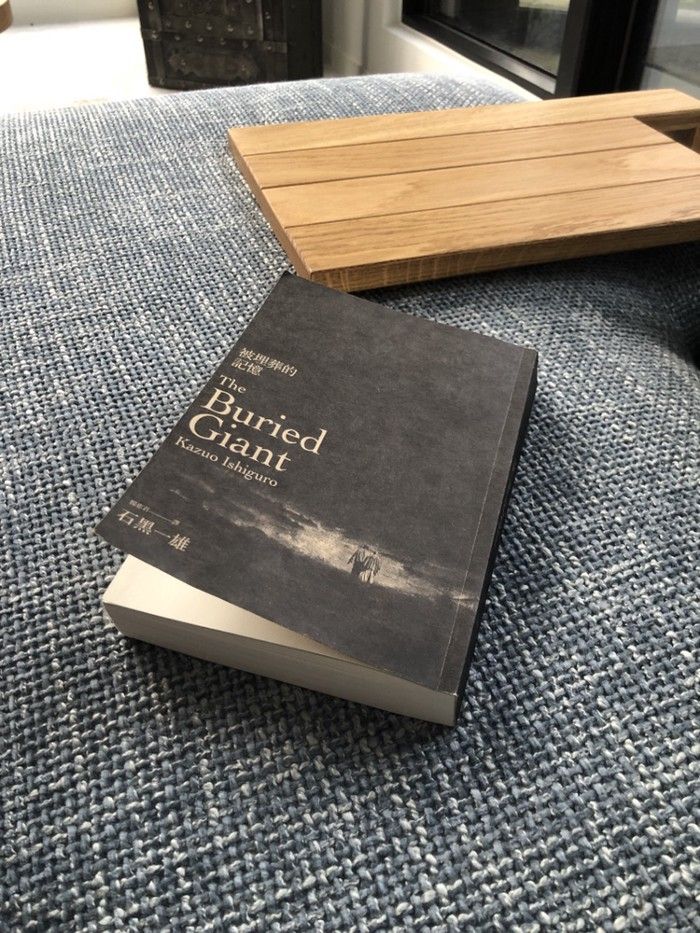方格精選
今晚,你想讓誰「被消失」?遊戲《Beholder》對體制的質疑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遊戲《Beholder》刻劃極權統治下的生存,玩家扮演秩序部派駐的公寓看守者,負責監視人民,「合法」的偷窺不僅無罪,還能定別人罪。同樣地,抓別人挾帶違禁品的同時,你可以悄悄將它們據為己有。
格局方正的公寓中,住客來來去去,夜裡,有雙冷眼監看眾人的一舉一動;在政府高度監管之下,只需要一點小理由,就可以讓一個人「被消失」──沒有人知道他們去了哪裡,反正對國家而言,他們是不該存在的人。反烏托邦遊戲《Beholder》的小公寓,是共產主義下荒謬社會縮影。
玩家是永遠的「清醒者」,不眠不休為政府(慣老闆)工作,隨時要接聽秩序部電話,依法辦事,與人交談、安裝監視器、潛入房間調查,最後,鑽進不見光的密室,為住客建檔,上呈犯罪紀錄......這款遊戲,你必須聚精會神,記法令編號,敏感地辨認每一個房客特徵,嗅出誰是危險分子。儘管,共產主義下每個住客都沒有臉孔,黑壓壓的。
偷窺住戶畫面
故事:從這個房間到那個房間
遊戲敘事帶動節奏,同樣是極權政府監控人民的背景,《This war of mine》明確以「一天」為單位,固定時間製造斷點,黑屏做出小小切換,像呼吸的節奏,玩家累積行動,情緒節制,到結局總回顧才像柯南腦中閃過真相那樣,咻一下把每一個點狀敘事串起來;《Beholder》雖然也以「一天」為單位,但公寓管理員不用睡覺,早晚有不同事情可以忙,幾乎感覺不到切換,又要在期限內完成各種突發任務,不給喘息空檔。因此,雖然也採點狀敘事,刻意切割,高壓氣氛卻不中斷。
《Beholder》的敘事角度,更接近「空間」串連。每個房間都是獨立劇情,在同一天裡,玩家可以到處行動對話,同時參與、推動不同房間的劇情。用空間做分鏡,打破原本的時間限制,事件雖然零碎發生,串連性仍很強。
白天緊繃蒐證,夜裡把握分秒建檔、舉報犯罪,一按下送出鍵,就有秘密警察上門,拳打腳踢地「帶走」房客,毫無預警的劇情選項還會突然跳出來,一不小心便會game over,因此玩家會明顯感受到每次行動的直接力道,一有動作就會「立刻」造成影響,這種充滿儀式性的緊張,也象徵一種權力快感。
節奏調控是《Beholder》精緻的部分。點狀敘事下,每天緊迫盯人,節奏不變容易疲乏,因此遊戲初期節奏相對緩慢,讓玩家適應收信、接電話、偷竊、敲詐、舉報等規則,在加害住戶的操作中稍微獲取小成就之後,馬上爆發一場人民抗議!扮演政府公務員的我們焦頭爛額,一邊面對上級施壓,一邊解決住戶疑難雜症,一邊面對家庭問題,包含女兒重病、兒子不願聽從政府安排去做礦工成為叛亂分子。同時,玩家得要飛奔接電話,和時間賽跑完成部長的命令,還要賺錢支付兒女需求,對房客監控又不能鬆懈......這款遊戲很殘暴,節奏的轉換是「加快」,讓玩家隨時感受即將爆炸的風險。
如果想讓兒子繼續讀大學,得湊一大筆錢
玩過遊戲的人,大概可以理解那種肩頸痠痛,還捨不得離開監視器的感覺,貼近人對權力的態度,恐怖卻又迷戀。
和權力同一陣線,可以做些什麼
《This war of mine》將個人從社會網絡之中抽離出來,營造一種失根、無助的感覺;《Beholder》扮演的角色,有一個明確的身分歸屬,甚至背後有整個政府系統在撐腰,是不是能擁有比較多選擇?
玩家在《This war of mine》面臨的,是良心與生存之間的艱難,不存在所謂的命令和負責對象,點選任何行動,好像都可以,又好像都很危險,玩家的遲疑回應到的是自己在現實世界的道德律──這款遊戲明明有明確的事件對應(賽拉耶佛圍城),體驗時卻不強調「背景」,沒有刻意把玩家拋入哪邊陣營,我們對角色沒有那麼強的「帶入感」,行動時就會按照自己本身的意願。
玩家在《Beholder》面臨抉擇時,也會回應到現實價值而騷動,但當你習慣部長電話說來就來(快來人把電話線剪斷!),卻沒有「提出質疑」或「不做」的選項──可以虛應故事,或不按照指令方式完成,但「結果」就是那樣才能交差。
監控房客過程中,甚至讓我們生出一種「大家長式」的矛盾情結:投入關心、維護管理和糾舉懲罰的三重行動同步切換,我們既好奇每個房客身後的故事,又隨時切換成冷面制裁者,依法舉報這些熟悉面孔。這座老舊公寓,象徵密不透風的體系,玩家自己也被嚴嚴實實包裹其中,受到更高層的政府單位監管,監視者/被監視者立場相對,卻連通成詭異的「命運共同體」。
收集住戶信息
監管就是偷窺,玩家一直守候在暗處當抓耙子,一邊暗笑這些違禁品毫無邏輯(蘋果?牛仔褲?),一邊不假思索地執行。看見房客出現反政府、做炸藥等破壞行為時,有種痛快,隨後又因為自己是有權力懲治這些破壞者的角色,產生一種高高在上的快感。遊戲的「兩難」大多回扣這個概念──如果住戶的違規,只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偷吃蘋果),要舉報嗎?操作時玩家自動套入「國家機器」的一環,檢舉一顆蘋果,和一把手槍,SOP完全一樣,都只是把法令填入表單空格,這種「科層體制」的設計,執行起來不痛不癢(把房客帶走是「警察」做的,不是我哦),加上禁令本身太蠢,從一開始就無法說服自己這是「正義之舉」,考量當然就轉往利益導向,遊戲的敲詐鍵,顯然也意圖建立這種暗示。
發現有人想推翻政府,或向你尋求協助時,擔心被捕的恐懼感,伴隨著怠職的焦慮,形成一種自我審查。玩家盡責地做紀錄,隨時準備接聽電話,任務完成在所當然,稍有差池便是一頓臭罵或game over(別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問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擁有權力的代價,是無止盡的「責任」,而我們自然地把所有活動都劃入了職責的藉口。
體制內尋找逃脫路線?
遊戲最後,人民起義,在這之前玩家必須鋪路拯救自己跟家人,否則,就會與政府一起被推翻,走向死亡或終生監禁。
《Beholder》沒有給出「不作惡」的選項,過程無論如何都會加害其他房客。面對人身安全威脅,目睹家人苦難,上下不討好、腹背受敵的困窘讓賺錢成為第一要務──沒錢,兒女會在面前死亡;想逃走,移民國外也需要大把鈔票,玩家把清除其他房客視為「必要之惡」。或許因為這樣必須付出代價,「完美通關」條件尤其艱難──眾多結局中,只有一種是和家人帶著錢平安出國,「假裝忘記」這段記憶,其餘都很淒慘,比如勉強逃出國可能身無分文、遊民一樣地過活;就算政府沒被推翻,你成為被國家獎賞的「忠誠者」,也可能被抓去做人體實驗,死在手術台上。不論哪種結局,「孤獨」是最可能的處境,呼應在國家監控之下,人與人的疏離。
在體制的邏輯裡,「道德」界線是曖昧的,隨時有模糊地帶:我們可以不舉報一個好人,但小小敲他一筆,或協助反政府組織偷偷殺掉某人,同時完成上級指令,做一個雙面間諜──既然腹背受敵,自己開創出一條兩面討好的路有何不可?上級檢核玩家是否怠職的標準,也不是「沒有住戶犯罪」,而是公寓中的犯罪率是否在「可接受範圍」內。(啊那個範圍的標準是?)
角色設定,一開始就不是「理想」派,即便跳出來反抗政府,出發點可能也不是站在人民那邊。畢竟,我們是介於二者之間的「夾層」,被指派當守門員,要守住的那扇門,除了政府,再來就是自己心中防線了──與體制離得近,很多作為都不假思索。既然道德模稜兩可,最後底線到底在哪裡呢?這名公寓管理員,只是一個普通小人物(害過那麼多房客,也稱不上大奸大惡),但不管是為了活下去、貪財或其他原因,一個接著一個平庸小惡,最後加總起來,造成多少家破人亡?我們所做的,不過是敲敲鍵盤。
我們所在的位置,是公寓的秘密地下,沒有門
當然,整個遊戲的監看、毫無公平可言,你知我知還要維繫表面正義,突出特定時空下極權統治的荒謬,而「體制」造成的麻木疏離,是極權運作的根基,也是更大的背景──透過給予少部分特權知法犯法的游移地帶,將之收編成為體制的一環,把所有房客和管理者同步綁在一個恐怖平衡(炸彈)之中。體制的目標,就是維持體制本身,在其中能盡到最大的善良,多數時候只是旁觀,光要保持清醒都很困難。
別忘了這座公寓的視覺設計:我們所在的位置,是比所有房客更低的地底下。體制複雜,卻又很簡單,把全副身家性命栓在內部的人,其實更加渺小,卑微卻又堅定地,把自己慢慢活成體制的一部分,國家機器下,一顆小小的齒輪。
整座公寓就是一個牢籠,微型社會;埋設地下密室的看守者,其實離出口最遠。
為什麼會看到廣告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