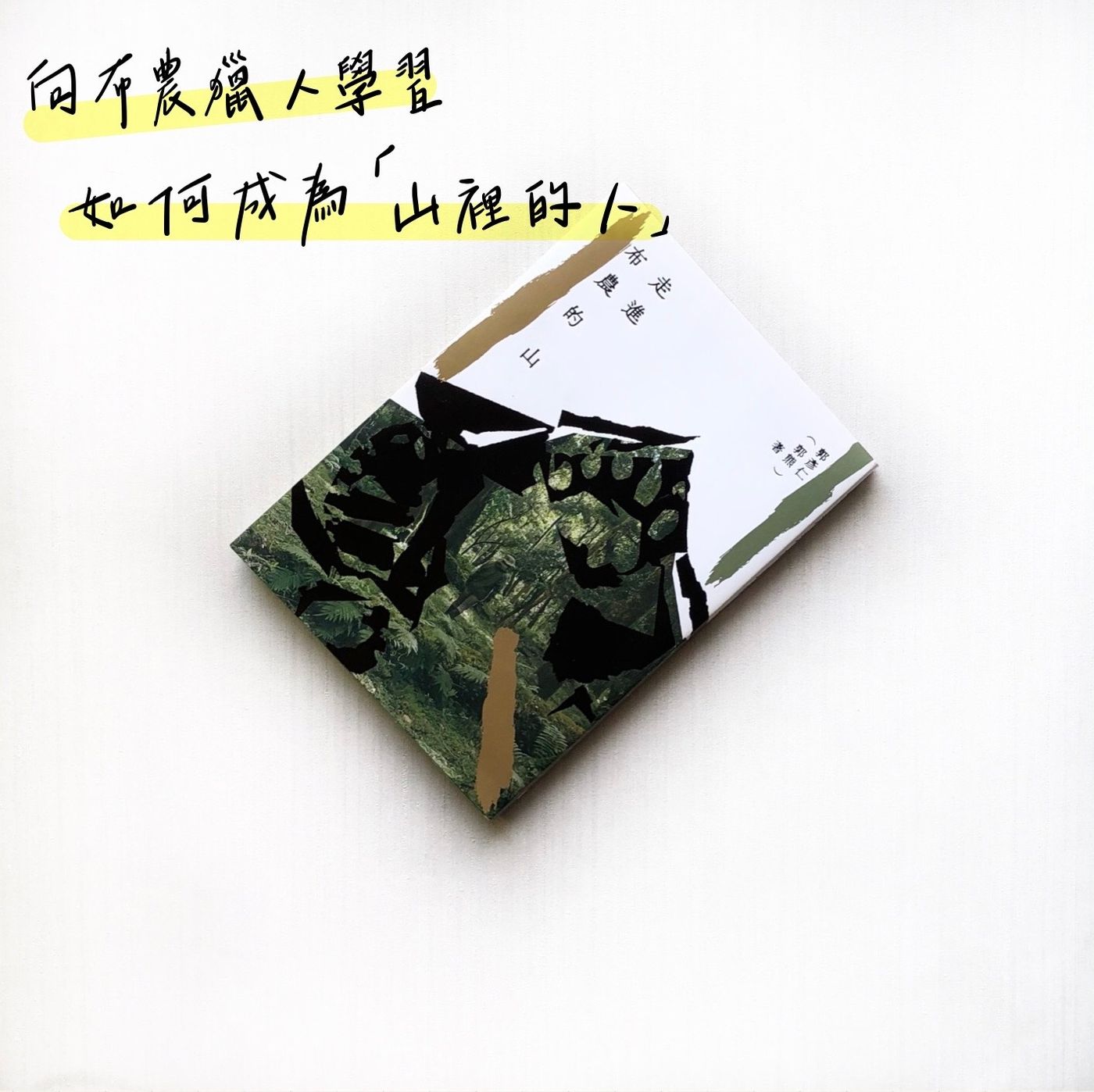《野蠻人入侵》|多重敘境裡如何拼貼自我?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千禧年初,馬來西亞電影圈掀起了一股以獨立影人主導、擅於游擊拍攝的電影新浪潮,其中,大荒電影的創辦人陳翠梅作為掀浪者之一,為馬來西亞電影提攜新導演、電影工作者,更在對族群、階級等議題相當保守的馬來西亞影壇中,嘗試切入、梳理,開創別於既有敘事的影像敘事。
《野蠻人入侵》作為陳翠梅自導自演的最新劇情長片,集香港及馬來西亞製作資源,以私電影的範式講述電影創作者何以在母職與演員身份間平衡,更嵌入影像後設情節,旁徵了如《神鬼認證》、《駭客任務》橋段,對白間更打趣地談論洪常秀,此外亦嫁接香港武俠電影既有的身體訓練過程,從中置換為菲律賓武術(kali)和以色列近身格鬥術(Krav Maga)的修行。
開場援引宮本武藏「一切皆是電影/劍」,實屬電影人的浪漫嚮往,《野蠻人入侵》即是透由虛實之間的切換實踐這層想像,創作者/演員的「自我」如何在多重敘境裡成為可能,便是電影的意旨。
《野蠻人入侵》的開場即是本片導演陳翠梅作為女演員的特寫鏡頭,無奈的表情隨鏡頭拉遠,才曉得那是在工作及育兒拉扯下女性電影工作者的困境,畫框裡只呈現的「自己」實然被圍囿於生活裡,而電影該當如何輻射出對他種生活和身份的可能,便是藉全片前後影像技巧顯著斷裂所嘗試理清。
片名中的「野蠻人」起初指涉的是從開場就完全不受控的兒子宇宙,無論是李圓滿的習武、日常行程,總不斷地被干擾、被介入,私人經驗裡的演員身份被迫退讓給母職即成為全片講述「自我」失衡的起點。而前段處理的對白中,亦由口語解釋意識地提起困境,無論是李圓滿對著導演的新助理傾吐,安排女性後輩同理,或是直白地以無可奈何、不斷遷就示人,處處彰顯現行下的難解。因此,在中段強行去除「兒子」元素後,李圓滿便被置換成重新登入/侵入原先的身體,一如演員之於角色的入侵。陳翠梅/李圓滿的修行於此不只是武術上的,更是習影式地訴諸電影以梳理自我。
而此處也是全片影像風格猶如鍛鍊至精熟的分野,前段仿武俠電影中必經的身體訓練,就鑄成另一層身份而言有其鋪陳與轉化功能,然室內武打戲多以定鏡中景拍攝,毫無疑問地營造乏味與抽離,而突如其來的觀點鏡頭質問李圓滿「自我」多少又太過直接地拋出私電影的題旨。武術作為女演員克服內外阻礙進而去尋求自我的手法,承接後半段動作片的轉向,意圖明顯,卻未能就著低成本的限制開創出新的影像語彙,而顯得此處的過招與調度僅是無新意的影史重複。
直到電影後半,演員的身份轉化、進入不同層次敘境裡,亦賦予了「野蠻人」更多種的詮釋。種族議題在此也順勢被輕輕挑起——就潛藏在當李圓滿刷新身份重新上岸,混入一群華裔非法移民之時,以新身份再次進入敘境時的類型張力。
當今華人身份仍難以見容於馬來西亞政治,大馬憲法仍存以種族為界的階級劃分,《野蠻人入侵》刻意讓聞名於東南亞的華裔演員置換身份,成為底層華裔從法治外登入大馬社會,緊接透由如程序性記憶的語言和武術能力抵禦一連串來自外在環境的拒斥,以一身空白記憶擾入族群界線。綜觀馬來西亞華人於今日的處境,實然也早在電影前段,男性導演談及電影資金困難時有所涉及:在當地製作資源稀缺(或集中於特定群體),須仰仗外來(中國)資金支持(華裔)電影,更甚是需要由中國演員介入,並與馬來男演員共演,而居間的李圓滿只能隱忍妥協,就如同開場以來以馬來語不斷向兒子遷就。在某種程度上,《野蠻人入侵》便是將個人從性別角色、族群去疆界化的土腔電影(註1),同時也是去除影像虛實邊界的電影。故此,李圓滿於第二段重登的身份即是表徵著馬來西亞土生華人如何在中國國族主體和馬來西亞國族主體建構的雙重排除之外從中雜揉,產生自我的敘事。全片塑成「自我」藉多元素交融,好比一下是粵語語境的香港武俠致意,一會兒又是禪宗啟發,或是對好萊塢商業類型的延攬,足以從個體身上窺見馬來華人身份的複雜交織,縱使其影像語彙未能跟上概念而顯得拼裝。
《野蠻人入侵》最終在多重敘境中,走成了拖沓的敘事步伐,陳翠梅/李圓滿的武術再如何有看頭,再如何企圖擴張身份之間的邊界,都難免感到生硬,「自我」該走向何方或許最終只有影人感到滿足,畢竟最後一顆鏡頭是突兀地留給了故事中的導演,李圓滿追逐全片的自我則顯得被輕放。
註1:「土腔電影」一詞引自許維賢《華語電影在後馬來西亞:土腔風格、華夷風與作者論》回顧哈密.納菲希:「土腔電影跨越各種邊界,進行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的旅程,它最重要是體現主角在追尋身份認同的過程中,如何操演其身份認同,其中包括尋找家園的歷程、無家可歸的旅程以及回家的旅程。土腔電影是在家國和留居地之間跟兩地的國族電影和其觀眾群間的對話。」
為什麼會看到廣告
24會員
32內容數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