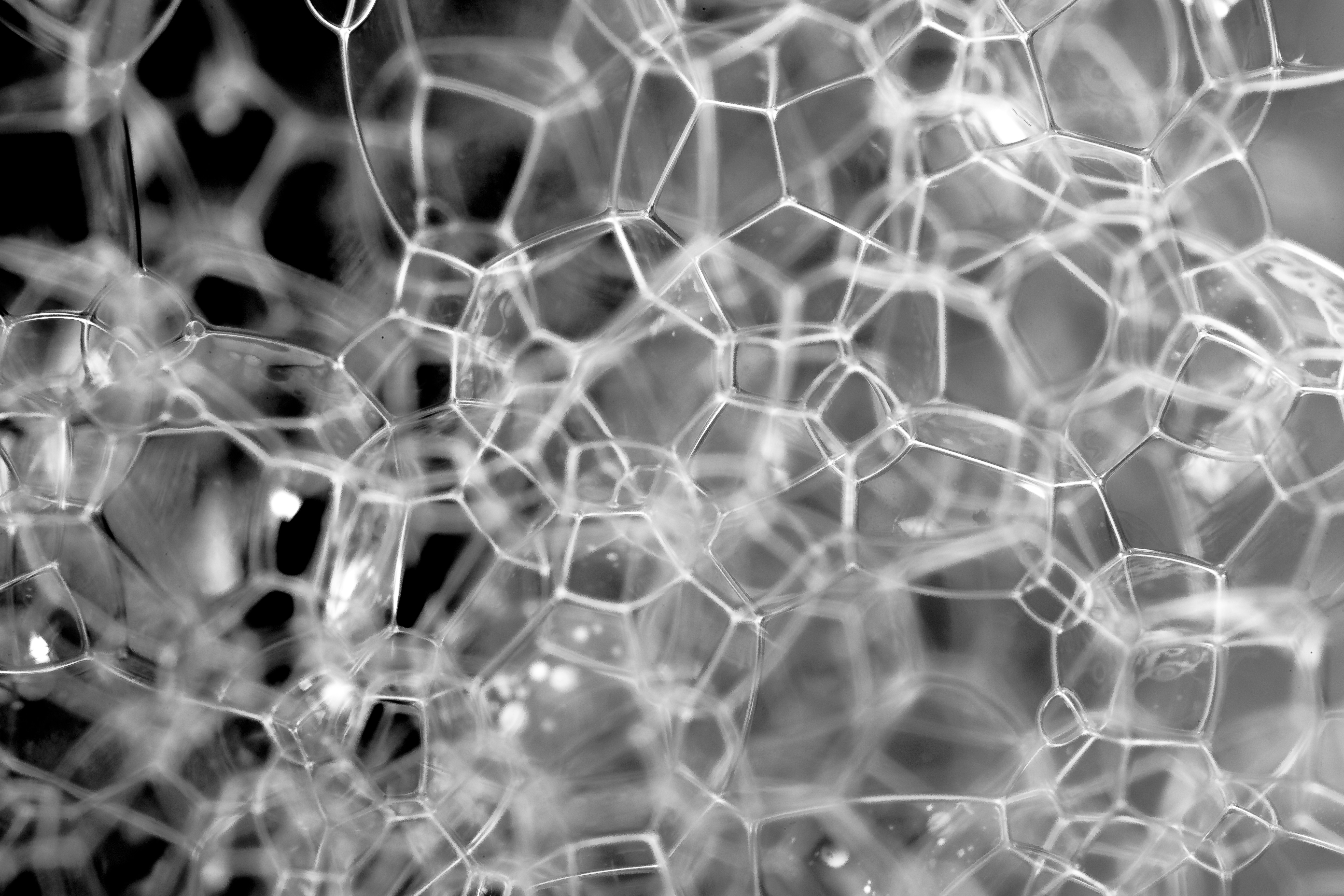(HIV相關)直到2024:HIV的污名化標籤仍以不同的事件在持續蔓延
新的一年的開頭,很遺憾的臺灣社會上還是正在發生對於HIV歧視與污名化的新聞事件存在,在同婚通過將近3年的現今,整體臺灣社會也許相較過往有更多多元族群的討論聲音,但另一個不分性傾向的HIV議題,卻還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新聞事件,給與其獵巫般的報導再加上負面標籤,將HIV建構成魔鬼,讓人聞之色變,彷彿HIV感染者即使是在U=U的情況下,也不應該有性行為,甚至將HIV的感染途徑只建構在性身上,而忽略其他感染者的個人經驗與聲音。
過去以來,台灣因為不去檢討「為什麼」,不去檢視歧視如何造成,歧視的源頭是什麼,所以即使那麼多人呼籲不要歧視,指出歧視不該存在,卻彷彿依然停留在三十年前的水準,只想倚靠政治正確的口號對減少恐懼、消除歧視毫無實質幫助。(喀飛,2021)
外國實況主事件
會用「直至2024,HIV仍舊被污名化」的標題,主要的新聞事件就是因為有一名外國實況主,因為之前有和感染HIV的女性發生性行為,並公開分享在直播影片上,近期來到台灣實踐性行為,而被網友、Youtuber與新聞爭相警告與報導。首先,讓我們先看一下,各家新聞媒體使用了什麼樣的標題來描述該起事件:

圖一、來自研究者自行截圖
首先,「疑染」很明顯出現在各大新聞標題,也就是說在報導新聞事件之前,根本不確定有沒有HIV,先撇開白人這些身分上的討論,只因為曾經跟HIV的感染者發生性行為而被描寫成「只要跟HIV感染者發生性行為,就會有HIV感染的風險」,但報導中根本沒有提到感染HIV女性的狀況,反而粗暴的直接將性、HIV、無套連結在一起。完全沒有顧及到其他HIV感染者的感受,甚至一再建構污名化的刻板印象,試問,這對於那些潛在的感染族群來說,又怎敢向社會公開自身的身分與尋求救助管道?
國際共識「U=U」(undetectable=untransmittable,測不到病毒=不具傳染力)目前共獲得1,099個國際組織認同,聯合國愛滋病聯合規劃署(UNAIDS)也於2018年7月便已正式公告「U=U國際愛滋治療共識」,其中指出,只要HIV感染者穩定接受治療且持續抑制病毒,即便有未經隔絕的直接接觸性行為,亦不可能發生傳染。(疾管署,2018;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2023)
HIV跟愛滋病的定義不同,感染途徑也不是只有性
HIV 指的是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會透過體液在人跟人之間傳染,攻擊人類免疫系統,使其無法正常運作。而愛滋病,指的是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是感染 HIV 的人在體內的CD4 細胞(一種免疫細胞)的數量,降到 200 左右時(正常人的數量是 800~1200),感染者的免疫系統已微弱至無法對抗各種伺機性感染,才會稱為是愛滋病。但不論是社群平台討論的聲音或是影音平台下方的討論,都還是看到許多人會將兩者混為一談,而沒有辦法好好針對其細部內容進行理性討論,而是用恐懼、貶義甚至人身攻擊的方式來作為自身接收訊息的回應方式。
另外,HIV的感染途徑除了不安全性行為之外,還有靜脈注射、輸血、分娩、哺乳等方式,然而檯面上的新聞事件報導,只強調HIV與性的連結,彷彿沒有其他途徑的感染者存在,而對於這些感染者的社會處境上只會更加困難(一旦曝光身分大家就會用「性」途徑的方式去看待你),根本無益於改善感染者的狀況。

圖二、截圖自Youtuber的標題
雖然Youtuber作為公眾人物提醒他人要小心惡意固然是件好事,但更加嚴重的恐怕是台灣民眾在沒有對HIV有一定程度了解下,而建構了感染HIV等於世界末日的可怕認知,這樣的獵巫行為,跟過往的黑死病獵巫事件或是愛滋病都是來自男同志的錯誤認知,根本沒有區別,它只是換個名詞以不同的新聞事件重複上演而已。
HIV感染者的去「性」化
在過往事件的報導中,大家有空可以回顧一下,以前的相關報導,都描寫成彷彿HIV感染者只要感染了,就不應該和他人發生性行為、不應該有性的慾望,甚至會面臨社會上學校、職場甚至是家庭的不諒解甚至是惡意。而造成感染者長期情緒低落,死於自殺、事故、暴力和藥物濫用的風險偏高(Dana Rosenfeld ,2022)。
因此無論是對於撰寫HIV相關論述的網友或是報導HIV相關新聞的從業人員,也許在執筆之前可以先思考一下,你即將寫出來的內容會不會無形中傷害到這個族群內部的其他個體,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但不應該是建構在傷害他人心理甚至生理的前提之下。
國防大學歧視感染者事件
日前衛福部疾管署控訴國防大學歧視愛滋生,依《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開罰一百萬。消息一出,輿論導向竟多為支持國防大學,許多網友囿於醫學常識不足,反過來指責衛福部無知,令醫藥相關及公共衛生背景的人士,包括筆者,不禁驚訝台灣的衛生教育竟如此失敗,對愛滋病的認識還停留在20世紀的黑死病。(潔西,2016)
很遺憾2012年發生國防大學歧視感染者的新聞事件,到了現在2024年歧視仍舊還是存在,甚至依舊透過網路平台與新聞事件重複建構這些負面標籤給大眾錯誤的認知觀念,1993年,真人真事改編的美國電影《費城》,敘述原本深受公司器重與栽培的律師,在主要合夥人發現他是愛滋感染者後,以其他名義將他開除。2012年國防大學學生阿立在某次健檢中被發現感染愛滋,後來遭校方以操行成績不及格退學,引發軍方涉嫌愛滋歧視爭議。
阿立:「為什麼只因為我感染愛滋,在校方眼裡就從未來軍官變成壞學生?」
偏見和恐懼一旦深植人心,就失去任何理性討論的空間(潔西,2016)。即使在2016年,衛福部裁定歧視開罰國防部100萬元,而成為台灣第一起因「就學歧視感染者」開罰的案例。然而台灣現今感染者的「出櫃」處境仍然十分艱困,因為一旦公開坦承勢必會遭受到他人不諒解的恐懼與害怕眼光,感染者只要按時服藥處於U=U的狀態之下,就跟社會大眾一樣,並且不具有傳染力,也應該擁有實踐性與慾望的權利,希望之後不要再看到有關於污名化HIV的新聞事件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