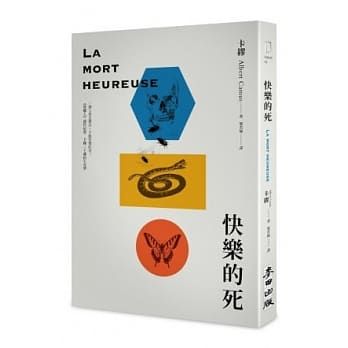《異鄉人》讀後感|淡漠是為他的原罪

「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確定。」
這是這本書開頭的第一句話。簡短、直接。一種淡漠、冰冷的感受詮釋著莫禾梭(Meursault)這名主角。
在葬禮上,他拒絕了與母親最後一次的見面,熾熱的太陽使他沒有更多心力,也彷彿燒乾他可能存在的眼淚。
他沒有在葬禮上。或者說,這對他來說只是個義務。
他在葬禮結束的隔天去往了海邊,認識了他的情人——瑪莉,還看了一齣喜劇電影。
當他的情人詢問他是否要與她結婚時,他以隨意的語調回答:「都可以,無所謂。」
這槍聲,就像四響短促的叩門聲,敲開了厄運之門
他所不在乎的一切,猛烈地襲來替他按下了那個板機,在那個震耳欲聾的槍聲中,有人應聲倒地,他的安寧從此破裂。
他似乎對於周遭發生的一切都那麼不在意,甚至包含發生在他身上的所有,而這份漠不關心、不在乎最後成了審判他的法槌,批判他為何如此,批判他是披著人皮的野獸,告訴他不具有繼續活著的資格。
他表示已經俯身檢視了我的靈魂:「諸位評審,裡面什麼都沒有。」他又說,其實我根本沒有靈魂,也沒有任何具有人性的東西。所有人類心目中的道德原則,沒有一項是我能理解的。
淡漠成了莫禾梭的原罪
他的律師告訴他,如果他說明他母親下葬的那天他沒有哭泣是因為他很好的控制了他的情緒。而莫禾梭拒絕了,因為這不是實話。
莫禾梭始終貫徹自己的價值觀,不迎合世人,拒絕神父的憐憫、拒絕遙遠的上帝的救贖。
他接受了判刑。
原因並非是他殺了人而是因為他沒有在母親的葬禮上掉淚。
死亡的直接使他強迫的審視了自己的一切,用他最後所剩不多的時間觀望自己生命的每一秒。
他理解了也釋懷了。
在這個充滿徵兆和星辰的夜晚,我第一次向這世界溫柔的冷漠敞開我自己。我感覺他跟我如此相似,又如此友善。我深覺我一直是幸福的,而且依然如此。為了使一切圓滿,為了使我不要孤單,我唯一能期望的,就是行刑那天,會有很多觀眾,以仇恨的吶喊迎接我。
猶如卡謬最經典的那句話:『向死而生』
死亡既是結束也是一份開始。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