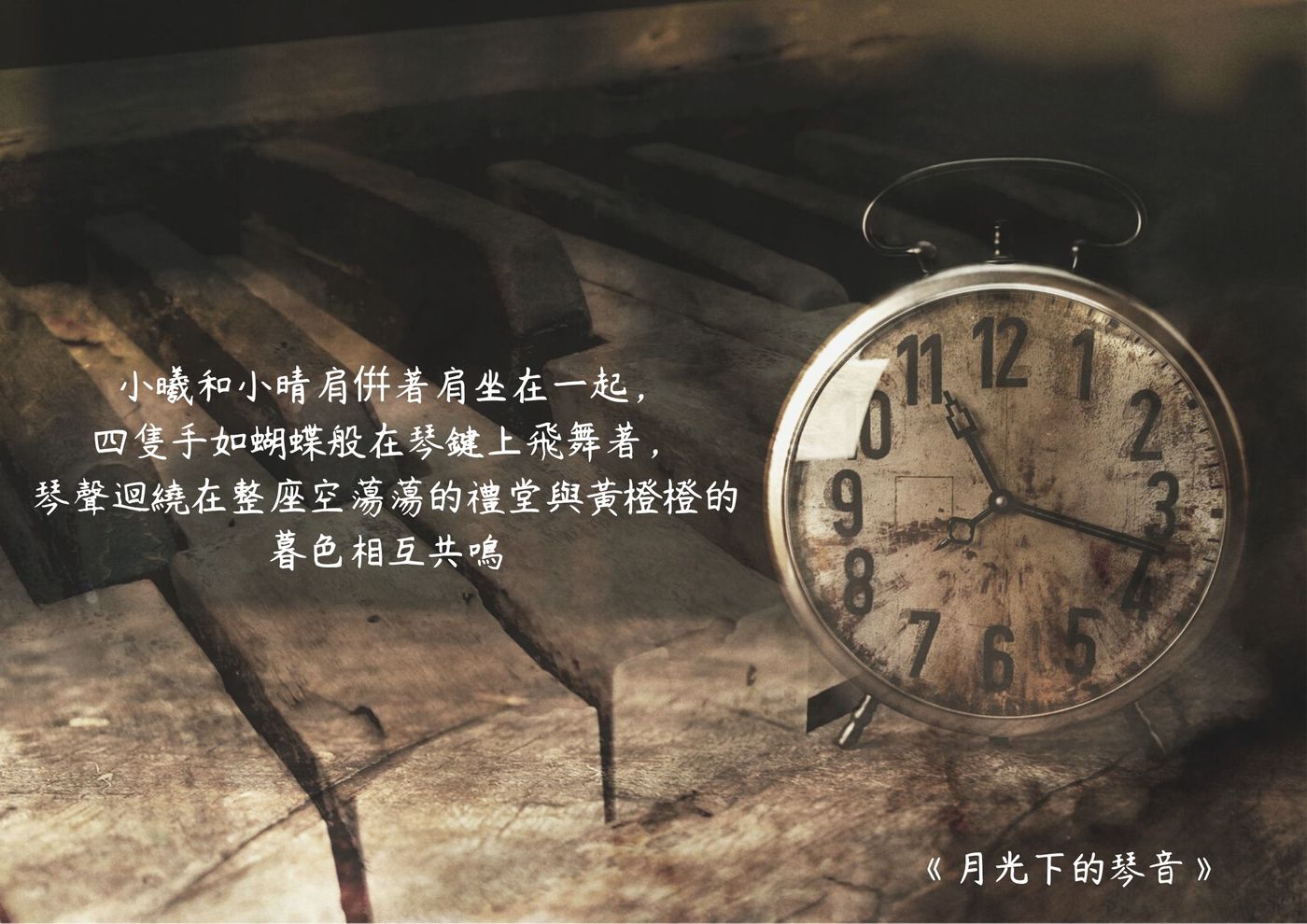「哈囉!」一個聲音傳來。
哈麗特抬起頭,看見了月亮。
「為什麼你坐在我的煙囪上?」她問。
「因為我卡住了。」月亮說。
「為什麼你會卡住?」哈麗特問。
「因為,」月亮說,「你的茶杯擊中我,所以我從天上跌下來了。」
《獻給月亮先生的音樂》
文 / 菲立普‧史戴 (Philip C. Stead)
圖 / 艾琳‧史戴(Erin E. Stead)林美琴譯,小魯文化出版社
當你撞進月光裡,所有煩憂,跟著皎潔得一乾二淨
我見過那樣的月亮──又大又圓又光潔,看起來相當靠近我;從房裡的窗子向外望,它就在鄰舍屋頂的上方,好像只須搭一座最簡便的拱橋就能走過去。
當時的我,還是名中學生。那晚,讀完該唸的書,我爬上床,熄了燈,然後輾轉覆側,竟有難言的不安;那些白日裡所壓抑的心緒,趁我不防,在夜裡全現形了。
此時,我注意到漆黑的房間內,浮現一層薄薄的白霧。我向左上方的窗戶望去,白色的月光霎時從床頭邊的窗外斜斜地灑落進來,就像銀銀亮亮的瀑布傾瀉而下,就像夜之公主以銀絲線織成的綾羅錦繡,就像月亮的腳步走了進來……它猶如一位知心老友,不管夜有多深,風有多涼,興致一來便「破窗」拜訪,使我今天整日的心煩意亂、明日難以招架的一成不變,都變得無足輕重了。
我把枕頭向窗戶挪了挪,就讓月光躺在我的枕邊,我的臉上,和我的頸上……月亮照亮大半張床,黑幽幽的房間豐盈起來。於是,我沉沉地入睡了。
每天、每天,總在掙扎面對的,不外乎是未來茫茫的不確定性、對自己的失望與困惑,還有人群之中過於喧囂的孤獨。多年後,當我想起那晚的月色,才恍然了解:啊,彼時被月光照亮、填滿的,原來是我的內心呀。

《獻給月亮先生的音樂》中,那位害羞、孤單的女孩哈麗特,也是如此。女孩哈麗特,一如她拒絕顯露的外表──長長的瀏海掩住她的表情──她也拒絕敞開心扉,拒絕被真實地了解。平時陪伴著哈麗特的,是一把大提琴。
哈麗特的父母親期望她將來能夠成為大提琴家,為眾人們拉奏悠揚的樂章。但是,哈麗特卻不願意,光是想像自己得在盛裝打扮得像企鵝的人們面前演奏,她就雙頰發燙、手心冒汗;比起在管絃樂團裡演奏,哈麗特寧可選擇獨自拉著小提琴。而哈麗特拉奏大提琴的地方,是她獨處時所想像出來的小房間;在想像的小房間內,她邂逅了被她在憤怒下扔出的茶杯擲中的月亮先生。
「哈囉!」一個聲音傳來。
哈麗特抬起頭,看見了月亮。
「為什麼你坐在我的煙囪上?」她問。
「因為我卡住了。」月亮說。
「為什麼你會卡住?」哈麗特問。
「因為,」月亮說,「你的茶杯擊中我,所以我從天上跌下來了。」
哈麗特對此愧疚不已。她找來一架梯子,爬上屋頂,將月亮先生從煙囪裡拉出來。
「我是哈麗特˙亨利。」「但是你可以叫我漢克。」
「我是月亮。」「但是你可以叫我月亮先生。」
他們互相介紹自己,一見如故,成為了朋友。接著,哈麗特拉著手推車,為感到寒冷的月亮先生到製帽匠那裡弄來一頂帽子;為想看見自己倒影的月亮先生向漁夫借來一艘船,再將船划到湖中央,面對面聽著船槳滴水與遠處浮標的聲音……
哈麗特與月亮先生共度了美好溫馨的時光。「我想,我該回家了。」
只是,他們終將得向彼此道別。離別之際,月亮先生向哈麗特提出最後一個願望,他希望自己能夠聆聽哈麗特演奏一曲。不愛為群眾演奏的哈麗特,儘管雙頰發燙、手心冒汗,她仍鼓足勇氣,答應為月亮先生演奏……這時,天地一片寧靜,惟有純淨如水的大提琴聲;哈麗特拉起琴弓,不為別人,只為月亮先生演奏。
月亮先生成為哈麗特的朋友,成為她能傾訴與分享的對象。
那晚,偶然踱到我房裡的月亮,則靜靜地陪伴我入眠。
故事最後,月亮先生回到了天上的家;隔日早晨,我床邊的月光早早地消失無蹤。然而,我的心中了無落寞與遺憾。東邊的魚肚白一出,我仍迅速下床洗漱,準備迎戰日復一日的學生生活。
彼時的我僅僅相信,我與「那樣」的月亮還會再見──有一天,它會如同昨夜那般,又大又圓又光潔,靠近地、溫柔地出現在我的窗前。而哈麗特,只要抬頭一望,也會發現月亮先生一直聆聽著她的琴聲。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一抹月光。你可能在不經意間看見它,或者離你看見它時已經隔了好多年,但屬於自己的那抹月色,恆常是記憶裡最明亮的。無論在漆黑的房間裡輾轉難眠,在小小的案前挑燈夜戰,抑或在暗夜裡偶然抬起頭,前一秒還繁亂喧騰不已的思緒,立刻在月亮含笑的注視下,靜默下來……
當你撞進月光裡,與那樣的月亮相遇,所有煩憂,跟著皎潔得一乾二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