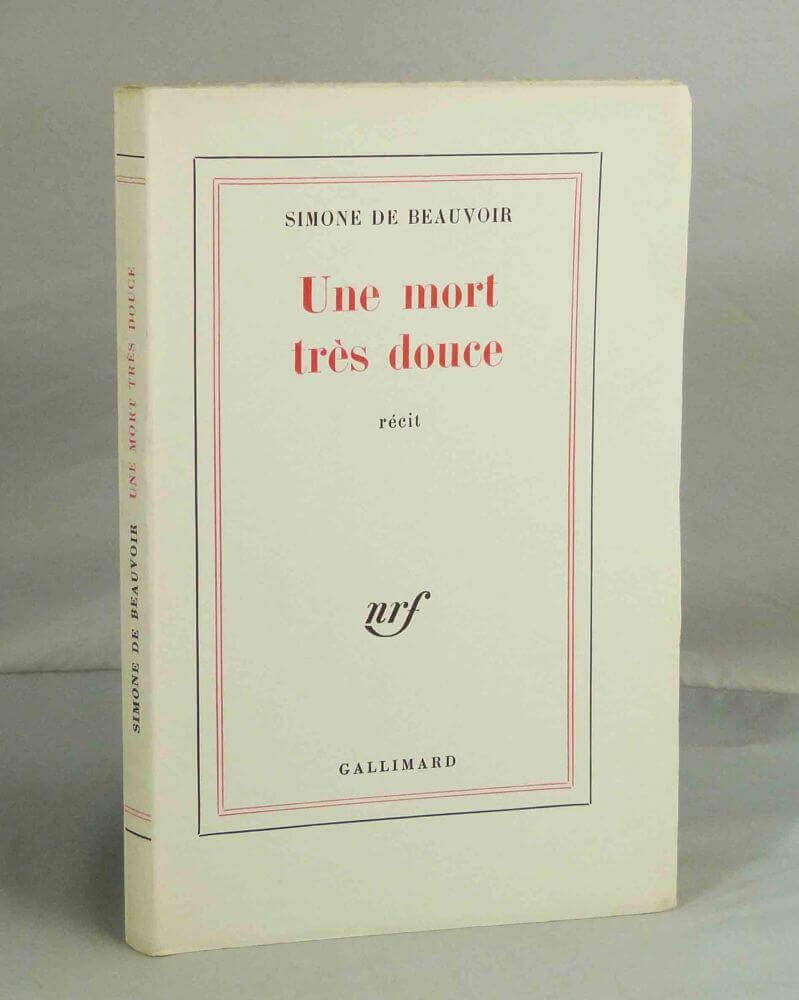緣起與碎碎念
滿二十五足歲的前半年,包含失戀等事件,我在生活中跌了N個狗吃屎,各種難題接踵而來。彷彿過去三年半內,戀情裡所經歷的平順穩定,需一次以猛料回扣,才不顯得平凡人生過於幸運。
心碎難以自持之際,唯有書籍能讓我暫時抽離現實生活。反正一樣都是弄壞眼睛,閱讀總好過無止盡的哭泣。失戀的第二個週末,至公館買了一帆布袋二手書,並與好友仙分享:「我的失戀33天,就是如此樸實無華且枯燥。」
仙邊調笑:「我覺得2021對妳真的有點太嚴格,鐵血教官來著。」邊捎來《成為西蒙波娃》一書出版消息。當時我手裡捧著《道德浪女》,正艱難地嘗試以先天標配並非頂尖的智商,理解何謂「(有道德的)開放式關係」。「西蒙波娃」這個名字再度躍入視野,靈機一動──對耶,西蒙波娃不就是一位終身實踐「開放式關係」的獨特女子嗎?這位在我大學時期啟發我接觸女性主義、上個世紀思想與行動的先驅,依然閃耀著黑曜石般,內斂而神祕的光芒。我亟欲在亂七八糟的生活中找到指引與解答,而她永遠都是一個刺激地很適切的起點。感謝前男友、摯友Q和仙與西蒙波娃,催生了《失戀書單與協尋自我、反證信仰的過程》系列文章。每篇(不確定會敲幾篇)預計以一書作為主軸,紀錄心得與思考。是我在這個絕無僅有的年紀,欲不自量力地,嘗試用大量閱讀採擷、用設計方法統整千頭萬緒,「鼓勵自己重新踏上人生旅途」,釐清、反證及反省自己在情感上與生活上的需求,進而得到成長的思考過程紀錄。

1933 失戀書單(2021版)
☛ 道德浪女:多重關係、開放關係與其他冒險的實用指南(第三版)。Janet W. Hardy, Dossie Easton(2019)。中文版/臺北市:游擊文化。
☛ 成為西蒙波娃。Kate Kirkpatrick(2021)。中文版/臺北市:衛城出版。
☛ 南方的社會,學(上):她者亦是共同體。Taiban、Sasala台邦・撒沙勒、邱韻芳、丁仁傑、張維安、張翰璧、洪馨蘭、趙恩潔、陳美華、王宏仁、楊芳枝、翁康容、洪世謙(2020)。臺北市:左岸文化。
☛ 思考的框架。Shane Parrish(2021)。中文版/臺北市:天下雜誌。
☛ 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那些關於自由、哲學家與存在主義的故事。Sarah Bakewell(2017)。中文版/臺北市:商周出版。
☛ 黑格爾。侯鴻勛(1998)。香港:中華書局。
☛ 西蒙波娃的美國紀行。Simone de Beauvior(2001)。中文版/臺北市:先覺。
☛ 告別玻璃心的女力養成指南。Amy Morin(2020)。中文版/臺北市:網路與書出版。
☛ 民國女力:近代女權歷史的挖掘、重構與新詮釋。柯惠鈴(2019)。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成為西蒙波娃》的險地之旅
承傳記作者Kate Kirkpatrick於本書前言所述:「這本傳記並沒有嘗試為波娃「真正的」模樣寫下定論,因為任何傳記作者都無法由上帝視角來觀看人的一生。確切來說,這本傳記的創作動機來自於渴望在「將波娃的人生與著作劃分開來」及「將波娃的著作化約為其人生」兩者間的這片險地上索路前行。」我在滿懷感激與驚嘆的情緒下閱畢,闔上書本時,深深認同她做得很好。
作者平衡著感性的私人立場,對龐雜資料一絲不苟,理性梳理。她將此前從未公開的新資料(部分波娃書信、私人日記),放回波娃人生的時間軸中,「還原(節制的懷疑、不煽情的批判)」了波娃在私領域與公眾視野中的矛盾面向。
波娃在前兩冊回憶錄《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與《鼎盛人生》中,將尚‧保羅‧沙特──無論作為「思想上無人能及的摯友」,或者是「必然的戀人」──放在極高的地位。而作者整理、比對了波娃寫作回憶錄同時期的日記與書信,才發現事實遠遠複雜得多了──更多不受限於身分與性別,卻同樣真切的情人們與更多的真實人生。我們不能確定,波娃是否為了遵守與「小家族」內成員的承諾(因為並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的情感關係)、維護隱私或其他理由,而隱去了多位情人的故事與重要性。波娃在寫作回憶錄的年紀,已然熟知了「成為公眾人物的景況」,其中的甜蜜與困擾不足為外人道也。
自我與他者的對立
全書作者一再反詰西蒙波娃於1927年學生日記中,寫下並思考的哲學概念(而後被世人認為是沙特《存在與虛無》提出的原創理念,日記成文時序卻比沙特的書還要早將近十五年):將自我分成「給自己的(沙特的「對己存有」)」與「給他人的(對他存有)」。在波娃晚年,作為她自己人生的主體,已然經歷傳奇且豐富多彩的一生,對比外界卻永遠視之「沙特修道院」(La grande Sartreuse)、「沙特的聖母」、「沙特最忠實的信徒與幫手」此等抱有性別歧視惡意的「第二性客體」──連作為讀者的我都感到無比氣餒,若波娃當下,確實為了「省事」而「矯造、藏匿」某些生活情節,來保護大眾所不能理解之生命面向與情感故事──我可一點都不會質疑她的矛盾。

波娃持續思考著「自我與他者的對立」,透過小說《女賓》寫下:「要相信他人也具有意識、也像我們一樣能到意識到自身內在的感覺,這件事近乎不可能〔……〕理解到此事是非常可怕的。我們會有種自己什麼都不是、只是別人腦海中的想像之物的感覺。」她藉由小說提出哲學:「與他人建立關係的模式分為兩種:第一種模式承認他人如同自己一般,是具有意識、內在生活豐富的脆弱個體。另一種模式則是拒絕看見此點,拒絕接受互饋可能性,以理所當然的態度將他者視為可供我用之物抑或阻礙我路之物。」
我對於波娃在此議題上採取與沙特(他人即地獄)相反的觀點感到敬佩。畢竟真正認知到「他人也是主體」(遙遙呼應《南方的社會,學:她者亦是共同體》這本標題下得太好的社會學論文集),意即你必須「尊重」與「真實看見」對方,像善待自己般,善待、接納對方。你必須「負責地」投身世事間與人交流,參與「標註」與「被詮釋」的互相作用過程。
我始終認為人不可能逃逸於社交、社群之外。然而,「有意識的」成為自己、見證他人又是另一個新的層次:保持警醒的能動主體(Agent)身分參與過程的推動,主動讓角色、主客體之間的平衡與立場流動,並接受它會隨著事態、歲月改變──它成立的前提,確實是真實的看見對方與自己皆是具有意識的自由主體,謙遜接受此消彼長,或共同前進,致力於幫助對方達成人生目標與成就,享受愛與被愛,達成互利共生。
Kate Kirkpatrick在文本中最後一句提及波娃的話,同時是本書的最後一句結語:「如果有一件事是我們能從西蒙‧德‧波娃的人生中學到的,那就是:沒有人能在孤獨之中成為自己。」傳神的點出波娃的人生觀(個人認為可用佛教語境裡的「入世」形容之)。波娃選擇自由的愛恨、貪嗔癡,純真且炙熱地愛著戀人們;既享受工作帶來的成就感,也承擔名利帶來的甜美與後果;經歷戰爭,所以積極參與政治行動、創辦《摩登時代》雜誌,數次表達與政府當局在人權議題上相左的鮮明立場;晚年正視階級帶來的「處境」,寫文章關注菁英/文化階級之外、處於各景況的女性與老年人,並與數名讀者魚雁往返數十年。
✍ 思考筆記:
- 我是否真實接納了「他者不容質疑的主體性」,並為之負起責任?
- 在高度商業化的資本社會裡,身處密集人際交流的公共場域例如「職場」,我需要投入多少真實的自我、「看見同事」「多少程度」呢?公私領域界線如何規劃?要如何讓自己不涉入過多的「他國事務」,卻又不消弭他者主體性的情況下,被完整定義與執行?
《第二性》不只是女性主義?
童年玩伴兼人生摯友莎莎香消玉損,看見其無力的性別處境而埋下書寫種子的多年後,西蒙波娃撰寫出「女性主義的聖經」《第二性》。她曾言:「我希望總有一天,《第二性》是落伍、過時的。」
而今的性別議題,舉凡受教權、同工同酬、月經貧窮、性暴力與身體自主權、接納或解構多元性別、解放所有固化性別角色、情慾去汙名化、家庭型態多元化等,皆已有許多進展。我卻認為《第二性》依然具有存在的必要與價值。原因有二:
閱讀角度一:以「性別身分」閱之
《第二性》當年出版英譯本時,遭譯者(生理男性)與出版社大幅刪去「他認為不重要(卻是波娃本人認為非常重要)的幾個段落(份量大概是全書三分之一)」。連近年台版由譯者邱瑞鑾從法文直譯的三冊裝(2013版,也是我大學時期拜讀的版本),都以「全世界都被英譯本誤導了60年!」作為宣傳,可見茲事體大。
「感受到即使身處1949年的社會,女性仍是次等存在,處境窘迫且難堪。」是否影響西蒙波娃在早年不以「女性主義者」自居?畢竟,被《第二性》所啟發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還要在時間裡走上廿年才會成為現實。書裡是這麼說的:「此書出版後,波娃作為樣板(補充內文上一段的樣板定義:在階級、種族與教育上都擁有特權的女性身分)卻竟敢直言不諱而付出極為高昂的代價。波娃從沙特巨大的陰影中走出來,卻發現自己成為了人們進行訴諸性別攻擊的對象,受盡嘲諷、蔑視與羞辱。」彷彿女性身分標籤只容許對極的二分法──不是聖潔高貴的聖母,就是不知足的臭婊子;且無論是哪種身分,最好都不要說太多話,即使說話,也不要說出習於被忽略的真相或真心話。
此處僅舉一個例子就好了:時至今日,各行業裡的獨身女性「因為沒有生過孩子,所以沒資格發表對xx事務的高見」此類因為身分而無限上綱、被剝奪話語權的案例還少嗎?至少我可沒聽過「黃金單身漢」因為同樣處境,而被阻止在任何話題上現身說法。這不比波娃在六十年前遇到的情況進步多少耶。鬆綁身分與性別相互綁架、固化的刻板概念,我們還有更多的努力空間。
上述立場,大致契合20歲時──女性意識覺醒後,初出茅蘆以「理解女性主義」作為目標──試讀《第二性》的感想。
閱讀角度二:「去性別化」閱之
然而,在大二到社三的這五年間,我陸續接觸了第三波女性主義(酷兒、少女革命、微觀政治、性慾去汙名化)。讀過《成為西蒙波娃》,明白了波娃對存在主義的詮釋與定義。我想是時候,適當地在某些段落,去性別化,帶著更宏觀的視野──「對於自由之覺悟」的角度去閱讀它。
西蒙波娃是一個注重「處境」概念的人。沙特主張每個人「都有」自由的權力與權利,並必須為之負起責任。波娃認同他,卻更細膩地關注:每個人手上握有可以自由選擇的權力並不相等,因為每個人都處在各自的處境裡。例如,早期美國社會只將黑人限縮在從事農僕、保母與擦鞋服務的勞動、傭人階層,再來責怪他們做得不好、沒辦法勝任更困難的工作,這並不上道──打從一開始,黑人擁有的選擇就不多。「『黑人』一詞,必須在白人所打造的世界裡才擁有意義。」「一個人只有在涉及和另外一個人的關係時才會被設立為他者。一個孩子存在於自身之中,不會察覺自己有性別。」是整座文明與個人處在的景況裡,塑造了這個人。
因此,波娃在《第二性》透過幾個方面來剖析處境:生物學(生理限制)、精神分析學(心理限制)、歷史唯物論(經濟限制),並從中推演女性應該要如何突破限制,成為與男性一樣的開放性存在。
上段即使抽除男性、女性等性別身分,也依然是「我要成為一位自由的人」條理清晰的檢視架構。成為自由的人,或更具體來說,「可以自由做選擇的人」,必須負擔什麼樣的責任或代價呢?
☝我要成為一名自由學習的學生:
☑ 規劃時間表,打工或自主學習,把握我想嘗試的事物(金錢限制)(哦對,未成年自由學生的主要照顧者也須受經濟限制)
☑ 偶爾尚須對抗權威的質疑(心理限制)
☝我要成為一名能真實掌握人生進程的獨立女性:
☑ 必須養得活自己、把自己的身體照顧好(生理限制)
☑ (如果想要生小孩但沒對象)須負擔得起凍卵或精子銀行(經濟限制)
☑ 能夠面對外界七嘴八舌指點的健康心態(心理限制)
☝我要成為一名自由戀愛且情慾自由的人:
☑ 花費更多心力,維護身體健康、保持良好外貌,且安全性行為(生理限制)
☑ 若處在多對象關係中,須更努力地維繫人際社交網絡,健康的心理狀態也很重要(心理限制)
☝我要成為一名民主社會中的公民:
☑ 在資訊爆炸的當代,花費心力培養批判性思考、攢取知識與足夠社會經驗,選出可以維護民主自由以及我的利益的公僕(知識經濟限制)
☑ 維護言論自由;尊重與我立場不同的人(心理限制)
多年前,曾經在人滿為患的捷運上邂逅一對母子。兒子大約六七歲,半撒嬌半撒潑地對母親發脾氣:「媽媽,我腳好痠,想要坐。」她的回話,至今仍深深影響著我:「你今天選擇要跟媽媽出門時,我已經分析給你聽了對不對?今天我們走的行程,以你的體力與年紀來說,會讓你很疲倦;回來的時間正好交通繁忙,人會很多,你必須承擔有可能坐不到位子的風險。而你仍然選擇了出門。我尊重你的意見、帶你出門。現在,你要為選擇負責任,你今天踏出家門,就要有能力回家。」
自由,的確是真實、深刻,且十分痛苦的事啊。
我、西蒙波娃與少女革命
承前所述,大學時期除了《第二性》外,作家施舜翔讚揚陰性特質、顛覆「正派」的著作《惡女力:後女性主義的流行電影解剖學》與《少女革命:時尚與文化的百年進化史》皆啟發了我更認同、更擁抱「女性身分」。大千世界中,它是流動的、包容的、彩色的、亦正亦邪的,一種幽默、迷人的人生信仰。
人們常將西蒙波娃與其著作「他者化」:視她的文學附屬於闡述沙特哲學的「通俗讀物」,視她的才情機智附屬於沙特,視她想藉由小說創作觀照人生的壯志附屬於「自戀的自我揭露,沙特那群人的貴圈真亂」。
然而,我卻自波娃身上看見少女力的展演與諭示。小從她喜歡著用良好衣料品妝點、展示自身,大到她以文筆、思想,著作操演、搬弄故事與人生情節,供給人們參閱、疑竇,為讀者帶來啟發,也使自己遭受攻擊與嘲諷──無論她是否為了保護自己,適當揭露、隱蔽或竄改事實,仍不掩她是擁有一定自主權的那一方的事實。
「我過往的人生經歷是一個問題意識,我不必提出解答,人們也沒有權利要求我提供答案。」波娃如是言。我們無法知道,她對於自己的人生活得精彩且具藝術啟發性,是否感到小小自豪。她卻已然真真切切地鼓勵了時光洪流裡,萬千渴望依照自己的方式而活的靈魂,去思考、去行動。
大劫與小結
回到自己的情況,自四月中旬感情狀態有所變化以來,發現自己在社群上有苦難言。這對於將寫作當成生活樂趣──傾訴自我、訴諸存在的我來說,並不常見。
憑據好友們往日的見證與讚許,她們形容我「總是做為能夠啟發她們:哦!原來女孩子可以這樣活」的角色。身在其中,我很快樂。將少女革命精神奉為人生信仰、不畏懼揭露自身、分享生命與想法、包容所有來臨與指教。它是我的自我認同中不可或缺的標籤。
而當難以區分對錯的感情狀態遭逢他人眼光凝視並錯誤解讀,與事實產生偏誤,化約了我的生命經驗,所有原本曖昧得有趣的事、亦正亦邪的事,都變成他人定義的「全然負面」。我的心情泥濘不堪,一切開始難以啟齒,無法精準下筆。
閱讀《成為西蒙波娃》的三個禮拜以來,數次被傳記作者Kate Kirkpatrick溫柔謹慎的文筆與西蒙波娃集瀟灑不羈與一絲不苟於大成的人格魅力拯救。
她確實因為公眾人物的身分,承受他人的妄自解讀還被要求解答,而感到困擾──但那也是因為她有權利感到困擾。我不認為「因為你是公眾人物所以受到這樣的對待是一種對於你收穫身為公眾人物的好處的回扣」(繞口令?)的大包套組合是合理的,何況我不是公眾人物呢。我只是一個以活好自己為己任,選擇以女性身分、女性主義者身分活下去的人而已。
承擔他人以自己喜歡或不喜歡的方式來解讀與觀看自己,因為自己的行動可能盡顯了某一面向,而並不完整。不過,完整與否、情態展演與否,這意味著我能夠身為能動主體,有意識汰選,在某對象面前展演不同面向的自我、展現自身流動性,不是一件需要被斥為「不真誠」的壞事。因為我的愛很真──對珍視之人的關切,對世界的好奇心,對知識與生命所有幽微真諦的叩問,都很真實。
只是我也更該,珍重所有離別、放棄奢求無解的答案,寬容自己的愧疚、懊惱、心神嚮往的真實欲求。它們全都是真實的,不會如股票獲利彼此抵銷,它們相關卻又獨立的存在著。不再責怪誰沒辦法達成我的要求,不再自責沒辦法引領誰去完成我的想望,更放過自己曾像灰姑娘繼姊一樣為了達到他者期盼而割肉流血,硬塞入不合腳玻璃鞋的悲愴與努力。
在想懂那些之前,我亦曾排拒「自身成長與我的愛人們皆有關」(是否每一位心思敏感又需要情愛的女子都曾不小心內化性別歧視進自我價值中呢?)但依據主體認知脈絡,是我認可社會性的重要、認可對方之於我的存在價值,所以承認我的劇烈成長「永遠」與我愛的人有關,並非一件可恥的事啊。只是他們因為我的性向而剛好都是「男人/男生」而已。所以此後「妳的成長都嘛和男人掛勾」等,我不確定發話者到底是否帶有貶意的評論對我造成的殺傷力應該也只會越來越小。因為那縱是事實,卻並非全貌。女性主義讀到最後,我作為誠實而敏感的人,「選擇成為」社會架構之內具有特定指涉意涵的「女人」之前,我們都只是人而已。
我就是在這一點一滴的,收藏喜歡人們的所思所想、神態舉止、小細節與小缺點的過程裡,帶著我的思想、舉止、細節與缺點,與人相處,成為纖細又理智的我。
關係們的死亡、停頓或改變,帶來的痛苦,令起初「非自願再生」的我,有點不安。爾後,聽到仙說今年是我的復甦年,會心大笑的同時,頓感一陣心虛:似乎否定了關係們多年來的平穩與關照?但現在認知到選擇都在自己身上,只有自己可以決定它是否具有意義──而我認知了此事,也依然心生感佩,它們就無比真實。它們讓我找到古又新的方向,重新迎向不同的挑戰與未來。
保持著開放且柔軟的心,繼續在人類尚僅能以科學理解的,單向度時空概念裡,寬容期許自己和所愛之人往更舒適的應許地前進。不排斥任何可能,不急促也不拖延地,成為自己。
嗨,我是1933,興趣使然身體力行少女革命的女性主義者。如果喜歡我的文章,歡迎按下小愛心或是留言踏踏。讓我們不定期再見(灬ºωº灬)
可甜可鹹,酸辣有致。
閱讀更多1933的文字/關於過盛的女性荷爾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