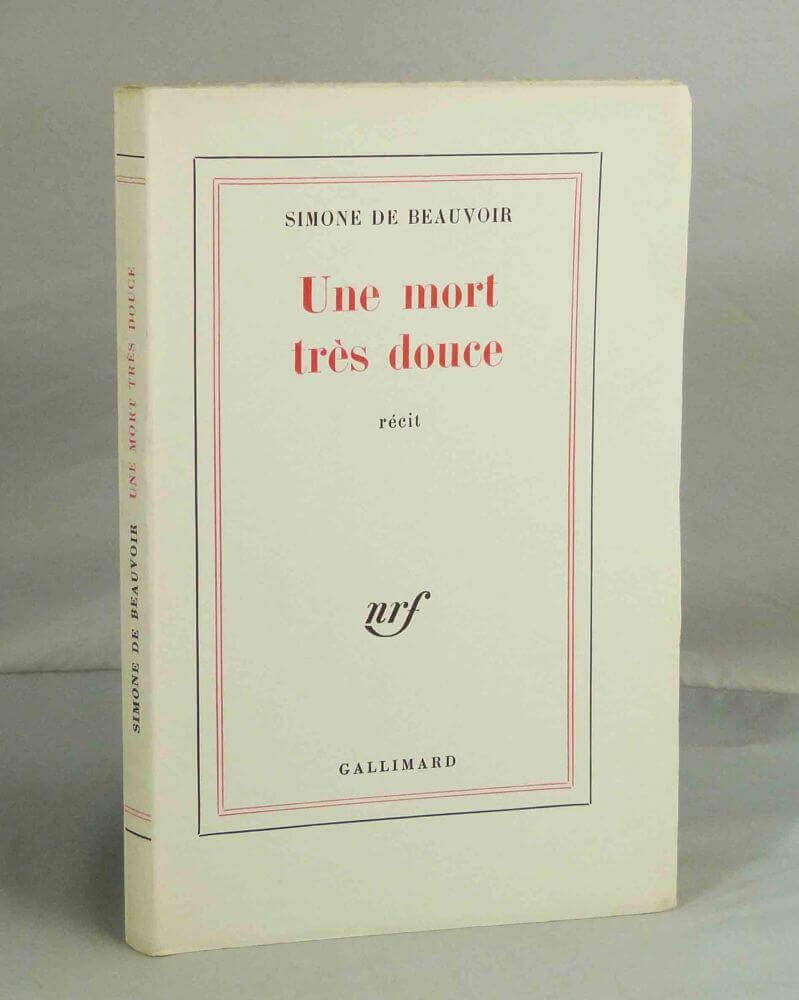前言
此為筆者某堂課之期末作業,有鑑於西蒙波娃的討論稀少,希冀能拋磚引玉。
一、選書
我選的書是《成為西蒙波娃》(2021),並夾雜著閱讀部分之《第二性》(法文直譯本;2013)及《西蒙‧波娃回憶錄—一位嫻靜淑女的自傳》(1991);為了補充邏輯思考的廣度與深度,還包含了《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2021)、《自己的房間》(2017)以及《成為一個人:一個治療者對心理治療的觀點》(2014)的部分段落。
二、之所以特殊與資優
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資優在哪?又屬於特殊族群資優的哪個類別?從波娃的第一本回憶錄—《西蒙‧波娃回憶錄—一位嫻靜淑女的自傳》中,可以看見幼年波娃的批判性思考能力非凡,即便她的母親芳絲瓦是位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幼小的她因為觀察到大人(grown-ups)對待她「像是在應付小孩」而非常生氣(Beauvoir,1991)。她的父親也認為她是個很有主見的孩子:「西蒙有男人的頭腦,她以男人的方式思考,她簡直就是個男人。」(Kirkpatrick,2021)。五歲半時,波娃開始去修道院學校上學,有別於其他孩子厭惡上學,她非常享受自己也有事情可以忙碌的過程:自己的書包、自己的作業、自己的生活。但其實那時對於波娃家族而言,上學是不光彩的—波娃家族擁有皇家頭銜,但家道中落史的她們無法負擔私人家教(Beauvoir,1991)。十一歲後,波娃突然發現她想成為的樣子並不是家人所期望的;波娃固然早慧,卻在十一歲以後要求她停止思考、停止閱讀。波娃曾經欣賞父親的博學,以及他願意與波娃討論自己提出的問題。波娃從前的開朗隨著父母開始欣賞小波娃兩歲半的妹妹艾蓮娜(Henriette-Hélène de Beauvoir,家人都叫她Poupette,即洋娃娃)長大,並較符合社會對女性的期待(洋娃娃般地美貌與行為舉止)而消散。波娃並沒有因家人的態度而灰心,她以《小婦人》裡的角色喬(Jo)為典範,喬不是眾姊妹裡面品德最高尚或外貌最美麗的,但她對於寫作的熱情深深吸引了波娃(Kirkpatrick,2021)。十六歲那年,她通過了第一次高中會考,並在準備第二次高中會考時愛上了哲學這門科目。波娃希望可以去讀培育公立初中與高中老師的大學,但這所學校並不符合芳絲瓦認為的「虔誠」,但最後她的父母讓步了—相較於他們希望的法律,他們讓堅持的波娃去讀文學(Kirkpatrick,2021)。
她在巴黎天主教大學修讀數學並取得數學和哲學專業的學士學位後,她到聖瑪莉學院(Institut Sainte-Marie)修讀文學/語言。波娃第一年便拿到一系列證書,涵蓋數學,文學、拉丁語,第二年拿到了哲學證書;20歲那年,在獲得心理學科證書後,波娃最終取得哲學文科學士學位。
21歲時,波娃認識了荷內‧馬厄(René Maheu)、保羅‧尼贊(Paul Nizan)與保羅‧沙特(Jean-Paul Satre),他們成為了未來支持著波娃生活「小家族」的奠基。他們一起組讀書會,準備教師資格國考筆試,並在口試中得到了第二名—僅次於已經準備第二年國考的沙特(Kirkpatrick,2021)。口試委員雖然認為波娃的表現比沙特亮眼,「是真正的哲學家」但礙於性別考量,還是將沙特列為第一名。拿到教師資格後,她便開始在法國各校任教,直到35歲後才離開教育體系,成為全職作家。
波娃的優勢在於她對文學的熱情、哲學的嚴謹、以及聰慧的學習能力;相比而言,女性的身分成為了當時的她「劣勢的處境」,即便在現代我們不傾向特別強調女性資優生是「特殊的」,但以波娃的背景脈絡與她為女性主義哲學思潮做出的貢獻,我認為便是特殊族群資優的優異表現。
三、資優展現與困境
1940年代,波娃曾表示
令我不悅的是,每當討論抽象事物時總會有男性告訴我:「你之所以會這樣想,是因為你是個女人。」而我知道唯一的反擊方式是告訴對方「我之所以會這樣想,是因為這是真的」—如此一來我便抹煞了自身的主體性。我不可能告訴他們「你與我想法相反,是因為你是個男人」—因為身為男性這件事並不具備特殊性,身為男性的人天生就是正當的存在(Kirkpatrick,2021)。
而這段「女人是男人所不是的」借鑑了黑格爾的「他者」概念。黑格爾認為,人類根深蒂固的傾向,總會把「自己」與觀看/視之為他者的對象(object)放在對立面,於是在男性視為自己為主體時,女人便被界定為客體了。
這邊要特別處理「看」這個字詞的用法。法文的voir和regarder都有「觀看某物」的意思 (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https://www.collinsdictionary.com/dictionary/english-french),相較於voir指的是「看見;目擊」(to see; to witness),regarder指的是「主動的觀看;觀察」(to watch, to observe)。而無論是黑格爾或是波娃處理「看」這個動詞時,熟稔英文的我們可以擴展為 “regard as”的「看待」(Cambridge Dictionary;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筆者認為這樣的澄清會讓讀者較容易進入狀況。
《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第一冊在1949年六月的出版蔚為暢銷。波娃指出,生物構造並不能決定人的命運。「身為女人並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狀態,而是一種成為的過程。在這樣的過程中,她必須與男性作出比較,而她的可能性便顯明出來。」而當一個人帶著意識的思考著並不斷地改變,如此使得「那樣的過程將是永無止境的。」(Kirkpatrick,2021)。
《第二性》第二冊道出了她的名言「女人並非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第二冊相較於第一冊的歷史耙梳,則展現了不同處境的女人的樣貌及實際經歷。在理解自己的生命經驗的同時,波娃也察覺到自己生命中所面臨的困境也普遍存在於許多女性的歷程中,即便寫完了《第二性》,波娃始終認為自己依然在成為的過程中。
第二性的出版碰上了二戰結束,大眾正盼望著人口數回升(戰爭導致法國人口數變少),有些人指控波娃不只在第二性的中對於母職的論述及直率的女性性慾描寫下背叛了自己的性別,還背叛了自己的國家。對於女性懷孕期間所失去的身體自主性,以及在意識到「成為母親」前的焦慮,波娃認為社會不應該將女性簡化為「生育功能之務」但這番論述並不是在拒斥母職(Kirkpatrick,2021);更精確地來說,在個別女性的處境不同的前提下,女人成為母親的歷程將會被以不同的方式被經歷。
男性在愛情中保有「主權主體」(sovereign subjects)的身分,男性珍視自己所愛的女性,但同時可以擁有其他的人生目標與追求的權利。反觀女性的角色,愛情似乎就是人生本身,理想的愛情觀鼓勵女性為了她們心愛的人而犧牲自我。社會教導女性,她們的價值建立在「有男人愛她們」的前提下。在珍‧奧斯汀(Jane Austin)的《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中,即便伊莉莎白拒絕了攸關整個家庭經濟與財產繼承權的婚事,最後仍然「認清了自己的傲慢與偏見」接受了達西先生—來自家財萬貫的仕紳望族—的求婚;波娃的啟蒙者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名言「女性若是想要寫作,一定要有錢和自己的房間。」也強調了資本的重要性。反觀東方,無論是中華文化的童養媳及重男輕女、抑或是開發中國家未成年女孩被強迫童婚(Kenzo,2015),一在地將女性物化成「財產」與男性的「欲望客體」即便女性想捍衛自己的主體性,如同波娃遇到的困境一般佈滿荊棘。
對於波娃來說,理想的愛情模式應當是「相互回饋的關係」,而異性戀主體的父權世界觀期待著女性以「殉道者」的身分為丈夫、原生家庭及子女付出隱形勞動(無論是物理上或心理上的);波娃認為,這使得女性在愛情與婚姻的架構中是危險的,但她也強調,如此的結果責任歸咎不只有在譴責男性上,女性在結構中也壓迫了自己—女性無法全身而退。
《第二性》出版時,波娃已經41歲,而《第二性》也被認為是超越時代的著作,以現代的觀點來看依然是女性主義的必讀經典。波娃可貴的地方在於她使用了自己最擅長的哲學語言,做了古典文化(古希臘劇作家、羅馬哲學家等)、哲學(叔本華、黑格爾)與文學素養的整合,也在撰寫此書時討論了「那些哲學菁英不認為可以當作是哲學」的問題,她跨出哲學,「觀察」了「順從客體女性」的日常生活:家事如何分配、女性中的性啟蒙與經驗。波娃在前言便提到自己「在開始動筆寫以女性為題的書之前,我猶豫了好久。」她無法袖手旁觀地看著上個世紀囑咐女人應當有的樣貌。波娃從來沒有預料過《第二性》會成為後世對於女性主義的代名詞,但她充分地透過書寫,將人類學與哲學揉進這部作品,展現了成為西蒙波娃的自我實現。
以Carl Rogers的語言來說,波娃「評價的內在樞紐」非常堅定—她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亦挑起了如此選擇所需承擔的責任;而「變動不居的複雜體驗」之於Rogers是心理治療過程的一部分,卻是波娃對於戀愛、女性主義、哲學與寫作的實踐歷程。人們總是批評波娃的「開放式關係」是毫無倫理與道理可言,儘管感情不是她之所以卓越的必備要素,波娃選擇如此與所愛之人(無論是他或她,書中有太多戀人了)形成的是「穩定的智性交流與關懷。」精確地說,在她母親跌倒時,是「小家庭」中的博斯特(Jacques-Laurent Bost)發現並通知西蒙的(Beauvoir,2021);在沙特病逝時,也是博斯特與朗茲曼(Claude Lanzmann)支持著波娃(Kirkpatrick,2021)。他們都是小家庭的成員,而他們在關係中尋找的不單單只有大眾認為的戀愛—更多時候是無條件的陪伴。
四、心得與結語
前陣子我在眾多書籍中發現了一個現象:當波娃被提及時,一定會談到沙特;但當沙特被討論時,波娃的出現不會是必然。沙特跟波娃是彼此「必然的需要與存在」,但他們的關係如果用單純的「戀人或朋友」之二分法看待,是不公平且不嚴謹的。
我從波娃身上學到的,莫過於她的勇氣以及在夢想之前腳踏實地的務實:她勇於堅持不讀法律忤逆父母的希冀,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作家,同時也考量生計,使用自己的強項(聰明會讀書拿證書的腦袋)考取教師資格養活自己。在中年以後,她順利成為作家,回應了幼時對自己的期許。
我認為資優之於女性,實務上可能沒有辦法以制度改變現象。但我們都在建構世界,就像波娃所說的「成為」我想身為助人者可以做的是:好好的regarder每個女孩,讓她們勇於成為自我。
參考文獻
Beauvoir, S. D. (1991)。西蒙‧波娃回憶錄—一位嫻靜淑女的自傳(楊翠屏譯)。志文。(原著出版於1958年)
Beauvoir, S. D. (2013)。第二性(邱瑞鑾譯)。貓頭鷹。(原著出版於1949年)
Beauvoir, S. D. (2021)。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周桂音譯)。商周出版。(原著出版於1964年)
Kenzo (2015)。全球童婚悲歌:26國女性18歲前被迫結婚機率遠高於繼續升學。關鍵評論網。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6264
Kirkpatrick, K. (2021)。成為西蒙波娃(張葳譯)。衛城出版。(原著出版於2019年)
Rogers, C. R. (2014)。成為一個人: 一個治療者對心理治療的觀點(宋文里譯)。左岸文化。(原著出版於1961年)
Woolf, V. (2017)。自己的房間(宋偉航譯)。漫遊者文化。(原著出版於19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