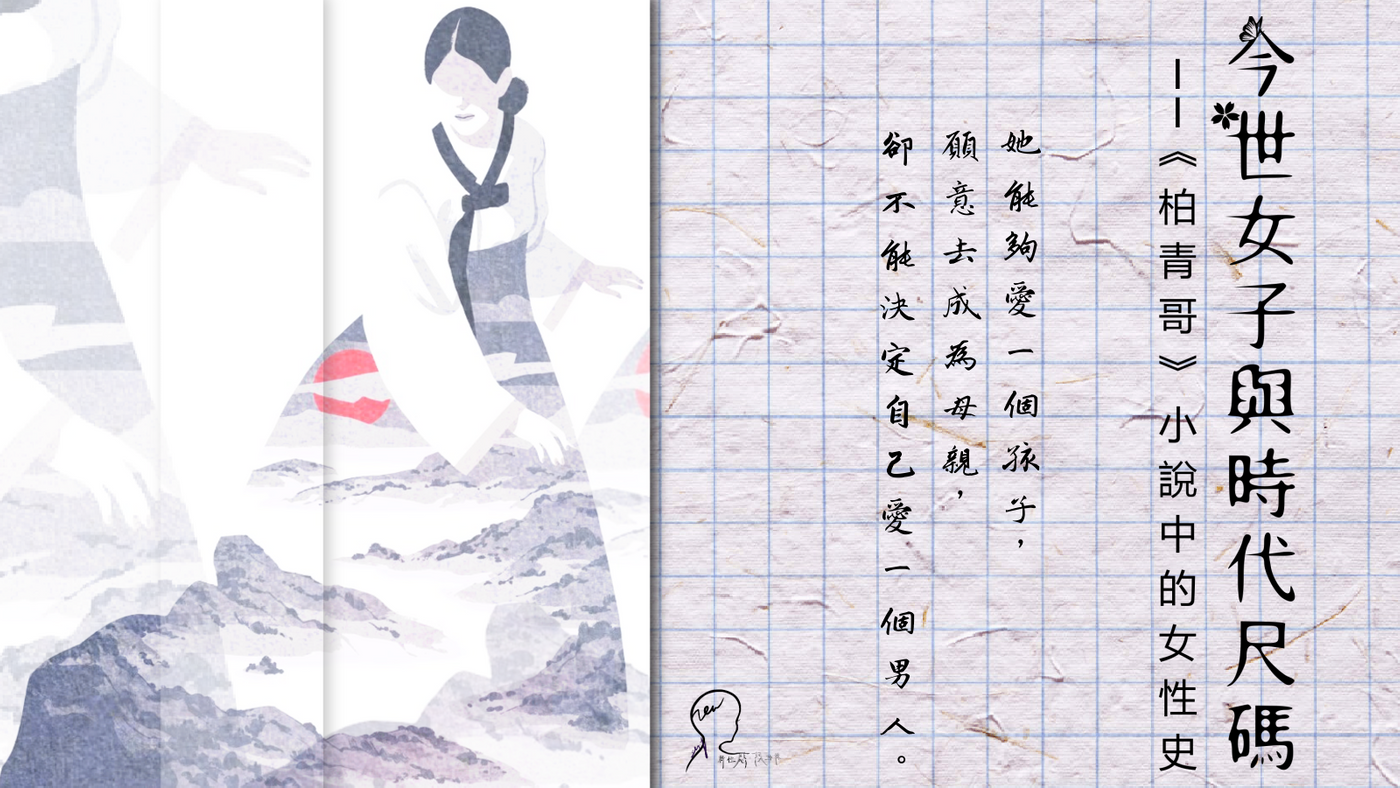我喜歡步行,在台北,在巴黎,在海邊,在山上,但不能在塔利班政權下的阿富汗,也不能在現在的基輔,還有其他受到戰火、暴君控制的城市。
我喜歡步行,此時的頭腦是自由的。那是屬於獨享的時間,一邊走路一邊思考,小時候待在家裡壓力太大,總是找各種機會出門,戴上耳機播放著喜歡的音樂,一直繞行民生東路上光復北路到敦化北路的那小段路,瀏覽著服飾店裡的衣服、欣賞眼鏡行的太陽眼鏡廣告、讀著咖啡廳掛在門外的目錄,彷彿是在城市的小旅行⋯⋯步伐隨著音樂節奏而改變,暫時逃離現實的生活。
我喜歡步行,步行中的城市是美好的。能看清楚行人的表情,猜測他們當下的心情,遇到喜歡的店家能直接停下進入,但步行的自由不屬於全人類,是離開故鄉後才有的體悟。在台北能以步行到達所有想去的地方,只要時間允許,離開台北城外,許多地方沒有行人專用道,無法悠哉行走,有時人行道會在中途被截斷,逼著行人繞路或者與車進行搶道。讀過作家愛亞的一篇散文,寫給台北市民的公開信。那時她兒子正要讀小學,以母親的角度期盼路上的車輛能禮讓學童,讓他們安心的步行上下學,母親也才能放手將子女交給社會。市民們能自由自在走在路上,享有行人路權,不只是政府在規劃都市時需考量的,同時也是將自己生命交給在道路上所有的用路人手中,是社會中的彼此信任與友愛,一旦路上有不守規矩的人,秩序則會被破壞,也會逐漸降低人們對彼此的信任感。
一座自由的城市,是有自由步行的權利。
但此自由不一定全面,在台北不論多晚都能在穿過公園,有時公園也被當作道路的一部分。但某些城市的公園有關門時間,不能隨心所欲經過,我曾在巴黎的公園散步忘了留意,被管理員「抓到」要求立即離開,才意識到這看似無關緊要的規則——通常是為了管理及避免成為治安死角——卻限制了部分人的行動,想像你若剛好從公園平行的兩側活動,就只能繞一個U字型的路線。
步行者的自由包括心境上的。
大學時到俄羅斯交換一年的朋友回來分享說,「我在台北校園中遇到迎面而來的同學,即使不曾談話也會點頭示意,畢竟見過他,無法假裝沒看到。但在那裡不同,和見過的人點頭微笑,他們只是板著臉,好像我是瘋子。幾個月後,走在路上看到有人跟我微笑,也覺得那人腦袋有問題。」
當時我回他:「還好你回來了。」在行走中遇到的行人皆不友善,也會影響到步行者的情緒。
盧梭在《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中提到,散步到傷兵醫院時遇到的老兵對他的態度從友善到忽視,造成他的心情低落,並猜測是誰在傳播他的壞話。我記得在巴黎第一週就留意到路上和陌生人眼神接觸,對方會禮貌的說「日安!」,那是我願意多走路的起因,而在地鐵遇到的人總是將彼此視為障礙物,這讓我不太自在,彷彿我不應該出現在此。
步行者最終被剝奪自由的一天。
二月二十四日,基輔當地時間七點起陸續響起空襲警報,部分民眾就近躲入附近的地鐵站內。戒嚴的那刻起,不再享有步行的自由,居民被告知不要離開住家,但要預先打包裝有必需品的隨身行李,以防隨時可能需逃難,駛離市區的公路已出現大塞車,即便如此依然有許多從未使用過彈藥的烏克蘭平民願意為國而戰,拿起武器上街對抗俄羅斯軍人。(烏克蘭內政部與基輔市府也在二十五日午後開始「武裝全城市民」,只要願意留守者,就能登記作戰、憑身分證領取步槍與彈藥)
沒人知道戰爭要持續多久⋯⋯願所有被侵略者、暴君、瘟疫所困住的人,能早日享有步行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