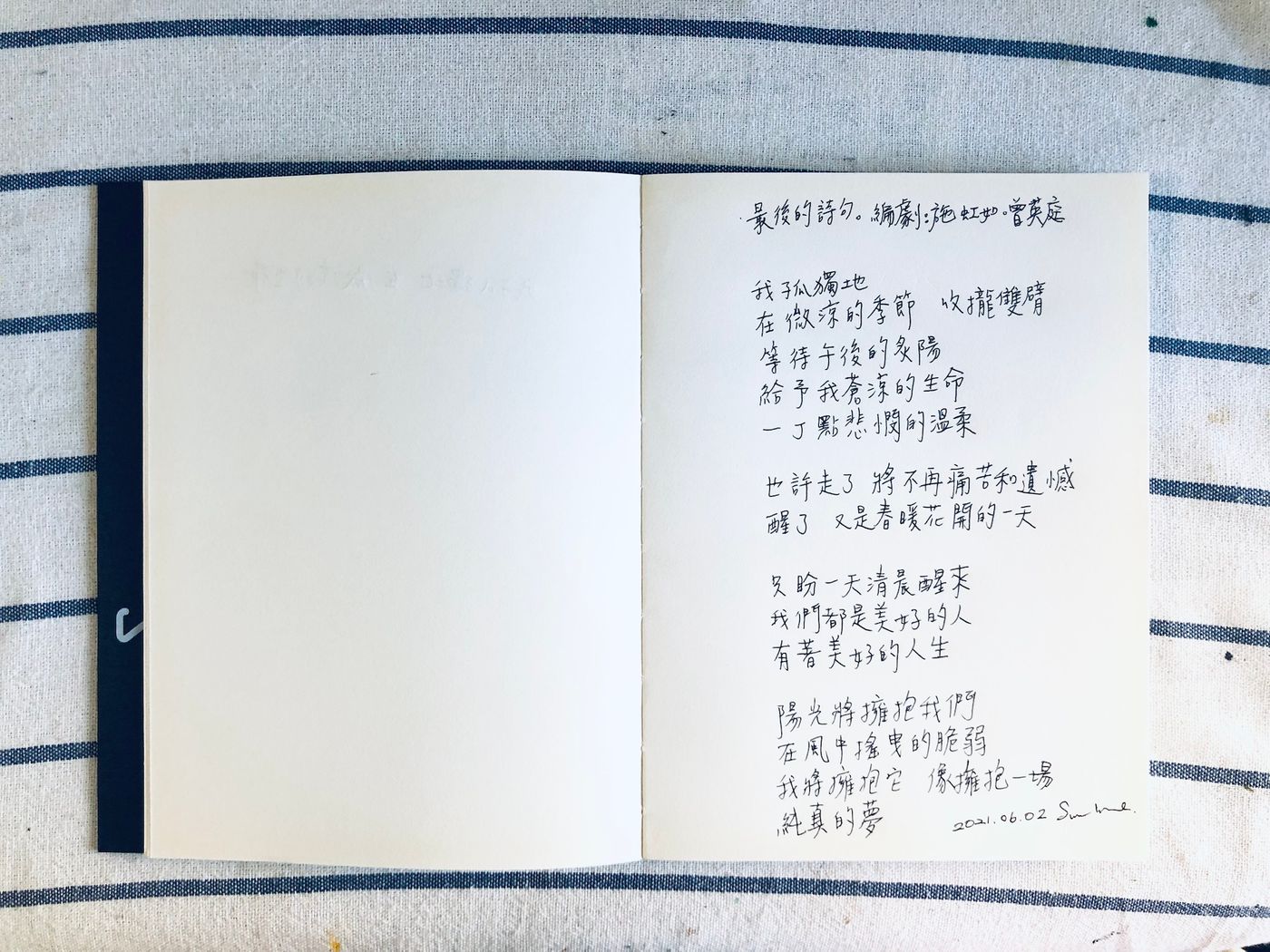「黑暗並不會讓我失去感官,當萬物撕去了一層層發亮的胎膜,裡頭就是我要尋找的詩歌。」——曹馭博
曹馭博的這部詩集,詮釋了年輕一輩看待社會的內心,很多人以為現代青年速食、膚淺,其實那只是表象,真實的我們簡單而深邃。時代逼迫我們嚴肅的面對生命與死亡,因此我們以針尖刺入深處,診斷與測度著毒素,這也是為什麼,他的字句如此凝歛。
作者的詩句看起來跳躍、斷裂,是因為現代本就斷裂而不連貫,不再承襲歷史原初的樣貌嗎?他在後記裡提到:
「我的詩行被干擾、挪移、破壞,像投影一部壞掉的幻燈片,燃燒著視覺畫面,某個細節片段一再重複,斷續的喀嚓聲響,像一位獨裁者傲慢的掌聲。」
或許某種程度上,這便是我們的解離吧。儘管我們出生時,台灣就告別黨國體制迎來民主,但過長的戒嚴時間,使得新生代必然面對社會的過度保守;而改變與突破現狀,也將遭受壓抑與困難。獨裁者的掌聲迄今依然迴盪,且陣陣地飄洋過海而來。
本書開頭所引用的詩,已透露這部作品的宗旨及核心:
我們已躺在
帶針葉的灌木叢生處,當你
終於匍匐著爬向這裡。
然後我們未能向著你
布下陰影:
這裡做主的是
光明之迫。
——保羅●策蘭(鄒佑昇 譯)
輯一、鑽石孔眼的複述。面對鋪上一層灰的現代,要想觀察真實的表象,我們必然匍匐地爬向灌木叢,而在那裡發現的是光明之迫。面對光明與黑暗的落差,人們經常困於孰是孰非,而無法前進。
後記解釋了「鑽石孔眼」來自赫拉巴爾,其明確指說:「人們恐怕就是虹膜進化的詩人,不信任偽造的光明,看似臣服於黑暗,實際上卻是在無邊的自由裡頭遨遊。」
為了生,我們首先必須面對死,輯一的詩篇即是在生死中浮沉,尤其龍山寺到江子翠站的〈四分鐘的黑暗〉,彷彿跟著作者在漫長的黑暗中,諦聽現代背後的聲音。身為台灣人很難不想到,那段黑暗裡曾發生過什麼。
輯一最後的作品〈夜的大赦〉,更引領我們走向鑽石孔眼的盡頭,裡頭有種荒謬而近似集中營的氣味。黑狗令人想起徘徊的絕望,歷史的錯誤與牆內的哼唱暗喻極權,蘊藏哈維爾〈無權勢者的力量〉想表達的核心;最後一段的幽靈很難不聯想到「一個幽靈在歐洲徘徊……」,而「野蠻的中陰身」,則隱隱含有「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至於中陰身則是那些受難的生靈。
此刻引出一個問題,「夜的大赦」究竟是什麼?夜,是洞穴隱喻的沒有影子的所在,對裡頭不存在罪行的概念,而進行赦免嗎?作者是否發現存在是虛無另一頭的大赦?但他在後記裡給出了指引:
「我原以為黑暗即是邪惡,光明才是人類的棲身之所——但不盡然,黑暗並非否定的概念,因為光缺席了,視網膜上的細胞產出特別的視覺效果,使我們「看見」黑暗......」
照此脈絡來看,夜的大赦更指向於強光之下的受苦難者,該受到大赦而解放的是他們,而輯四的標題〈人工的光〉其實也透露了線索,且更符合全書意境。
「也許黑暗才是這個時代真正的庇護所,光明可能是暴力,並非正義或法理,而是強制與權力。」
輯二、幽靈的複述。即作者代替中陰身說話,複述幽靈們曾經歷的苦難,這裡每一篇都在極端的荒謬中,尋找微弱的生。
〈貝加莫醫院〉是發生疫情的義大利,也是全世界的一個縮影;〈吃冰淇淋的女孩〉則透露了,我們不是普羅米修斯,只能給小女孩挖冰淇淋,且對邪惡的禿鷹麻木。
〈我的屋子空了一間房〉,是關於香港的抗爭詩;〈賣火柴的少女〉則是成人童話,也是格林童話的本質。〈小說〉也是部抗爭詩,老婦令人想起天安門母親,那「三次投稿未果的小說」或許是89、14、19,而「它尚未完成/將會重生:情節、字型、肉身……」,也是種深刻的隱喻。
尤其最後的〈六月,廣場,我正前往〉,這首抗爭詩能夠看見年輕的苦難,彷彿走在通往三十年前的廣場路上,而三十年前的廣場,其實又走在七十年前的路上。一個世紀了,吶喊與徬徨仍未消散,天曉得台灣人何時也將前往那場構火,或者屬於我們的戰火。
「我呼吸——就只是呼吸,讓細胞的火爐開始運轉,感官的薪柴驅動了記憶,思想伴隨著詞語,如同列車般緩緩駛進視覺的站台。」
是服膺獨裁的漠然,亦或在荒謬的時代裡,忠實地記錄下過程便是一種反抗?記憶,是一種真實性,若想合乎時宜,最好的方式是任其走過眼前,轉眼即忘,甚至乾脆蒙蔽或刺瞎雙眼。
終究,在這假性的和平下,最好的方式是記錄。於是我們對這份集體與偌大的和諧失語,在紛雜紊亂的繁華裡,聽見喧囂裡的孤寂,也看透光華底下的汙穢,並複述幽靈的語言。
「同時代人聽見了我的腳步聲。」
我想說,我們聽見了。
輯三、當幼鹿尋覓語言。在枉然焦灼後,作者想像自己跟隨數十位詩人,或者說數十頭成鹿,尋覓草食及語言。有趣的是,假設將整部作品當作一個過程來看,這輯頗有跑馬燈的意味,開頭的〈當幼鹿尋覓語言〉即透露了追隨之意。
「他們逝世前的那個早上,複述著同一個夢。」
於是「幼鹿開始尋覓語言」,作者是幼鹿,而我們也是其他的幼鹿。詩句與對應的詩人,應該某種程度上都跟他們的生平與詩句有關,例如波赫士曾寫過:「詩人,和盲人一樣,能暗中視物」 ,而〈眼睛〉裡便有提到相應內容。
這輯並非只是沒〈卵蛋〉的臆想,作者在其中有意地表達志向,因此也像幼小的星星向星辰尋找語言,跟著他們的軌跡尋覓。〈蘑菇〉裡提到,「悲傷是詩人的遺產」,就很有承繼先賢的意味。
但最終似乎只來到諷刺的結尾:「蝴蝶只是另一個人刀片的拷貝/近似一顆露珠/上帝恆久的近視眼。」
輯四、人工的光。跑馬燈後,前世那漫長的死亡又回來了,這輯一開頭,刺眼的強光就不斷射入眼眸,在夜裡照出我們的身影,拖向死亡的深淵。〈人工的光〉裡寫著:
使我無情的,並不是節制
而是悲痛與恨意。詩行狹窄
足以讓詩人用亞歷山大體
下葬一個同代人的生平。
到了〈四樓窗台下的即景〉更是寫著:
——我扒開了它,陽光
立刻將萬物糊成一處傷口
世上所有人都來不及痊癒
之後走過地獄最熾熱處,來到〈我們的傷口終會相認〉,經過漫長的死,令人失語的極端後,後面幾篇生之氣息漸漸回來了。最後一篇〈關於詩的問題〉,作者和小詩人透過對話找回本源,透露出詩的本質是生命的熱情,好像終於窺見黎明的微熹,我們也終於能夠喘口氣。
漢娜鄂蘭在〈人的條件〉裡提過,音樂和詩是「物質化」程度最低的藝術,以及詩的材料是語言,它似乎是最人性的、最不具世界性的藝術,其最終產物一直最接近原本啟發它的思想。
後記裡,作者用詩意散文詳盡闡述近況與想法:
「在不開燈的情況下,黑暗才能發出回聲——在許多個瞬間,我是如此堅信,黑暗能包容一切,在裡頭,萬物皆能互文,我們的傷口終將相認。」
誠如廖偉棠老師所言,作者危險的征途才剛剛開始。或許,作者在地處河口的淡水,學會了為都市把脈,感受著緩慢而急促的將軍令,諦聽其中蘊含的悲苦,也聽遠道而來的黃頭鷺傳遞耳語。
而我們唯有棲身黑暗裡,才能獲得夜的大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