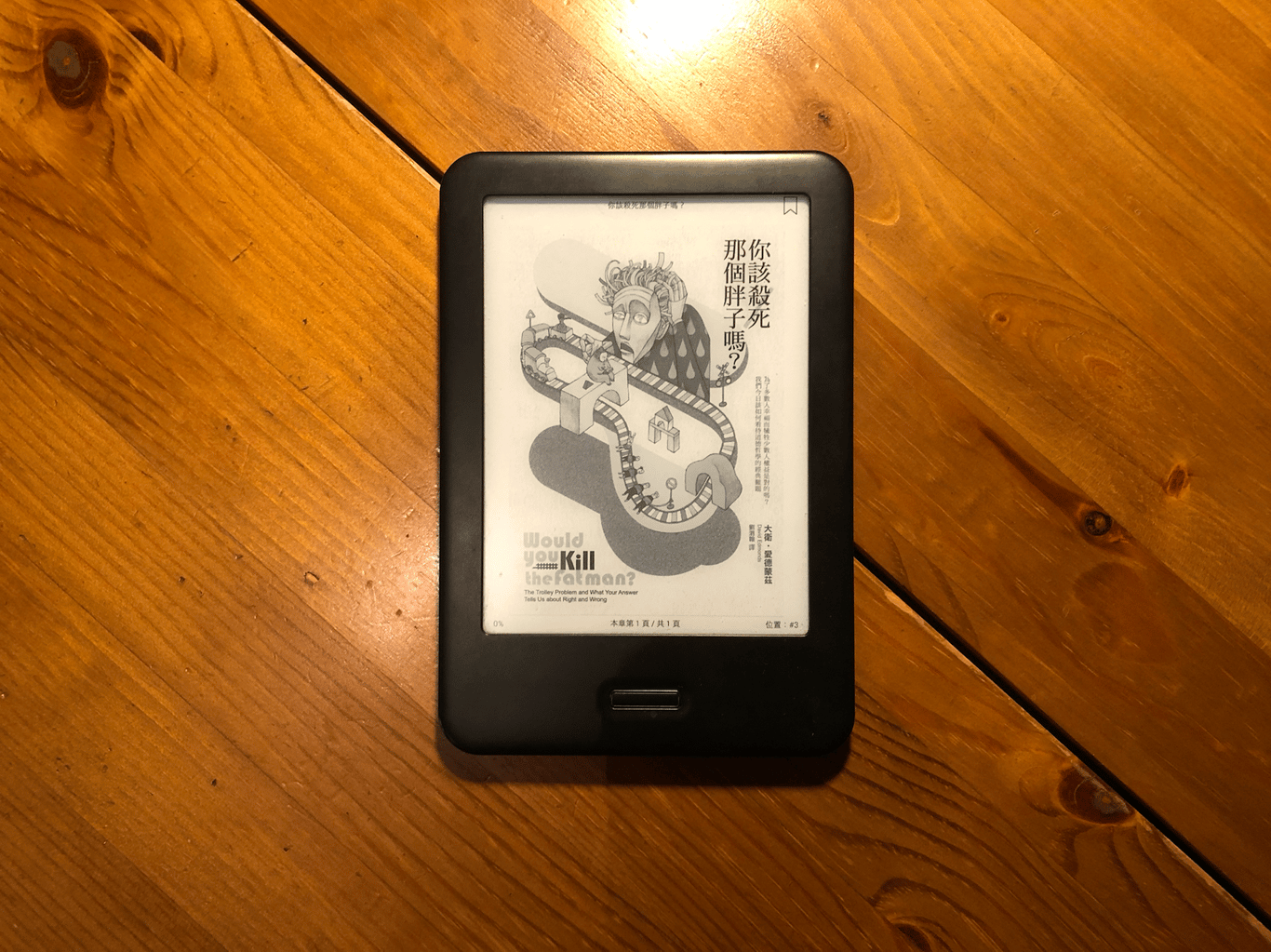簡介
這本書以日常的事件起手,逐步引領讀者思考究竟該如何反應那些「模稜兩可」的事。
這讓我想到學物理時的事。學物理時,課本會先講解理論定義,而後再講述應用。為了更全面描述定理的適用範圍,這些述敘句子通常會很長。學生在學習時,也不可能直接記住這一長串字數。當時我老師的做法就是直接解題。這個做法就和這本書一樣,藉由設定情境題,感受何時該使用這些理論。
我認為這樣是最能讓門外漢快速學習的方式。
以下我就簡單記錄此書中的重點,作為未來的你我複習之用。

教養與教養教育
二○一七年的金鼎獎,郝廣才說「人們在台北車站大廳席地而坐,顯示出因為不讀書而導致的教養問題」。引發熱議。
新聞網址:「台灣人沒教養、坐在車站大廳像外勞?」金鼎獎主持人發言惹議- 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網
「習慣在捷運車廂裡大聲講電話。」涉及「應該如何尊重他人生活」,為「公民的教養」。
「常坐在車站大廳的地上。」涉及「應該看起來如何」,為「習俗的教養」。
「坐在車站大廳有礙觀瞻」難道不算是尊重其他行人嗎?如果這個成立,那我們可能也要同意──為了不至於讓別人看了不順眼,大家應該避免把頭髮染色。
習俗的教養與文化有關,如「吃湯麵的聲音很大」,在台灣可能被批評被教養。但在日本則展現了對拉麵師傅的尊重。如「坐在車站大廳地板」是出於他們對「習俗的教養」的理解,也是一種文化衝突。
當我們將各式各樣奇怪的規範丟到孩子身上,而又說不出好理由為何這樣做時,到最後孩子會變成怎樣的人?
哲學家的思想實驗
如果有個惡魔,逮住了你,又抓了一個倒楣鬼。這個惡魔要和你玩翻銅板。
● 如果你翻到正面,惡魔會放了倒楣鬼。
● 如果你翻到反面,惡魔會殺一個倒楣鬼以外的人,接著繼續翻銅板。
● 如果你拒絕翻銅板,惡魔會殺了倒楣鬼,遊戲結束。
不管怎麼選,期望值都只有一個人會死,你會怎麼選?
這種思想實驗看似沒有意義,但唯有在這「幾近真空」的思想實驗室裡,我們才能釐清自己對風險、期望值的態度是什麼,以便進一步思考道德上要怎樣把風險、期望值納入考量。
生命的荒謬
當我們日復一日地進行千篇一律的事務,可能有一天忽然回過頭來,自問:「我究竟在幹麻?」當我們朝向一個目標努力許久,也可能有一天驀然驚覺:「如果我們都即將會死,我的努力還有意義嗎?」
人生的荒謬在於追尋意義的人流失意義感。這種人希望理性能協助自己活出有意義的人生,但是理性卻同時讓他得出虛無主義的結論:人生毫無意義。這種衝突令他感到荒謬。
信仰「上帝」或滿足感官需求是好的嘗試嗎?卡繆認為這只是否定荒謬。然而荒謬就是存在,再怎麼否定,它還是在那。
卡繆建議我們要反抗它、正視它。如同推石頭的薛西弗斯,如果我們覺得薛西弗斯是痛苦的,他是悲哀的,無法戰勝巨石與自己的內心。若我們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呢?那他就是自己命運的主宰。
雖然乍看之下是鴕鳥心態,但仔細想想,也唯有如此才能讓自己過得開心點。
生命的意義有客觀標準嗎?
阿明整天一個人玩電動。有天爸爸看不下去了,說:「阿明,別再玩電動了,去做點有意義的事。」
阿明不爽地問:「不要然做什麼事才算有意義?」
爸爸解釋:「你要找到自己的興趣啊。」
阿明回嘴:「我的興趣就是玩電動呀。」
爸爸怒道:「那你有想過自己做了什麼貢獻嗎?沒有,因為你只想到你自己。」
關於人生意義的兩個觀點:
- 「主觀滿足論」,人生的意義就是滿足感,找到熱情則是獲取滿足的手段。
- 「客觀價值論」,是為有客觀價值的事物做出貢獻。
前者有道理的原因是,人們覺得滿足時,常覺得自己的人生有意義。
後者則常用來評斷別人的人生意義,如愛因斯坦的人生很有意義,因為他為科學貢獻良多。
而「主觀滿足論」的衝突思想實驗是:
如果薛西弗斯被注射一種物質,讓他對推石頭產生熱情,並從中獲得滿足感。使薛西弗斯在滿足中過完餘生。主觀滿足論會認為「滿足版」薛西弗斯的生命意義比「原版」的更多。但一般人不會這樣想。
「客觀價值論」的衝突思想實驗是:
薛西弗斯覺得推石頭很無聊,但他不知道自己不斷推石頭,其實把附近的禿鷹都嚇跑了,於是周圍的居民不再受禿鷹侵擾。以客觀價值論來看,「稻草人」薛西弗斯的生命意義比「原版」的薛西弗斯多,但這種人沒有滿足感,因此不該算是有意義。
因此,合理的解釋應是要揉合兩者,不應過份強調主觀滿足感或客觀貢獻。所以回到一開始的例子,合理的建議是:「在追求熱情之餘,也得想想自己的熱情所在,是否能為世界做點貢獻。」
要人保護自己就是譴責受害者嗎?
二○一七年九月,媒體上一則《五歲女童全裸在台北車站捷運出口玩耍》的新聞引發網路輿論。女童母親表示,自己在女兒提出脫掉衣服的想法後,已與她充分溝通,除了確認那是她所希望的決定,也明白自己無法勸阻女兒,因此才選擇尊重她的決定,把衣服脫掉。
新聞網址:北站捷運出口女童全裸母稱:尊重小孩的選擇-社會-自由時報電子報
有些人指出,當父母放任女兒於公共場合全裸活動,可能使女童暴露於遭受潛在犯罪者侵害的危險中:即使沒有立即的侵害發生,也可能使潛在的犯罪者進行侵害的預謀,或至少引發潛在犯罪侵害女童的意圖。既然已知有這樣的預謀,父母應該採取必要措施,保護女童陷入風險之中,也應該教導女童保護自己,避免風險的危害。
這是不是在「譴責被害者」呢?但那些人的想法很可能很單純就是:如果能透過一些簡單的方法來保護自己,為什麼還要堅持暴露在犯罪的風險之中?
讓我們想像一場森林大火,其發生原因是營火未完全撲熄。然而,若只有營火未完全撲熄,顯然不足以引發森林火災,還必須有許多條件配合才行。那為什麼我們通常認為營火未完全撲熄是原因呢?
這時再想像一個場景:有一群金星人觀察了這場火災,他很可能會說氧氣才是這場大火的原因。因為金星上沒有氧氣。
這其中的差別就是判斷者的認知不同。
我們會根據什麼事情本來就應該發生,以及哪些事情其實不應該發生,來區分什麼是導致事件發生的原因,什麼又是背景條件。例如前述的森林大火,空氣中有氧氣是應該的,它是背景條件。而沒熄滅完全的營火是不該發生的,所以它是事件原因。
那麼受害者如果保護好自己,就不會受侵害,這也是事實。所以受害者確實有責任要保護自己免受侵害。
然而,這裡的責任並不包含「分擔加害者的責任」,而僅是認為「每個人都至少有責任保護好自己」而已。所以當我們主張他人應該要保護好自己時,這其實是一種未經授權的譴責。
道德上,我們可以反抗打人的警察嗎?
想像情境,如果有一個人衝到街上打你,你知道如果不反抗的話,會被打到手臂骨折。請問你是否可以反擊?
又再想像個情境,如果有一個警察衝到街上打你,你知道如果不反抗的話,會被打到手臂骨折。請問你是否可以反擊?
(這裡的可以指的是道德上)
如果有人說前者可以,後者不行的話,那麼會得到一個結論:因為他是警察。
人民有服從國家的義務嗎?有些人說國家和人民之間有一種類似契約的關係:國家提供給人民安全、保護、基礎建設,而人民接受這些東西的代價,就是服從國家的法律和命令,譬如警察打你時不得反抗。
然而警察在打你時,有做到上述的事嗎?安全呢?也就是說,警察在無緣無故打人的瞬間,就已經違反上述隱形的契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