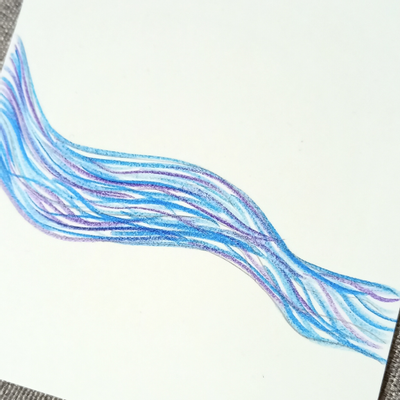風聲拂過樹林,帶起細碎的鐵鏈聲。
聲音遠遠迴盪,聽不出是風,還是什麼在笑。
車門重重關上,悶悶的聲響在車內回蕩。
陽光從玻璃灑進來,刺得眼睛微微發痛,卻無法驅散我身上的寒意和汗水。
林芷瀅雙手緊握方向盤,指關節發白,眉頭緊皺,整個人像是剛從陰影裡走出。
她的制服沾染了泥土,卻絲毫掩飾不了那份冷峻和戒備。
「妳剛剛…妳剛剛說聽到了什麼?」我忍不住開口。
她視線依舊盯著前方,聲音卻低得幾乎被引擎聲吞掉:「不像是人走路的聲音……更像——」
她停了一下,像是連形容都覺得不對勁,「…骨頭在摩擦的聲音。」
寂靜,車廂裡的空氣瞬間凝固。
「妳不覺得,我們剛剛被…看著嗎?」我壓低聲音問。
林芷瀅沒有回答,只是緩慢轉動方向盤,把車開上山道。
幾分鐘後,她才開口:「你祖父的名字,在那裡出現過幾次?」
「至少三次。」我盯著車窗外掠過的樹影,
指尖不自覺握緊,「新聞、筆記、還有坑道牆上的符號。」
「還有林老三。」她補了一句,「檔案被人動過,死亡時間不對。」
我轉頭看她。
她的表情沒有變化,但語氣冷得像刀鋒。
「有人不想讓這段歷史留下來。」她說,「而且,不只一個人。」
引擎聲在山道間迴盪。
誰都沒有再說話。
回到家時,已經接近黃昏。
老屋的木門吱呀作響,門內瀰漫著藥草與潮濕混雜的味道。
父親躺在床上,呼吸紊亂,嘴裡斷斷續續念著無法拼湊的詞句
「爸?」我試著開口。
他沒有抬頭,呼吸紊亂,嗓音乾裂,像是對空氣說話。
「你爺爺…他還在挖。」父親低聲呢喃。
「挖什麼?」我逼近一步。
「挖———回來。」他的聲音忽然尖銳起來,
抬起滿是血絲的眼睛,死死盯著我,「不能讓牠們出來……」
下一秒,他就像昏了過去,沒有任何的聲響。
「唉..」
我替他蓋好被子,視線卻落在他書桌上那張照片。
泛黃的影像裡,是坑道外的軍隊合影,一群日本士兵和苦工站在坑道口。
而照片一角,赫然寫著一個名字陳木河。
這名字,我在第一次進坑道前,也從另一個人口中聽過。
第一次進坑道前,林老三在胡言亂語中喊過,說那是「唯一活著走出來的人」。
當時我以為只是老兵的瘋話,可現在這名字竟然同時出現在照片、父親的囈語、還有照片裡。
這肯定不是巧合。
陳木河一定知道些什麼。
而且,他可能是唯一能證明坑道裡「那些東西」是否真實的人。
我直覺,他是打開這場謎團的鑰匙。
我翻出筆記本,把坑道符號、父親語句和照片拼湊在一起。
符號排列像某種路標,而父親重複的「挖」字,或許指的不是尋找黃金,而是..就像再掩埋什麼。
我開始懷疑,那坑道裡根本不只藏著黃金。
警局深夜值班室裡,燈光閃爍不定。
我再次調閱林老三與兵工廠的舊檔案,交叉比對最近出入兵工廠周邊的目擊紀錄。
名單裡,出現了一個幾乎被忽略的名字陳木河。
他的紀錄詭異得不像話:
戰後被列為倖存苦力,但在不同年份的檔案裡,
死亡時間出現兩次,一次在1950年,一次在1965年。
更離奇的是,兩份死亡紀錄的證人名字都不同,但簽名的筆跡卻一模一樣。
有人在篡改紀錄。
而這個人,或者說這股勢力,比我想像的還要深入。
我盯著桌上的地圖,指尖滑到海岸線外的一個紅點,一個廢棄漁村。
那裡只僅剩一戶人家,戶籍上名字就是陳木河。
如果只是單純的老兵,為什麼他的名字會同時出現在兵工廠舊檔案和近期的清理紀錄裡?
更詭異的是,死亡紀錄出現過兩次,筆跡卻完全相同;
這表示有人刻意維護他的「存在」,也刻意模糊他的「死亡」。
所有線索都往同一個方向匯聚,
就像有人在引導我一樣,可這一切,是陷阱,還是真相?
而江靖川,他到底知道多少?
我收拾相機、相片和筆記本,帶上錄音機。
這次,我要把真相留住,不管那是真實還是幻覺。
我檢查手槍、裝滿子彈,額外帶了手電和膠帶。
調查不是盲目闖入,而是防止被「人」或「不是人」偷走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