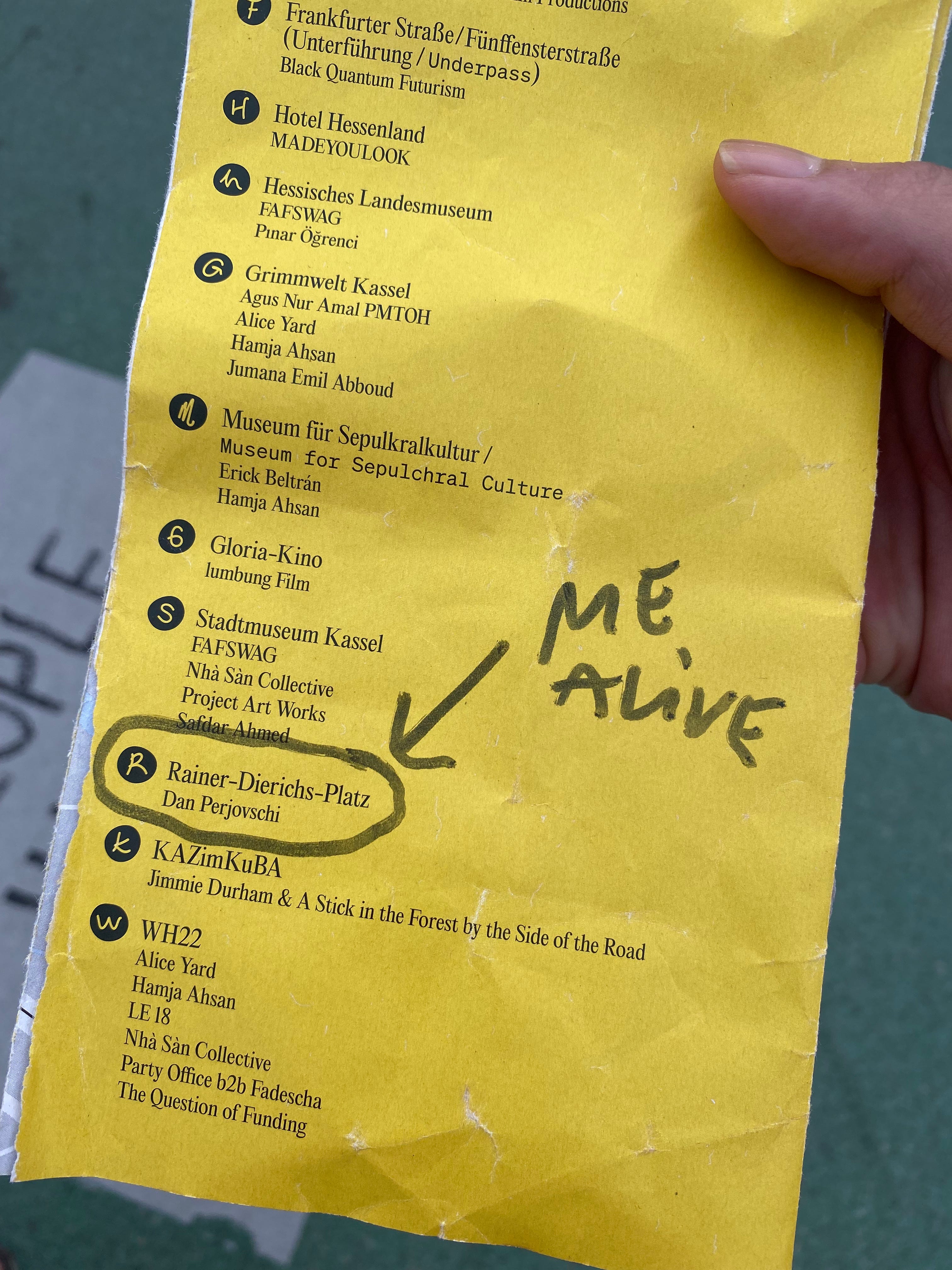看完卡塞爾文件展後也半年了,我目前依然覺得他會是我往後觀看當代藝術的一個重要的參照點。

我喜歡主展館入口進去就是以托兒為主題的展覽,而且真的可以讓父母進到一個有隱私的區域照顧小孩。雖然我們常聽到當代藝術要拓展關係、更貼近生活的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但能照顧到(care/care for)這樣顯而易見卻總是被忽略的面向,某個程度上回答了我對當代藝術的疑惑。

以自然博物館為展場的展區,也配合展場的原本功能,展出以人類學視角觀看自然與人類技藝的考察/研究型藝術,我個人對這展場的心得是:這是試圖提出另一種技藝/記憶的抵抗,抵抗的對象是現代性與資本主義帶來的同質化世界。藉由展出其他文化的建築技藝、編織技藝等,佐以社會學式批判內容的展覽文獻和影像紀錄,可以感受到策展人的政治企圖,而非天真的少數文化的展覽。

在大場館中設置滑板場,據我在場刊讀到的說明,是將卡塞爾社區帶進文件展的企圖 — 在文件展的說明中心地下室的小展中,其實已經有展出和提到,十四屆以來的卡塞爾文件展,卡塞爾當地的藝術家或工匠都從未參與,彷彿卡塞爾文件展是一個地區/政治上的真空地帶,儘管他號稱是非常政治的。說明中心的小展展出了當地藝術家、學者、發明家,還有奇人的物品,而滑板場則是將卡塞爾的滑板社區帶入展場,並會在固定時間請滑板高手表演(可惜沒看到),滑板場的平台可供塗鴉,藝術家也會前來製作工藝品(像是芭蕉扇的東西),再走過去則是印刷廠供藝術家印製海報。一切都是動態的。雖然這使得展覽的潛力很難在一時一刻完全發揮。看到一些藝評在展覽初期前來,大部分展場卻還在創作中,或是一群藝術家舉行小圈圈的論壇。我來的時候基本上展品都已經製作完成,藝術家現身和互動的場合變成是固定時段的活動,對於只有四天時間的我來說實在很難躬逢其盛T___T。




(雖說如此,還是有和一位來自紐約的羅馬尼亞藝術家聊到天,後來也參與到了印尼藝術家辦的印尼語教學 — 不過,從教學的方式來看,可以看出藝術家沒有太在意大家有沒有吸收…XD。雖然可以說是姿態大於實質,但寬容的說,我們好像參與到他們第一次辦印尼語教學,也就是說,又是一個動態和學習經驗的過程。但這樣是要我們在卡塞爾待四個月嗎(呃),所以同時也可以理解到這為什麼會讓人有小圈圈之感 — 只有待在這裡的藝術家可以長期參與這些其他藝術家的活動啊)

卡塞爾以格林兄弟的故鄉聞名。在格林兄弟博物館中,文件展借用了場地來展出印尼的童趣的想像力 — 塑膠製品拼湊裝配而成的機器裝置,若從威尼斯雙年展的高蹈審美來看,絕對是可笑的 — 但這些鮮豔的塑膠製品,還有印尼國寶老先生在錄像中唱歌講故事的影像,呈現的就是另一種「另類」。這甚至不需要援引理論,而是實作帶來的奇妙力量 — 這些作品是藝術家來到卡賽爾後製作的,例如「卡塞爾先生的炸香蕉」(炸香蕉似乎是印尼的點心吧…)。
這次文件展策展團體的核心概念lumbung,是一種共享資源和知識等等的團體模式,讓策展被去中心化,將資源和權力分散到更多藝術家 — 最多達到一千五百多人。雖然不乏有爭議,但我認為這去中心化並不如某些藝評所說是混亂且不成功的。由於文件展內的反猶爭議,似乎讓德國對這次策展方式有些異音,而台灣或亞洲藝評也從這新聞延伸這個觀點。然而,這正是去中心化的效應:實際上,除了醜化猶太人的畫像以外,這次另有展場展出巴勒斯坦和日本赤軍合作製作的左翼紀錄片,控訴以巴地區戰爭的暴行(我時間不夠,只看了有關黎巴嫩的片段)。這些挑動西方神經,尤其是德國社會最敏感神經的議題,在展場內展出或一度展出,就已經是對所謂西方意識形態的挑釁。根據我粗淺的歷史爬梳,印尼由於宗教的緣故,對巴勒斯坦帶有強烈的同情和支持。儘管我無法肯定策展的最核心是否有這樣的政治意識,他們也承認,他們無法全盤掌握展場內容;但不如說,就是在這種無法全盤掌握的集體行動之下,lumbung的合作、開枝散葉到最終的作品,才真正是非西方的。
我並不是說,只要跑到德國大喊反猶,就是對抗西方,反殖民,找出所謂「xx作為方法(你可以填亞洲、伊斯蘭、非洲,etc)」 — 而是沒有審查,沒有自我審查,這件事本身,在我看來是說的遠比做的簡單。我也不是說就沒有任何倫理界線,但在這件事看來,那個所謂醜化猶太人的畫,從整個脈絡看來,是在批判東西方腐敗的政治群像之一,並非無事尋釁。無論如何,lumbung仍然是「印尼的」,也就歷史的會是「伊斯蘭的」,就算這概念再怎麼適合被轉譯,再怎麼具有世界公民的特色,這次策展的實作依舊會有這種區域性的特質,是文化、歷史、政治交織出來的特定產物。雖然最終這個畫像被撤掉(其他仍保留著的樣子),但我想這次卡塞爾文件展已經做到一個至關重要的行動:就是置疑當代藝術內的遊戲規則。
其他印象深刻的有:描繪印尼政治事件的版畫,由藝術家深耕印尼當地社群後,和居民一同製作,藝術家的個體由團體取代;越南藝術家請卡塞爾的越南人提供越南人食用的植物,種在庭園中,並讓在德越南人可以取走帶走一些種子,藝術家的錄像內容則是考察在國外的越南人如何取得香料或其他植物,如何在自家栽種 — 考察對象正是台北。政治與集體如何藝術/藝術如何政治與集體,十五屆卡塞爾文件展會是我的參照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