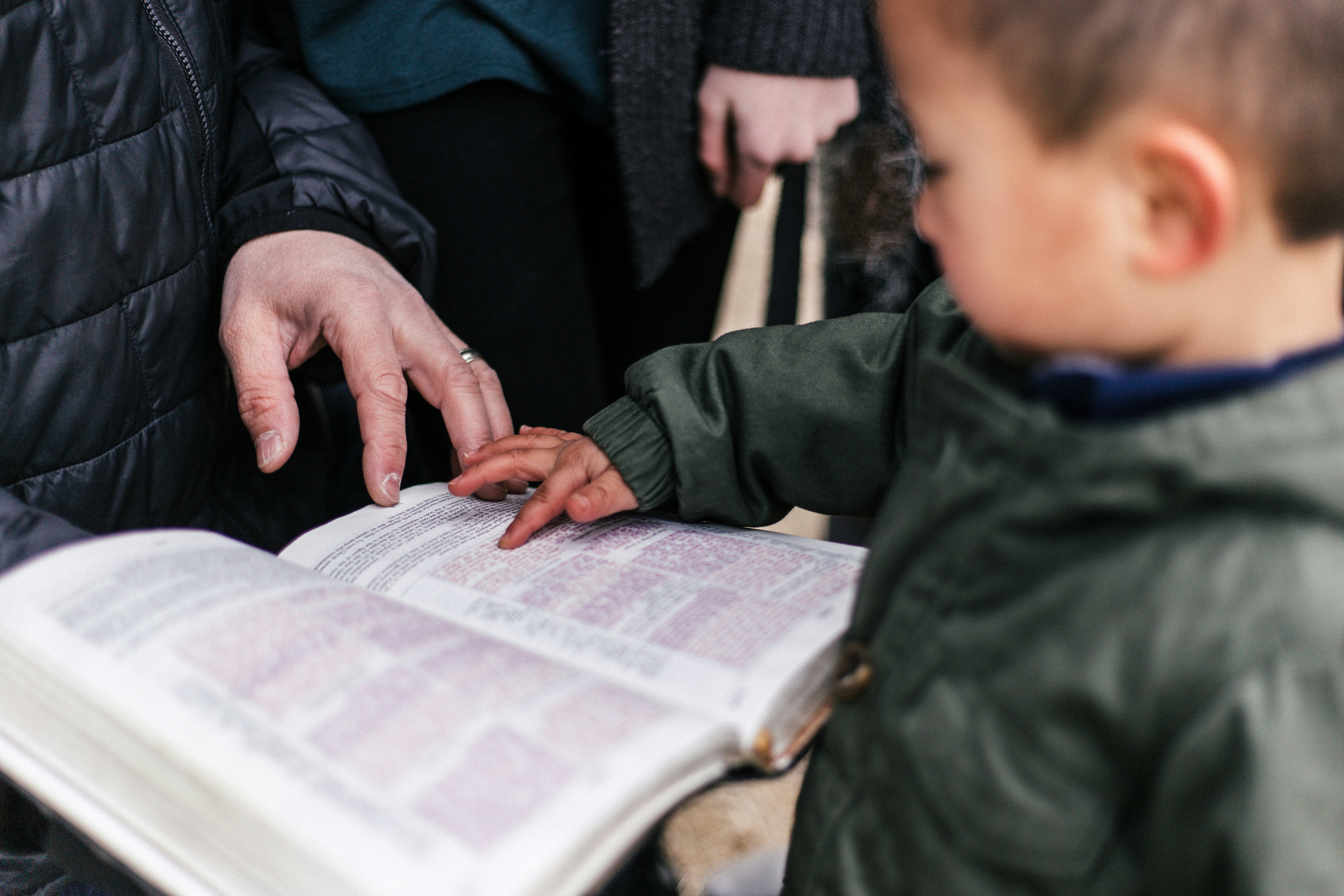不會介紹所有展品,請購票入場。
以海德格引介人的存在,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展覽主視覺以「亻」為符碼,擷取中文部首表意的特性,暗指「人」在各式際遇組合下的可能性;而「Dasein」則出自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探詢人類生存的本質與境況時所賦予的「存有」一詞。––La Vie網站報導。
以上是關於近期在忠泰美術館《亻─ 生而為人》Dasein – Born to Be Human這個展覽的報導介紹。在展覽主題中,放入了海德格對「存有Dasein 」的想像。
一看到這個部分,就激起我不妙的好奇心:海德格除了他的哲學思想、與漢娜·鄂蘭的八卦情史外,反猶、加入納粹的過往同樣出名。於是,在名為人的展覽中,何謂「人」這件事(更直白的說,似乎有些人不應被認為是人),變得微妙而難以言喻起來。雖然從海德格的be there說起人並不壞,但引起我偏門的期待後,沒有處理到這個面向,不免失落。
引言即是引言,概念只是敘事的開端。
談人就是談關係
回到展間,看策展藝術家如何解答「人」這一題。
Candy Bird(糖果鳥)的〈專心(102天)〉,不附圖。因為這個展品,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無」。
102本關於去處與歸途的囈語之書,喃喃著不需要導航又預示一些方向,每過一天,都有一本消失在併排的序列。只會留下殘膠和三分之一、難以滑順撕下的底紙痕跡,已經不在的,喚起存在的感受。個人蠻喜歡這個動態行進的展品與概念,只是作為這個展覽頭幾個作品,對觀者如我,似乎有些跳躍—以討論人的角度來說,或許有些太快進入抽象概念的存在,人在此是意念而無體的展現。
與其說是探討存在的展,不如說是一場盛大的勞動苦難博覽
接下來是二樓的展間,最好拍也最好放在IG上。在不鏽鋼球體轉圈,神色姿態各異的上班族、色彩豐富的影像紀錄,一踏入這個展間,感受到濃濃荒謬的意味—一個談人的目的的展覽,最終還是繞不過勞動。
轉來轉去的上班族,鞠躬哈腰,平日受氣、假日文青的上班族,沒想到來陶冶氣質也躲不過勞動這一題。人的本質就是生活的本質。
日常的勞動之外,也有遠方的勞動。遠方的意思,大概是在這棟樓之外,想像中假日與美術館無關的勞動者。蠻喜歡這系列的影像作品,盯著螢幕,想找出影片的起始與終點,一晃神,終點又變成起點。無休無止,永劫未盡。苦難的勞動者恆久忍耐,雙臂一度顫動,幾乎以為有什麼要打破持續下落的無法承受,卻只是更堅定的,將痛苦僅僅收攏在眉間,除此之外,一切安好。



勞動未曾休止,屏幕後不斷進行的人體紡織,把自己困成蜘蛛,咚咚咚的捶打地面,嘴咬著絲線因此失語。
兩側的黑白相片(無圖,請進場看展,照片我很喜歡),呈現另一種截然不同的風景:同樣是勞動,靜態的微笑或做出預先設定的手勢、或搭配一隅街景,真實的勞動現場,勞苦的氛圍竟比不上鮮豔做作的人工苦難。但或許也真,勞動,本身是人難以迴避的部分,其中不想承認的,也有快樂與意義的寄託。
小小的展場裝不下「人」巨大的存在

最後說說火柴人。細看各異面孔,亞洲臉孔的火柴棒特別短小,有趣的巧合(或有意為之)。終點是燒毀,未達終點的也不得寧靜。過小的展間,幾件展品,太快走到結尾,中間嘛,充斥著工作人員絮絮叨叨的提醒。在這裡,人能擁有的空間很小,人對意義的遠大追尋與想像,是難以承載在兩層樓裡。
生而為人這個巨大的命題,在過窄的地域矮下身子。還是推薦走走看看,畢竟一百個人就有千百個想法,也能夠想像千萬種身而為人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