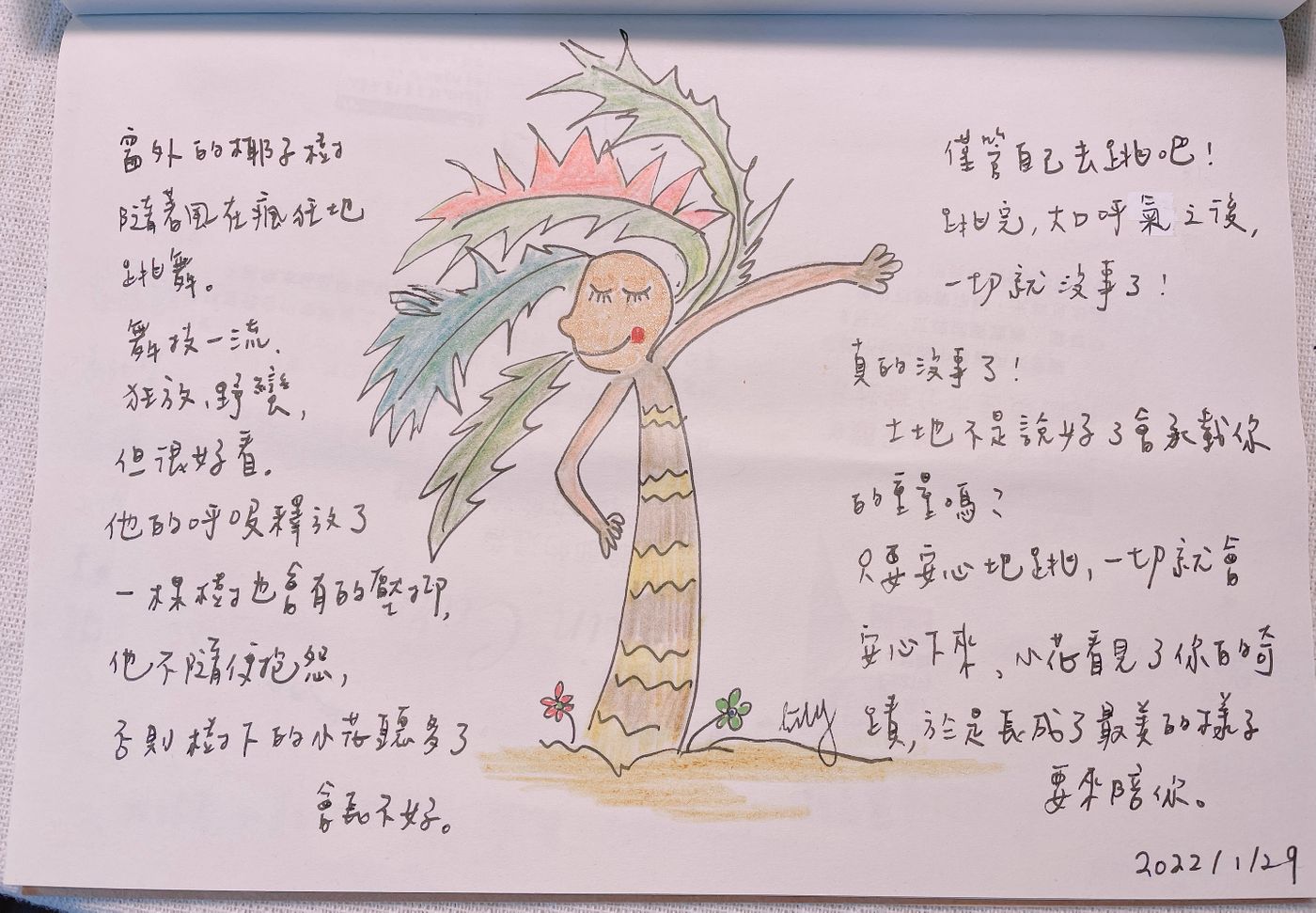欣聞香港作家梁莉姿以《樹的憂鬱》榮獲金鼎獎,將本文略作編輯後重貼分享。
第一次知道梁莉姿這個名字,是幾年前在台北大稻埕的啤酒館樓上,忘了是獨飲或者等人,只記得信手將端坐於小書架上的《明媚如是》取下翻閱,這個名字與清風般的文字觸覺,就一直留在心裡。
後來在新年時讀了《日常運動》,隔段時日又讀了《樹的憂鬱》。五月參加梁莉姿的分享會時,她提到,有人質疑她「為什麼寫得這麼快、出得這麼頻密?」
——我總覺得這種事隨人說,寫得快了別人說「是否不顧品質趕著風口浪尖消費議題賣血饅頭」;寫得慢了別人說「是否江郎才盡心理出問題也就跟一片歌手差不多」——話都給這些人講就好。
.初初來臺的青澀、好奇、猶豫、以及格格不入
單就讀者感受而言,《樹的憂鬱》確實寫得急切,部分語句甚至還有未抹平的匠痕;但我可以理解,她是要在變成老江湖之前,「珍惜來臺的陌生感」,寫下新手的青澀、好奇、猶豫、甚至格格不入。
當然某些觀察是辛辣的,尤其對自詡「華人」民主聖地的臺灣人來說。〈野貓〉中,來臺港人「真真」以為臺灣人都對政治、參政權和公共事務充滿熱情,「在對話中益加進步,儼如積極公民」;結果發現大家標榜的權利主張就像電腦後的標語貼紙,是海市蜃樓,「好看、易於破損、輪常替換」。
自嘲亦不手軟——〈辦雜誌〉的陳瑜在被捕前一天說,未來的博物館裡應該要有小孩已認不得的紙本雜誌、工業大廈、「還有個香港獨立展館」。
某些尖銳是幽默的。「當一個稱職導遊跟當一個稱職移民者有什麼共通點?——配合凝視和期待,面對伸手,張口,索求訊息時,盡力專業滿足」;關於路名的笑話:「和平在哪?建國路堵住,光復已過去很遠了,我們找不到民權」〈寫生團〉。
某些叩問是直指在臺港人內心的,「有時候,妳迷濛醒來,望及室外藍天白雲,難得陽光明媚,就覺著,這麼溫煦地活著是可以的嗎?」曾經在異國,隔著時差不分晝夜地眺望故鄉那幾個生死存亡時刻的臺灣人,對這樣的場景和心情,應該也是很熟悉的吧。
.樹的憂鬱是一邊紮根一邊發芽、瞻前顧後的憂鬱
不知道是否共鳴較強,至少聽過兩個寫作者喜歡〈To Write or Not to Write〉這組揭示寫作者創作過程與內心轉折的對寫;我喜歡其中〈家長〉的小懸疑設定,也喜歡〈愛人〉的創作課堂記錄感,但卻更被〈樹的憂鬱〉這組對寫打動。
小時候看韓劇《藍色生死戀》,記得好清楚,女主角恩熙楚楚可憐、反反覆覆地說著:「如果可以,我想變成一棵樹。」
變成一棵樹就能待在一處,此生不必顛沛流離、不必與難得的摯愛分開。
而梁莉姿所謂樹的憂鬱,是對比著「一隻動物上路⋯⋯光溜溜⋯⋯無法回頭,無太多行裝」的憂鬱。
樹的憂鬱是即使種子渡海而來,仍然一邊紮根一邊發芽、瞻前顧後的憂鬱。
時移世易,即使樹「不會說話,不會奔逃,就在這裡」,樹仍然記得,曾有另一個島。
身體「就在這裡」、但心裡或許還緊握著另一個島的樹,該怎麼面對周遭環境呢?「躺下來,不追逐,不索求,不介入,讓一切自行生長,是一種方式。但躺久了,看到什麼閃閃有光的東西,想要追上去,也是一種方式。」至於追上去會發生什麼⋯⋯
「那都要妳先追上去,才會知道。」
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小說中已可在台參選的港人賢哥這麼說。這是只存在當下、眼前一黑的信仰之躍,也是「如果當刻不種(樹),那未來的自己無論還喜不喜歡,都沒有選擇」的避險。
.忘掉各種盤算,先追上去、先栽下去?
曾聽說過「買島建港」論——集合港人的財富,買下並移居至另一座無涉國際政治的島嶼,重建香港——當下只覺得既困難又容易,有種說不出來的微妙感。
亦想到20世紀初英國報人Wickham Steed對猶太人的刻板印象和批評:「這些人與國家沒有任何利害關係,因此他們行事大膽,他們關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滿足自己貪得無饜的財富與權力欲。(轉引自琥珀眼睛的兔子,可參閱【繽紛聖誕的波坦金城和日本「根付」】)」
並不是說港人(以及上個世紀避居海外的台人)就是猶太人,但當腰纏萬貫的商賈想安定下來,參與社區,甚至和國家政體「發生利害關係」時,是不是都得有個忘掉各種盤算的瞬間,先對著那道光追上去、先將那棵樹栽下去,才會知道呢?
追記:梁莉姿在分享會上很客氣地笑說:「我的小說比我本人聰明」;或許大家寫作時都有同感:靈機一動或者神來一筆,簡直都是瞬間的「降靈書寫」。選擇暫居後山的梁貌似是離群索居之人,但又有非常健談的一面,聽她嘩啦啦說話,真暢快。
感謝您的閱讀、參與和贊助支持,讓我們持續分享宇宙和心靈的共鳴。This is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