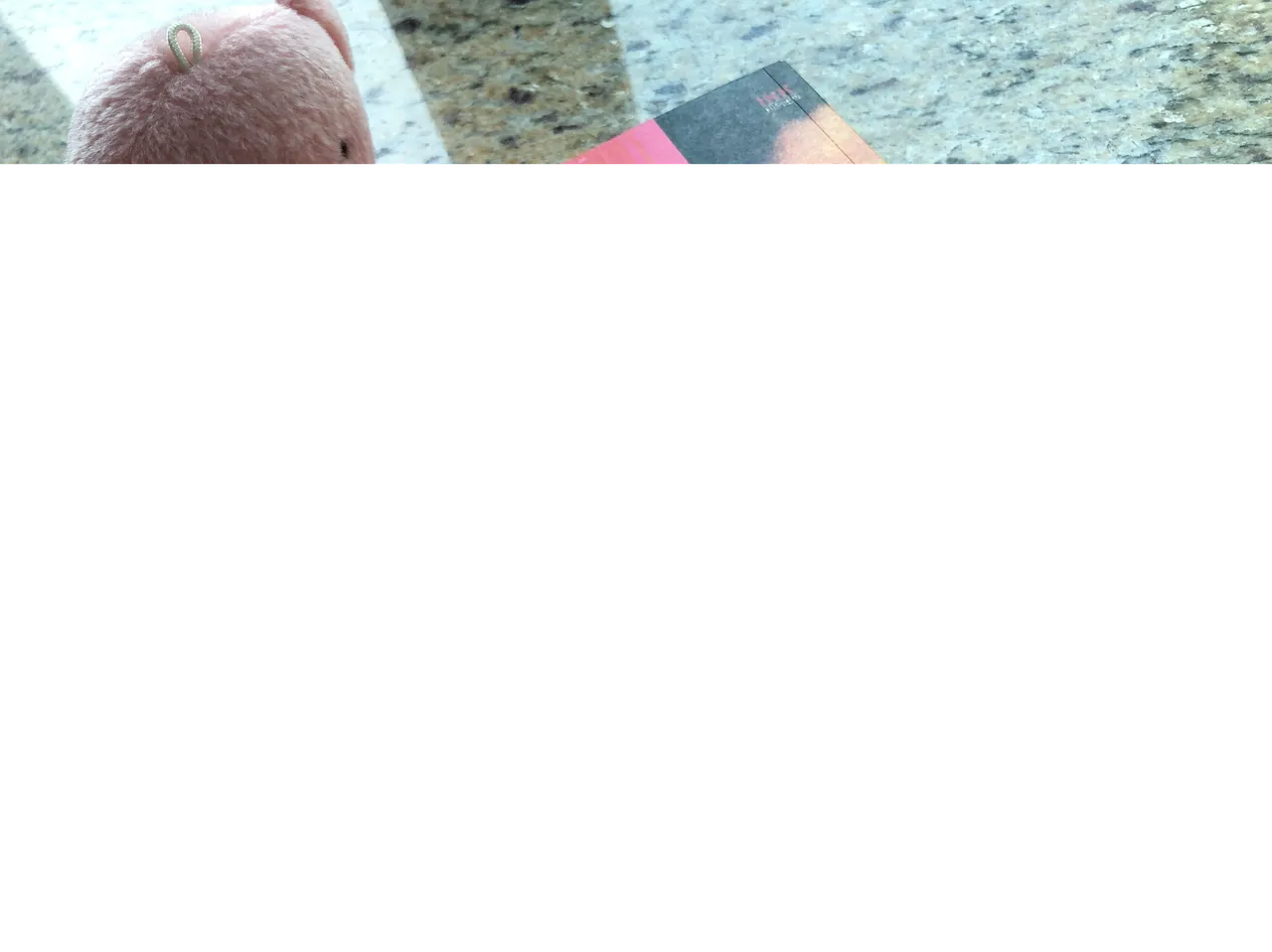「張愛玲的最後一夜」是表演工作坊於2024年的春季所帶給大家的精彩獻禮,那更是對張愛玲致敬的一種獨特方式。劇中以極其特別的形式,描繪著這位在華文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才女,面對生命的堅持與無畏,更創造出每每讓人反覆玩味的精彩角色。戲劇以最後一夜的角度切入,那像是生命邁向最終的過程裡,重新回望己身的遭逢,重新審視過往的創見,那是告別,那不也是一種不捨與欣慰。
極為特別的是這齣戲劇的編導是楊世彭博士,他在張愛玲辭世之後,才在相關資料的檢視裡發現兩人竟是表姊弟的關係。或許也因為如此,面對緣慳一面的遺憾,遂有了創作戲劇致敬的念頭。而心裡不禁猜想著,那也源於張愛玲於1995年於洛杉磯過世時的許多訊息,不免讓人慨嘆。透過戲劇呈現,也許那是一種緩解,或是一種轉譯,抑或者那是一種從另一個角度去描繪邁向死亡的意象。
而整齣戲劇中,最為特別的莫過於編劇創造出「解說者」的角色,那不同於一般所謂的旁白,更重要的是,劇本賦予了他是張愛玲「心靈顧問」的絕妙存在。也就是面對獨居的張愛玲,單單的旁白去訴說她的內心世界,不免過於片面與單薄。但戲劇中創造了一個虛構的心靈對話者的存在,讓張愛玲是在對話的過程中訴說著旁人總是難以理解的內心世界。
那樣的發想或許架構在人們總是不免喃喃自語,在那樣的過程中,那或可視為與自己對話的歷程。若將這樣的角色獨立出來,創造出更多的對話,那麼整齣戲劇將更顯鮮活。更重要的是,那再次緩解了孤獨辭世的悲涼。尤有甚者,透過那樣的對話,當可讓人們以不同的角度來面對張愛玲的走向人生終點時的心思。當然,這不過是一齣戲劇,這不過是編導所創造出來的意象。然而面對著種種耳語,以及某些人眼中關於張愛玲之死的謎團,也許放下那種種紛擾,創造出另一個更讓人能夠回到張愛玲創作作品以及自身遭逢的回顧,當是更值得玩味。
劇裡當可分成兩個部分,一是著墨於張愛玲最後一夜與解說者的對話,更由對話的過程中,帶出她生命中極為重要的兩段情感。而這兩段情感,分別以戲劇演出和張愛玲口述的方式來呈現,那在情緒的衝擊上,也有所不同。戲劇的表演,即便不自覺地涉入其中,都仍不同於口述時情感奔騰的發酵。是否那也意味著在編劇心中嘗試去描摩兩段情感在張愛玲老年時內心的感受。初戀的過程與細節,甚至是當年彼此深情的對話,依舊刻骨銘心。而異國相伴的戀曲,則是在生命的依戀與照顧裡,留下了極其深切的情感。前者的抽離,像是故事的轉化;後者的涉入,則是生命的停駐。
另一個讓人讚嘆的則是,透過解說者與張愛玲的對話,帶出眾人耳熟能詳的三部作品《紅玫瑰與白玫瑰》、《傾城之戀》與《金鎖記》。受限於時間的因素,只能檢選部分情節,透過讀劇與表演的方式來闡述。當然,這關鍵未必是在劇情的發展,而是能否藉由戲劇中的壓縮與取捨,而精準地呈現著幾位關鍵角色的獨特樣態。諸如《紅玫瑰與白玫瑰》裡的王嬌蕊、《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當然還有讓人難以忘懷的《金鎖記》裡的曹七巧。
劇中透過解說,讀劇與戲劇的呈現,讓人很快地便掌握了這三個故事的發展脈絡。然而誠如上述,也許更重要的是劇裡描繪著張愛玲究竟如何看待這三個角色。不論是王嬌蕊所描繪的種種顛覆,白流蘇為自己人生所選擇的孤注一擲,甚或是曹七巧的扭曲刻薄,都讓人玩味再三。戲劇裡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舞台上演出這三部戲劇的過程中,張愛玲於一旁深情地觀看著。尤有甚者,《金鎖記》是最後一齣上演的戲劇,那也意味著整齣劇即將邁向尾聲,是故編導安排張愛玲看戲的過程,卻也慢慢地移向那最終的安息之所,也就是她房內的行軍床。
然而,當她躺在行軍床上時,不多久卻又起身,而且這次竟然走入了劇中,且默默地靠向老年的曹七巧。那是她所創造的角色,相信沒有人能夠比她還要了解曹七巧內心的悲痛與絕望。扭曲,往往來自於現實的磨難,內心無處安頓而痛苦不堪,那是不得不,那是走頭無路的求生。然而那卻也是旁人眼裡,不近人情的尖刻澆薄。當看著張愛玲靠向曹七巧時,內心突然有很深的悲痛,若說角色的創造裡,隱含著內心的情感投射,那麼那樣的靠近是否可以視為一種拾回,在生命的最終,在旁人難以理解的狀態裡,看見了己身所創作的角色與內在的一種共鳴。而那樣的共鳴,更是在劇場裡引起迴盪。是否,對每個觀者來說,那都像是一種拾取,關於己身、關於己身的片面、甚或關於己身的陰影。即便只是倏瞬,彷彿都已銘記於心頭。
謝幕之後,王嬌蕊、白流蘇、曹七巧與張愛玲四個角色在那疊合裡,緩緩地交互滲透,那不被理解的悲苦,那不甘於命運的堅毅,那仍欲掙扎創造己身命運的勇敢,還有那看似強勢卻隱含著退卻,而不被外人所知悉的內心。搭襯著「誦讀劇場」的表演形式所傳遞的張愛玲細徹入微的文字,讓人領受著文學的洗禮與心靈的湧動。那確實是極其特別的感受,卻也在那樣的感受裡,不經意地瞥見了文學的迷人與心靈的豐富。
總還記得,劇中特別透過解說著與張愛玲的互動,訴說著當年傅雷對張愛玲作品的批判,而張愛玲也訴說著她的角度與想法。她只是細膩地刻畫著在那個時代裡小人物的樣貌,那奮力掙扎求生的欲望,反倒豐富了人性的種種,何需執著於善惡二分的論述,何需框限在既有價值的牢籠。文學所背負的,也許可以比想像中更為多元,一如人心的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