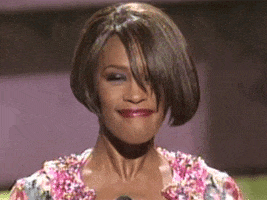《畢設週記02》
閱讀時間約 2 分鐘
在台北現存的城門中,北門因其位置,成為一座有故事的城門,那下個場景又會是什麼畫面呢—要置入什麼議題?
在台北之上,疊了一層又一層的事件,而在20世紀出生於台北的我,似乎都輕踏在最表層,遊走在前人們打造出的現代工廠中,日覆一日地生活著,看似迷人,但這樣一直作為城市中傾聽故事的角色不對吧?像個陌生人孤獨地聽著屬於自己城市的故事。
因此,我想著如果在這片逐漸被一座座現代產物所覆蓋的地景之上,有個可以收集記憶並產出故事的工廠,那麼大家是否都能成為說故事的人了?而記憶也能透過故事的包裝不斷地流傳。
「故事並不全然是記憶,記憶比較像是易碎品或某種該被依戀的東西,但故事不是。故事是黏土,是從記憶不在的地方長出來的,故事聽完一個就該換下一個,而且故事會決定說故事的人該怎麼說它們。記憶只要注意貯存的形式就行了,它們不需要被說出來。只有記憶聯合了失憶的部分,變身為故事才值得一說。」
(吳明益,2011,《天橋上的魔術師》,p219)
將記憶視為所有故事的原型,那如這段話提到的,以什麼形式「貯存」會是生產線上重要的步驟。而從一開始的「記憶」,到最後的「故事」,會是怎樣的一條線,抑或是多條線?是由哪些節點所串連?這是接下來我會不斷探討的,且衍伸在之後最實際的問題—也就是空間需求會有哪些。
「Hooper Greenhill說過,我們從前(現在仍是)以建築物來想像現代主義的博物館,而未來的博物館則是以過程或經驗來被想像的。後博物館將要、並且也已經開始採取許多的建築形式。」
(殷寶寧,2021,《我城故事:大稻埕街區生活書寫》,p234)
藉由物件的收藏、展示,搭配著推廣教育,來作為保存記憶之載體,向人們放送這些資訊,是現代博物館的作用,而話語權始終不落在參觀的人們身上。而未來的博物館(也就是後博物館)的概念趨向「放大」人們進博物館的「體驗過程」及在這過程中的與物件之「對話」,並在最後成為自己的「想像」。
在我城一書中,跟隨殷寶寧老師探究大稻埕中的兩座博物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及迪化街博物館,讀到Hooper Greenhill曾說的這段話時,想著這與自己思考的議題概念是相同的,但自己是想操作具紀念性意義之地方博物館嗎?不是,不過後博物館的概念中是我能收集的關鍵字。
我想操作的是在具紀念性之場域中,建構前述所說的機制—收集記憶,產出故事,將話語權回歸至人們自己—視角呈現多元的,而北門會是場景之一。然而比起只有紀念「事件」本身,這個機制的過程是我更想述說的。
這艘忒修斯之船航行中⋯
147會員
688內容數
#金大建築15歲 +4了!畢業設計相關的文章,不論是自己的畢業設計、參加宜蘭大評圖的心得、或是相關書籍的閱讀心得,都請在「準備發佈」裡的關鍵字中加上「金大建築15歲」。讓我們來好好回顧我們所接力走過的15年吧。
留言0
查看全部